■郭超颖 张子帆
一代学者之学术研究,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应照这一时代特色。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步入了自晚清五四以降第二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时期,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席卷了整个思想与学术界。但正如言人人殊的“五四”一般,在思想史层面的“八十年代”也是一个复调的、多面向的概念。在“新启蒙”运动高歌猛进的同时,另一批学者则从传统的学术资源出发,通过点算清理中国传统学术的丰厚遗产,为回答80年代的时代之问——“中国文化的未来向何处去”做出了不同层面与角度的解答。
80年代的南京大学便是后者的代表。自民国以来,中国学界就有着“学分南北”之说。不同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派“能疑古”的风格,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派则具有“勤苦”的治学特色。正是南派学人治学深厚的功底,以及对传统学术的“温情与敬意”,为南大在80年代世风与学风的席卷下坚守自身的特色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南大学人在匡亚明的组织下,编撰了《中国思想家评传》大型丛书,这部书意在重评学术史,估价古典学术中那些极为重要且关键的演进脉络。在这套丛书中,由李开教授撰写的《戴震评传》与《惠栋评传》是两部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纵观整个清代学术史,惠栋与戴震共同构成了乾嘉学派的双峰,是帝制晚期的中国在传统学术上的开疆拓土者。在治学风格上,惠、戴二人分属吴、皖两派,吴派重材料,皖派重阐发。李开教授在为二人立传的同时,亦吸收了二人的治学特色,将二家之长融为一体,形成了材料与阐发并重的风格。
作为李开教授弟子的顾涛,在学术研究上亦承接了这种二家并重的风格。这就表现在顾涛不仅注重符合经学研究核心旨趣的文字校勘与文献考据,更是在经义、故训、制度、天文地理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观照整体经学史的大历史观。合观《耕读经史》(凤凰出版社)《礼学翠微:由小学通往经学史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二书所收论文,起于2000年,至于2022年,前后二十余年,其畛域约不出章太炎所谓“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之范畴。于今而视之,确如度寸之良珠、光莹凌然其百仞之水上。其治学的特色凸显了根柢与融通。小学乃治学之根柢,由小学入经史地理之学,是谓有根柢。文字有古今,语言有南北,制度有因革,其学不拘泥于一时一地,是谓能融通。
整体上来看,顾涛的经学、小学文献研究,带有强烈的章黄学术风格。南京是章黄学派的重镇之一,即如顾涛所言“黄侃在南京学统的传承者,当以洪诚、徐复二先生最为贴切”,洪诚先生任教南京大学,为训诂学大家,而又兼通礼学,顾涛的小学研究风格承继洪诚先生所秉持的学术风格。洪诚先生之训诂学,其一大特色是基于经传材料,重在词义与语法,故而特重词性、文法分析,淹贯以声韵,而最终落脚于经籍文义。顾涛关于“伊”字词义演变的探讨就注重词义基础之上的句法功能,依照词在句法中的分布位置和语义关系进行词类区分。
更能凸显顾涛这种由勤苦之学转至会通之学特点的,当属其对于《尚书·禹贡》篇的研究。中国古典学术向重系统与条理。“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是王道治政之谓也。《禹贡》是研究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不仅记载了大禹平治水土的功绩,并且还详尽列举了九州的山林川泽、风土方物等地理概况。正因《禹贡》山川地名涉及范围之驳杂,自两汉以来训读便渐生分歧。有鉴于此,顾涛在黄侃《禹贡地名啧隐表》设想的基础上,撰写了《〈禹贡〉地理条列啧隐》一文,“以水行脉络为主线,山行与水行相表里,州际地理附骥参照以见首尾,而将禹治水回巡之路线一并抽出以系联奠尾,俾观九州水系之大势。”应当说,顾涛对《禹贡》地理条列的“考镜源流”是非常成功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将历代学者对于《禹贡》文字的训读分歧收归为一,更让《禹贡》的文字转化成一幅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古舆图,使文字考据有了历史现场的真实感。
若兖州属《禹贡》所划定的“九州”之一,“地处黄河下游,在东河与济水之间,西北至黄河,南至济水,东临海,涵今河北南半部、天津以及河南东北部、山东北部与西部。”从字形上来看,“兖(八)”字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训作“山间陷泥地”,今作从口从八。“口”是山谷,“八”象水败之形,这就有了水沿着山谷顺流而下的意思。这种地形多水,且水上有土,是沼泽地。从谶纬来看,《艺文类聚》卷六引《春秋元命包》曰:“五星流为兖州。兖之言端也。言堤精端,故其气纤杀。”在这里,“端”侧重的是“开始”之意,突出兖水水系在古兖州段地域的地势问题;“堤”乃堤坝,就是水系由上游婉转而来,对于山谷山间地貌的一种描述;“精”则是对水系包含着上中游而来的云雾蒸腾,以及百草谷物繁育的描绘。这种关于兖的意含发挥,是建立在早期地形地势及生态环境的大致描摹之上的。在体国经野的古天文、地理学中,北斗星是一个中介星。司马迁《天官书》继承《吕氏春秋》对分野系统的认知,认为角、亢、氐,为兖州。北斗与四季的关系,斗柄运转,体现春夏秋冬之规律。兖水,属于季风气候区,又是上游山川来水,故一定是季节性水域,这就是其所谓来水规律有信。一方面,信,从人,从言。兖与之古音相近,声训可得。另一方面,山间陷泥地,来水必有时节,季节性雨量,时节至而雨水至,故而有征信之义。由此观之,不论是从训诂的角度分析,抑或是从义理的层面阐发,说明的道理是相通的。
顾涛治学的根柢与融通不仅表现于文字校勘与文献考据中,其对于经学史研究范式的整体思考也体现出这一治学特点。顾涛的这一思考,是由“新经学”到“活经学”铺展开来的,从顾涛而言,当于其进入南北朝义疏进而检讨经学史之必然。顾涛认为,在经学史研究中,学人应回归长时段、大问题的研究,扭转以往经学史的书写模式,从而建立一种通经致用之“活经学”的研究范式。
有必要上溯至百余年前“经学时代”的结束与“后经学时代”的开端。清末民初,随着“经学时代”的结束,经学学科被文史哲诸科肢解,成为被安置在博物馆中供人参观的“国故”,取而代之的是“后经学时代”中经学史研究的兴起。在这个典范转移的过程中,由于经学史的研究无可避免地涉及文献考据的工作,因而经学史与文献学的关系便逐渐接近,而同历史学的关系则逐渐疏远。可以说,在步入“后经学时代”之初,经学史的学科任务虽然是研究“经学的历史”;但客观地讲,对经学史料的考据成为学者的主要工作,经学史的研究往往停留在了历史文献学的层面。
所谓“新经学”,与梁启超在论述清代学术史中提出的“以复古为解放”相仿,是对“后经学时代”经学史研究中的陈旧方法和观点的一次全方位的“反动”,是经学史研究返本开新的必然过程。具体而言,在“后经学时代”,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经学史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接受“新史学”观念的学者成为经学史研究的主力,由于他们跳脱了传统经学自身的束缚,因而经学史的研究较传统社会的经学研究而言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以往经学史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文献学层面,追求的目标常止步于考据本身,常采用一种历史文献学式的研究路径。而很少有研究能更进一步,在考据的基础上发掘经学史“历史”的面向,以整体的、长时段的总体史研究方法去还原经学的整体发展历程。从而导致在目前经学史的研究中,“对经书义蕴与现实制度之间关系的认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断裂状态,研究至今较为空白”的状况。
由章太炎到刘师培,构成了“经学时代”结束、经学瓦解到“后经学时代”开始、经学史发端的一条学术脉络。顾涛发掘出的这条学术史脉络,是站在长时段经学史的整体视角下,基于对前人学说的修正而形成的,是“新经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如何构建这种长时段的经学史研究? 如何使经学史研究真正步入“新经学”“活经学”时代? 顾涛认为对传统经学文本蕴含的礼乐实践的解读,是解答这些问题的答案。“礼者履也”,礼学作为传统经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理解经学原理的必经之路,因而也应当成为经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礼学的研究不只能停留在对各项具体礼仪制度的考据,更应将其放在礼制实践的背景下来看待。经学史的书写只有包含了礼乐实践的主题,经书义蕴与现实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得以凸显,经学史的研究才能真正步入“新经学”时代。
正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经学史的文献学化虽是顾涛所反对的,但这绝非是要脱离文本而另起炉灶,相反,文献考据仍然是“新经学”的基础性工作。在顾涛的学术体系中,对礼乐实践的系统考察是使经学史研究步入“新经学”时代的关键,但“新经学”研究绝非要与文献考据截然二分。从近现代历史学发展的整体视角来看,过分强调“史学即史料学”的研究范式固然导致了史学变为“支离事业”,但倘若完全脱离文献考据,强行以己意阐发历史则又会让史学成为“易简功夫”,对史学的危害较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顾涛的礼学研究首先是建立在对礼学文本的详尽考据之上的,特别是通过对《仪礼》异文的研究,使其对礼乐实践的整体把握有了坚实的基础;而对礼乐实践的整体研究,则使顾涛的经学史研究较前人而言有了系统性的推进。
百余年前,面对学术界“学分南北”的状况,胡适曾预言“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功夫”。如果跳出民国学术的视野,将胡适这段话置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下去理解,那么顾涛的学术无疑具备了上述特点。从治学特色上来看,顾涛深厚的小学、经学与史学根柢代表了一名学者的“勤学功夫”;在经学史、礼制史研究范式日渐固化的同时,顾涛希望打通学问之后壁,将文史哲诸科之长融会贯通的“活经学”倡议则预示了经学史与制度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因而是一篇具有“疑古精神”的学术宣言书。
这种“疑古精神”,不仅是对史料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能以一种多识之眼光和新知之精神进行考证研究;还表现在驾驭史料、贯通历史发展关节的能力上。近年来,顾涛推出的《礼制与边疆:〈通典〉与中国制度传统》《礼治三千年: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当是这一学术理路的发展演进。“礼者,治辩之极”。这实质上是建立在超越性之上的对矛盾辩证发展之把握。是能对矛盾发展的趋势具有远见卓识的辨析能力,并能够认识到这种努力需要在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中予以克服前进。承认长期性、复杂性,是具有超越性之前提。这或许是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故事的意义。汉唐之盛,非独见诸于学,尤著于兵政礼乐之制之建设务实之中。治事之行之有效,在于条贯以经学之义,二者相辅相成。天下沿流溯源,历时久而曲折多,若不能推原省括,执因求果,其利害蕃变,必纷繁不可究诘。若如此,率由旧章或非、求新立异愈误。若为学治事二途合辙,则尤见典章制度与经学研究之活力。顾涛自身学术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疑古精神”与“勤学功夫”的贯通,治学的根柢与融汇,亦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史学家的严肃思考。
审近以知远。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具体时段的“八十年代”早已步入历史,但“八十年代”所聚焦“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于今日而言,也即如何把握学术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发展路向,以探求学术发展的未来动向,从而真正预时代之流,却仍旧期待着学术界更有力度、更具气度的回答。
(作者单位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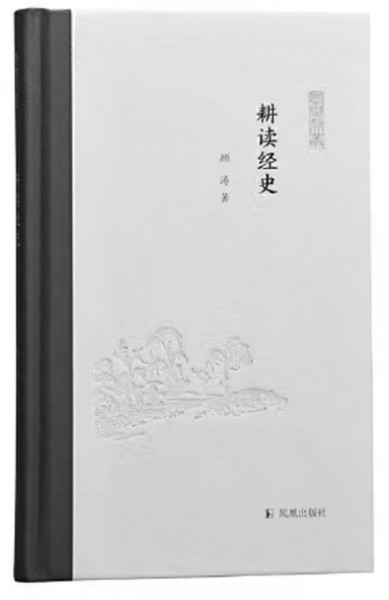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