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灏
在中国,太少人知道保罗·法默及其做过的事情,实在是太过于可惜了。
保罗· 法默的完整故事可以在普利策奖得主特雷西·基德尔为其所作的传记《越过一山,又是一山》(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中读到。保罗·法默在其所著《当代瘟疫:传染病与不平等》(姚灏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4年11月 出版)的第一章里也回顾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当然,我自己作为医生,对于他人生轨迹的回溯难免会拿我们这样的普通医生的人生轨迹作为比照,总想着见贤思齐,看看他到底哪里异于常人,又是在怎样的人生节点上走上了少有人走的路。
法默本科在杜克大学念医学人类学,当时他就开始在海地的医院做志愿者,因此也目睹了海地糟糕的卫生状况与医疗条件,目睹了海地的政治动荡、殖民遗产、跨国流动与社会不公,以及它们对海地人民的健康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后来,法默到哈佛大学攻读医学博士—人类学博士双学位项目,因为他一方面想要对海地人民所经历的苦难进行更加批判性且系统性的思考(由人类学提供),另一方面又不想对这些苦难无动于衷(由临床医学提供)。
也正是在哈佛念博士的这段时间,法默认识了金镛和奥菲莉亚·达尔,同时也认识了波士顿慈善家汤姆·怀特,并由后者出资共同创立了后来享誉世界的“健康伙伴”组织。这家组织及其姊妹组织在海地、秘鲁、卢旺达等很多国家建立了多家医院,也启动了大量公共健康照护项目,旨在为海地及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人民——尤其是穷人——带去高质量的医疗照护与公共卫生服务,改善他们的健康结局。
当然,法默在从事医疗服务的同时,作为人类学者,也在不断思考贫穷及其他社会不平等因素给海地这样的国家或地区所带来的健康影响:为什么有些人群会比其他人群更容易罹病? 为什么有些人群在罹病后会比其他人群面临更差的健康结局? 并对国际主流观念及公共卫生实践——以成本有效性为理由倡导预防的优先级应高于治疗,投资应更多地流向预防而非治疗——进行批判性省思。在那些“临床荒漠”,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地方,治疗需求是显著且迫切的。当然,法默在这本书里也大量批判了当时的人类学学者及主流媒体在分析不同人群的健康差距时“将文化差异与结构性暴力混为一谈”的做法,后者往往习惯将健康差距归因于他者的文化陋习,却忽视了更加宏观的社会性力量(法默称之为“结构性暴力”)对于人群健康的影响。
也就是这样,法默走上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他成了一名医生、人类学学者、公共卫生实践者。
作为一名医生,他并不满足于安稳的中产阶级生活,而是将自己大半的时间贡献给了为贫病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人道主义事业。
作为一名人类学学者,他并不满足于枯坐书斋写漂亮的民族志,而是直接介入健康照护的不完美现实,永远与他的研究对象同在,做他们的服务者与倡权者;他并不满足于对他的研究对象进行文化层面的诠释,而是以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学的眼光去揭露导致健康差距的结构性暴力;他也并不满足于人类学者所擅长的社会分析,而是对自然科学有着终生的好奇,并试图弥合生物学视角与社会学视角之间的裂痕,与他在哈佛的同道共同倡导“生物—社会”的分析取径。
作为一名公共卫生实践者,他并不满足于只是进行卫生服务的递送,而同样会对影响服务递送的结构性因素进行历史的、批判的、动态的、系统的检视,更重要的是不落卫生发展主流话语(如本书重点批判的“成本有效性”)的窠臼,而是谦逊地扎根地方世界,切实地回应地方需求。
对法默来说,这些不同的身份并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地组合成了一个整体。临床医学为法默提供了微观的视角与在微观层面行动的工具,法默可以在切身的临床工作中去聆听患者的故事,并为患者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人类学则进一步为法默的临床聆听提供了更为严谨的方法论,不再只是关注患者的病史,而是将病史放回到患者的生命史及更宏大的社会史中去加以检视,从而使得法默能够跳脱出有时可能过于狭隘的临床框架,以更加宏观的系统视角去省思不同层面的健康照护实践,看到周围,也看到过去。但止于省思——法默显然认为——是不够的,公共卫生实践则为法默提供了在系统层面进行变革的工具。
因此,法默既有了在微观层面重思与行动的工具,又有了在系统层面重思与行动的工具。法默是在做一名真正的“穷人的自然代理人”。他的临床工作也好,田野研究也好,公共卫生实践也好,焦点是明确的,就是要实现人人享有最高质量的健康照护的目标,哪怕是资源最匮乏地区的资源最匮乏之人也平等地享有健康照护的权利。就像那部有关他的纪录片——《弯曲弧线》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他的所有努力都是在为了让健康照护的弧线能够弯向公平与正义的一边。
其实,所有从事社会医学研究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疾病是沿着社会经济梯度(或者用法默的话说就是“社会的断层线”)进行分布的,社会经济地位更低的人群总是面临着更大的疾病负担与更差的治疗结局,从而在不同人群之间制造出健康不平等的鸿沟。而且,正如理查德·威金森、凯特·皮克特在《公平之怒》(新星出 版社2017年9月 出版)里所说明的,不只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会导致更多的疾病,社会经济不平等会给所有人群(无论其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健康都带来显著的影响,无人能够幸免。当然,相比富人,穷人总是背负了更多。
也许,许多医生会说,自己对所有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是一视同仁的,这既是医学伦理所要求的,我想也是许多医生正在做的。然而,许多研究却已经表明,作为医生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只决定了人群健康的10%,起到更大作用的是那些所谓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包括性别、收入、种族、职业、环境、住房、教育、行为,也包括更加宏观的卫生及社会政策与体系。这些因素可能会直接地影响人群的健康,也可能会间接地通过影响照护服务可及性与质量从而影响人群的健康。因此,穷人往往不只是背负了更多的疾病,同时也面临着服务可及性与质量方面的不平等,正如法默在本书里反复讲述的那样。他们在罹病以后很有可能就没有机会得到任何的照护服务,所以根本就不会来找医生寻求帮助,即便最终找到了医生,可能也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出现了许多并发症与合并症。
“挑病人”是世界上许多医疗文化里都存在的“风俗”,尤其是在那些诊疗量很大的医院里。床位总是有限的,哪些人会得到优先安排,哪些人则只能继续等待,所有医生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这门或者可以戏谑地称为“患者质量评定”的隐形课程的学习过程。医生会基于某些因素来评定患者的质量,包括患者是否“干净”(也就是说在主要诊断之外是否还存在很多并发症与合并症,如果并发症与合并症太多,那就不“干净”)、患者的经济条件是否允许、患者是否容易沟通、患者的依从性是不是好、患者有怎样的社会地位等因素,在美国的语境下可能还要加入种族、医保等变量,而在中国的语境下则可能要加入家属、“关系”等变量。基于这些因素,医生会决定(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无意为之)哪些患者质量比较高,因此可以优先收治,而那些质量很差的患者则可能就会被“弃置”在像是急诊室这样的地方,名义上说是在那里“等床位”,但他们可能在某份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等候清单上永远都排在末位。我们自然无法对“坏病人”与“好病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统计,但倘使要统计的话,那么前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许很大概率是要显著低于后者的。
我至今仍旧深刻地记得去年在急诊抢救室轮转时所见到的那一张张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当时,有一位晚期肺癌的患者,肿瘤已经全身转移,恶病质非常厉害,骨瘦如柴,白蛋白和血色素都已经很低,家属把他送到医院想要寻求最后的治疗,但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又是外地患者,没有本地医保。作为医生,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这样的患者是不大可能会被收治入院的,所以就只好留在抢救室里接受所谓的“姑息治疗”,但抢救室所能提供的“姑息治疗”也就是对症处理处理罢了。
关于这个例子,自然可以提出许多的问题,包括:患者自决的问题、过度治疗的问题、协助死亡的问题,其中每个问题都可以写成独立的民族志。这样的例子在抢救室里并不少见。这些患者的面孔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因为我似乎没有必要——更没有时间——去了解他们的人生;可是,他们的面孔对我来说又是如此地熟悉,因为他们似乎都有着相似的特征:疾病晚期、合并症多、并发症多、实验室指标“七上八下”,更重要的是他们似乎都有着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做到了自己所说的“一视同仁”? 可是,这样的归罪又是合理的吗? 正如我曾经写过的,医生与患者同样都在现代医疗体系“这只更大的怪兽的腹中瑟瑟发抖”。如果无法批判性地、系统性地去分析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互动,那么就可能会做出——用法默的话说——“不恰当的因果论断”,从而将问题归咎于所谓的“医德医风”,却罔顾由更为宏观的结构性困境所造成的防御性反应。
实际上,小小的急诊大厅里往往会塞进远大于核定容量的病人,病情又都比较复杂,而医护人员的资源配置又很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所能够提供的照护质量的均值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决定了。但是,如果拉远镜头,重新对焦医院或城市,我们还是会发现,似乎有只无形的手在决定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在罹病后的不同去向——究竟哪些人可以住进病房,而哪些人又只能留在急诊大厅里,病情永远都不是唯一的变量。
此外,我们作为医生似乎也忘记了那些虽然罹病却得不到医院照护的人们。法默在这本书里讲述了太多这样的故事,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得到医院照护,而是成了某种形式的“裸命”被“弃置”在所谓的“临床荒漠”之中。现代的医生已经大体上成了医院的雇员,我们的医学也已经大体上成了医院医学的代名词或缩略词。顾好自己医院里的病人——对于许多资源欠发达地区的医生来说——已经是沉重的负担,又如何能够要求他们付出更多? 如此想来,法默在波士顿工作的同时能够兼顾海地及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医疗援助工作,除了他自己不可否认的毅力之外,是否也代表了他作为波士顿地区白人男性医生群体代表所能享受到的许多“特权”呢?
法默对此有着深刻的自省。法默在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享有“特权”的同时并没有浪费掉这些似乎已经无法被撤销的“特权”,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或许可以成为输送资源的管道,这些管道里装着一些单向阀门,从而可以让资源逆潮流而动,重新回到我们所研究的那些贫困社区。”如果我们享有了更多的“特权”,那我们是否也享有了更多的赋权于无权者的“特权”?那么,这是否就是我们的使命所在呢?
“人人享有健康照护”是长期以来全球卫生领域的口号之一。但是,这一理想却还远远没有照进现实。而且,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变革,健康照护的不平等还在不断加剧,正日益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主 要特征。健康照护应该成为基本人权——关于健康照护的讨论,如果缺少了公平与正义的部分,那么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的目 标是提高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那么就应该摆脱医院医学的狭隘框架,去实现医学的再脉络化与再社会化,去省思健康照护的不平等及其社会动因,去服务那些需要照护却又得不到高质量有尊严的健康照护的人。如果我们同意,所有人的生命价值都同等地重要,那么,健康照护的弧线就应该永远地弯向公平与正义的一边。
在我翻译这本书最末几章的时候,法默不幸在卢旺达猝然离世,这位“治愈世界的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法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个人的人生观,谨以此文缅怀法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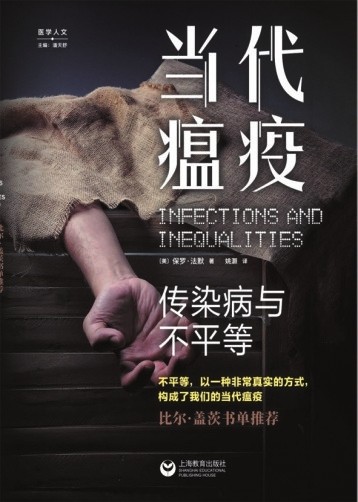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