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绚隆
我和玉亮是曾经的同行,又是曾经的同事。细数起来,同行的 时间较长,同事的时间则很短。从认识到现在,我们的交往只停留在工作层面,没有更深的交流,以至于我对他的过去几乎完全不了解——只知道他最早在巴蜀书社工作过。但玉亮做事认真、待人热诚,倒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以貌取人”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它几乎是“有眼无珠”的同义语。读了《纸背藏身》的稿子,我发现对玉亮,就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但这不能完全怪我,是他的外貌骗了我。他身材清瘦,皮肤白净,说话嗓音清亮,总是满脸阳光的样子,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新人。当看到他在《自序》里说从2005年进入出版社,已经做了20年编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糊涂。
认识玉亮是在2018年,当时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那段时间,我们先后组织出版了任笃行先生《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的修订本、赵伯陶先生新著的《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加上早先出版的《全本详注聊斋志异》,基本把市面上最好的三个《聊斋》整理本都集中到了文学社。为了宣传这件事,我在微信圈里发了条消息,介绍了我们针对经典名著,按照不同需求打造版本集群的出版思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主编杨牧之先生看到这个消息,约我以此为题写了篇稿子,刊物方面具体负责对接的就是玉亮。记得我们刚建立微信联系不久,他就到过一次文学社,是去古典部会朋友的。我在文学社的办公室,与古典部有个屋子连着,中间还通一道门,那门总开着,这样就见到了玉亮。他那充满阳光的笑脸,从那时就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2020年底组织调我到中华书局任总编辑,和玉亮成了同事。初来乍到,我要尽快熟悉书局的情况,整天忙于同各部门谈话调研,查阅分析各项经营和管理数据,几乎无暇他顾。玉亮虽然此前就认识,但我不找他,他从未主动找过我。来我办公室时,也总是笑呵呵的,谈完正事就走,从来不多说什么。2022年我正式担任中华书局的执行董事兼党委书记,主持举办了书局成立110周年庆典。那次活动规模较大,在策展过程中,玉亮出力极多,好多文案都出自他手,他对中华局史的熟悉,令我印象深刻。
玉亮这些年深研近代文献,先后整理了多种集子,尤其在谭嗣同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这些,我都是在微信圈里注意到的。他平时在单位闷声不响,但在微信圈里却很活跃。谭嗣同的《仁学》我早年就读过,看到玉亮整理了新的版本,就跟他讨了一套。书送到办公室,也没讲太多的话,只是很矜持地笑着对我说:“我以为您不会感兴趣呢。”除了做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还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原则,沿着谭嗣同的足迹去甘肃等地考察。去年国庆期间,忽然接到他的微信,居然都跑到了我的老家庆阳了。
玉亮最初在中华书局的古代史、近代史编辑部做图书编辑,2018年开始负责《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中国出版史研究》不是所谓的C刊,发行量也不大,组稿、经营都面临很大压力,他在微信朋友圈中有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表达,我那时还未到中华,隔岸观火地给他说过些鼓励的话。他为了工作方便,建了个“《中国出版史研究》作者群”,我很荣幸地被拉进了群里。2023年4月,我辞去中华的行政职务,调入清华工作。离职前,退出了过去所有的工作群,却赖在他那个群里没走。记得去年某个时候,他在群里特别解释,自己原则上不请在职的中华同事进这个群,因为我是调到中华前进的群,到了中华他也没好意思给我请出去。他自称是“见官躲”,用他的话说:“最怕官提携,何劳官指引。捉将官里去,头皮今亦紧。”(《儿童节偶题》)据我观察,他说的是实情。如今看来,对我这个曾经的“官”,他那是相当客气了。
《纸背藏身》记录了一个有情怀、善动脑子、肯下功夫的编辑,一步步扎实走来的足印。书中的文章,基本都是围绕作者的日常工作产生的。有的回顾自己过往的经历,有的是对编辑经验的总结,有的谈读书中发现的问题,还有些是学术研究的心得。尤其令我没想到的是,他的旧体诗词写得如此之好。玉亮非传统以文史见长的高校出身,能在文史领域有这样的建树,除了兴趣和努力外,恐怕没有别的诀窍。
凭着过去留给我的印象,如今再读他的文字,我深感玉亮是真诚、善良又富激情的人。以他“不信情怀尤自缚,还将肝胆对人倾”(《当年》)、“寒花自傲朱颜暮,出处吾心了不疑”(《丁酉冬至感事集默存句答友人八章》)的诚挚与清高,工作中应该遇到过一些很不开心的事。他虽然对我只字未提,但从其诗作中还是能窥见一些影子:“当面高情背后刀,报销三士有双桃。”“蜗角微名非我愿,随人唤马又呼牛。”(《感事三章》)“瘦任到骨足蚊粮,目语心声两渺茫。”“一流顿尽惊身在,百忍相安亦大难。”(《丁酉冬至……》)相信人们读了这些诗应该能认同我的判断。在这一点上,我跟玉亮其实是有共鸣的。他日有暇,我也希望能对自己过往的经历做点回顾。
《纸背藏身》涉及学术、编辑与阅读等多个方面,我无法对其内容一一评价,倒是对其中一个话题,有些自己的看法。玉亮在《自序》中说:“我所在的中华书局是一个历史悠久、名家辈出的老牌出版机构,许多为人称道的学者型编辑至今仍是学林佳话。……而我在中华的十几年,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所谓‘学者型编辑’境遇的变化,这种变化令我困惑。”这种困惑其实代表了所有对学术有热情的人,进入出版业后内心的纠结,想当初我也有过。记得中华有个应届毕业新入职的编辑,工作半年后,在个人的年终总结中发出了一句灵魂拷问:“我服务学术的初心到底该怎样实现呢?”看到这话,我曾心头一震,既感动于她的真诚和单纯,也为没及时关心他们的成长而心存歉意,于是赶紧约她谈了一次,希望帮她解开心结。
以我的理解,所谓“学者型编辑”,几乎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出版业特有的现象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重新布局,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化人进入出版社做编辑,他们凭着自身的专业素养,既为出版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又坚持着个人的研究和写作。此风延续到本世纪初,仍有一批编辑活跃于学术领域。后来随着出版单位改制上市,对码洋、利润的增长有了严格的要求,指标压力干扰编辑的学术成长,于是就出现了玉亮所感慨的一幕:“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和专业分工细化,编辑与学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学者型编辑’一度被明确为不再需要,早先那些前辈的成长环境也已不再。”应该说,从历史上看,并不是编辑工作成就了这些学者,而是这些编辑本身就是学者。所谓学者压根儿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如今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在学术机构工作的未必都是学者,在机构外坚持学术追求的也未必不是学者。我认为玉亮自身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完全可以不必为此而困惑。
学术在本质上是无功利的,但如今的学界,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可谓乱象纷呈,不在这个圈子里,倒可以避免量化考核带来的许多烦恼,对有心学术的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好事。职业和爱好一致,固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过度内卷的学术圈,其实已成了很多“青椒”的噩梦。我认为,所谓“学者型编辑”,并没有哪个是靠人为培养出来的。凡是心怀学术理想,工作中脚踏实地,勤于思考、喜欢动笔的编辑,就一定会成为学者型编辑。玉亮已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他以“书奴”自居,将自 己的视频号命名为“手民老张”,都表明了他对编辑工作的热爱;给本书取名“纸背藏身”,则是对甘做书籍生产幕后英雄的形象化表达。而《纸背藏身》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他在工作过程中,围绕自己所编辑的书稿,进一步思考探究的结晶。
拜读玉亮的书稿,使我对这位曾经的同事增加了了解,既有遗憾,也有欣慰。遗憾的是当时没与他有过深度交流,错失了大好时机;欣慰的是在这个浮华的时代,他让我确信还是有人在为理想而坚持。用他的话说:“幸有砚田供傲啸,江湖满地一书奴。”(《书奴》)这种无怨无悔的精神,是我们生而为人最为珍贵的东西。写下这点文字,聊表我对他的祝贺,也期待他下一部著作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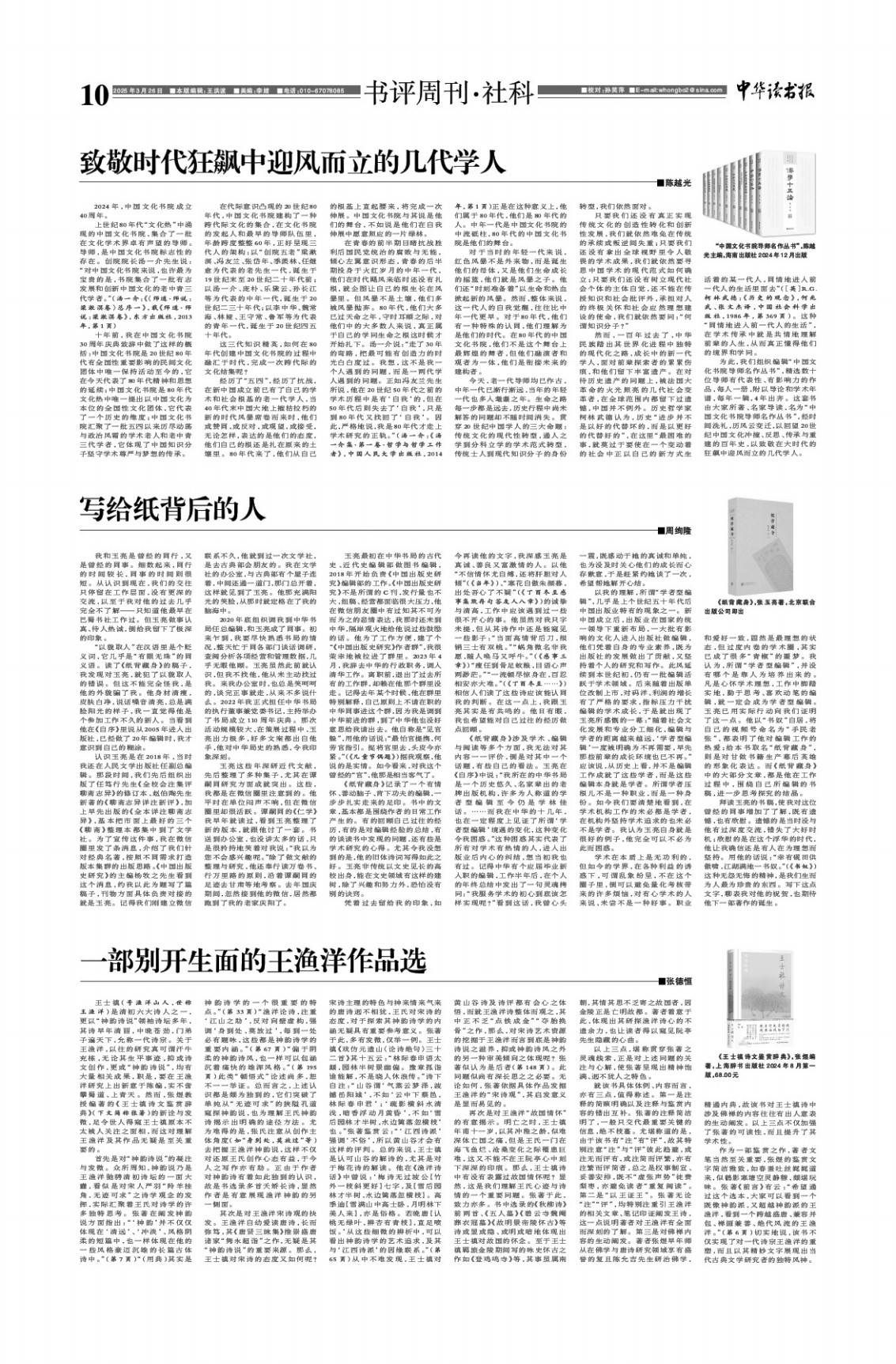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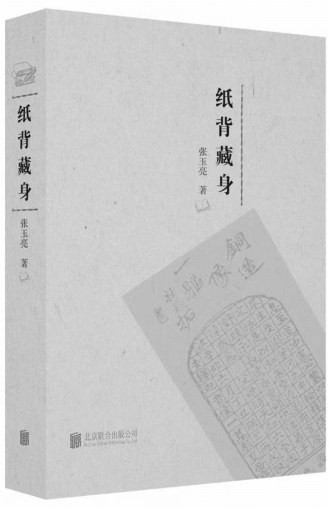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