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士颖
“精神”以其内容丰富、外延宽广而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在当代西方的精神史研究者那里,“人们精神世界的东西”包括“意识形态、想象、神话、思想、概念、习惯、礼仪、信仰、梦幻、时尚等等”(参见孙有中:《当代西方精神史研究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更早期的俄国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则强调精神的主体性,直接否定了定义“精神”的可能性,认为“精神将被这样的定义给窒息”(参见[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精神与实在》,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精神的特殊性使得当下中国的精神史研究多着眼于精神世界的呈现或对精神品质的艺术烘托,很难系统地将精神视作研究对象来进行理性讨论。许纪霖教授的《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以下称《前浪后浪》)一书,既是他耕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四十年之后以精神史视角重访该领域重大议题的尝试,也是构想并实践精神史研究的范式探索。作者试图通过具体历史语境的还原,将别尔嘉耶夫视为不可定义的“精神”转化为可分析的历史对象,不能不说是在进行一场令人心悸的“知识探险”(语出序言第2页)。
《前浪后浪》作为“知识探险”自有其别开生面的开拓意义,但是细究文章的思想资源与论述逻辑,得见作者治学工夫的自然延展和研究思路的前后贯通。
作者将19世纪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狄尔泰注重生命体验的人文精神引入知识分子研究,颇具新意。狄尔泰关注人的生命存在如何同结构的、历史的情境产生互动以及个体在此过程中获得的内在体验。狄尔泰认为“每个时代有其独特的生活世界和心理结构”,落实到具体研究中,狄尔泰的历史哲学表现为对研究对象“生命历程”和“历史语境”的关注,学者要“还原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价值观和意义结构”,也即是《前浪后浪》中所致力勾勒的“精神世界”(第6页)。除此之外,作者曾长期受益于思想史名家张灏先生的研究路径:“把他(对研究对象——引者)的思想放在他的时代脉络里去看,看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刺激和生命的感受,如何在思想上作自觉的反应。”(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4页)狄尔泰与张灏,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学者的思想资源,在作者的精神史中被有机地融为一体。作者以“鸟瞰近代知识分子的整体世界”为行文要旨,对个体与所处时代的关联性进行贯通考察,将独立的人置于广大的社会结构与时势背景中进行讨论,揭示出个体经验同生活世界的复杂联系。
《前浪后浪》一书的问题意识也同样显露了“知识探险”背后深层的、持续的核心关切——对“启蒙”的多维阐释。“启蒙”是作者最为关切的问题,他曾先后出版过《启蒙的自我瓦解》《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等思想史专著。相较于前著对思想论争与观念流变的刻画,《前浪后浪》以精神史的角度书写晚清至“一二·九”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迭代与分化,是对既有“启蒙”叙事的解构与再建:启蒙的理性气质不再成为度量的标准,而看似不相协调的情感、品味、审美与驳杂异趣的众生相成为叙述的中心。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在作者个人的学术脉络中,既是“启蒙”现象在精神维度的拓展延伸,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次对“启蒙”的再反思。
《前浪后浪》发掘出历史研究中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并通过知识人代际群体的具体实践呈现出精神史研究的两重思路,概言之,包含着历史发展的精神逻辑考察与精神形成的内在结构分析两个既有紧密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方面。
精神逻辑体现在知识分子赓续的精神脉络以及精神对历史走向的现实影响。精神脉络是历史的“潜流”,通过追溯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渊源,作者得以重新解释五四后期知识分子的“内战”。“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两个知识群体的对立实则是二者精神气质之间的冲突,以竹林七贤为代表、风流倜傥任侠自由的“名士”鄙薄“道学家”的伪善与酸臭,而体制内严肃正经的“绅士”则自恃正统瞧不上体系外的“野狐禅”(第293页)。在对“学衡派”的研究中,作者认为他们的精神气质依然是士大夫的,恪守的是正统的理学传统,更趋向于审慎保守,因此难以为激进求新之世所容。历史发展的精神逻辑还体现在精神在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五四前后怀疑主义盛行,其引发的权威真空使得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具有虚无、苦闷、无意义感,对“信仰的主义”“确定性”产生了强烈的精神渴望。而马克思主义能够同时满足知识青年的认知需求和心灵信仰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走到了历史的台前。在建党以后,中国共产党以精神“父亲”的强大感召力迎合了知识青年“出走”以后的再嵌需要,其组织力与信仰力的“神魅性”,吸引大批追随者与拥护者“到延安去”,并由此构成了历史的先声。(见《前浪后浪》第六、九章)
精神形成的内在结构分析有别于历史发展层面精神逻辑的发掘,而是以精神为主体、结构化地分析精神的形塑因素,揭示出知识分子的精神既与个体所接受的思想学说有关,又深受公共空间文化气质的浸染。一方面,思想是个体对生命处境的回应,是个体内在世界的组成部分,因此作者对精神的考察格外重视精神与思想的互释。他擅长用学说的精神推演学人的气质,例如心学的浪漫主义、神秘主义就塑造了康有为激进大胆而敢于幻想的精神特质,而理学的经世面相逐渐衍生出李鸿章等人功利庸俗的文化性格,形成了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角力之势。另一方面,作者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分析个体精神如何在公共的语境中呈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场域”(field)与“文化惯习”(habitus)理论来建构宏观与微观的深层联系。“场域”指的是相对自 主的客观关系空间,“文化惯习”则是“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味、信仰和习惯的总和”,象征着集体的身份认同。(第291-292页)布迪厄的理论启发了作者从个体生存场域所内涵的精神趋向来解释个体差异化的精神品质与行为选择。例如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的风气差异,海外留学圈中哥伦比亚大学同哈佛大学的文化氛围区别,这些“场域”与“文化惯习”大有分殊,在此间涵泳的人格类型也就姿态各异。
作为一场“知识探险”,本书也有其“冒进”的不足之处与论述的单薄之处。作者对人物精神气质的作用偶有夸大,在论述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党时期的陈独秀时,作者分别以“一个领袖的气质决定了一场运动的性质”(第82页)和“一个政党的理论趋向和精神气质,取决于领袖”(第265页)起笔。领袖固然作为切入群体研究的“典范性人物”值得格外留意,但是将重大历史事件的众多精神面相辐辏于“关键人物”一身,论述逻辑就很难不带有些许唯精神论和英雄主义的嫌疑。另外,作者观察到了时人的“精神建构”现象,例如五四学生运动期间对自杀学生的形象矫饰、王国维成为“学衡派”同人的理想典范、时人对“志士精神”“五四精神”的提炼升华等,但是并未进行深入讨论。作者试图掀开“公共精神”的面纱,但却忽视了在精神意义上讨论事件或人物如何升格为符号的历史过程。
总而言之,《前浪后浪》作为一次可贵的“知识探险”,在学术意义上有三重突破。首先在知识分子研究领域,作者突破了将知识分子视作“理念人”的局限,发掘出人物内心世界中更为丰富、生动的精神底色,并以此为线索对相关历史事件与议题进行重新阐释,揭示出时代变迁中不为人知的面相与逻辑。其次,作为一项对精神史的研究,作者将难以定义的精神具体呈现为个体的性格气质、情感体验、思想倾向和由群体共享的时代精神、精神症候、典范人格等,确定了精神史研究的基本锚点,并通过研究实践开拓了新的议题和路径。最后,由于精神史同情感史、思想史的研究范畴有部分重叠,作者在书中对精神与情感、思想的关系做了精彩的论证。三者互为线索,成为将“人”的研究引入内在世界的观察视角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此《前浪后浪》也在问题和思路的交叉、融合上为不同方向的学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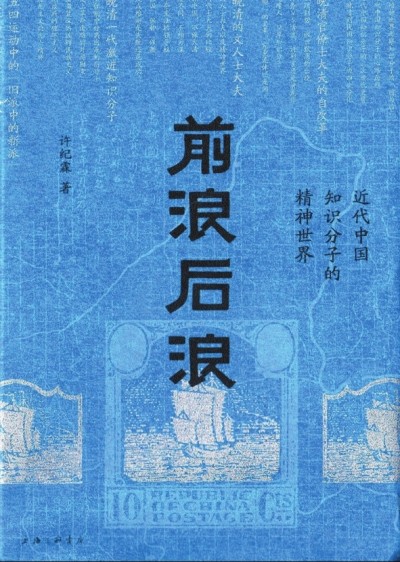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