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寅 黄志立
就我个人的文献使用经验而言,近代文献因其数量庞繁且多数尚未得到认真清理,考证的难度远甚于古代。倘要在近代的旧纸堆里旁搜资料,无异于大海捞针、沙中拣金,能否找到所需的文献,全靠辛苦和运气。因此,许多价值珍贵的史料也就难免恒久被埋没在馆阁深处,以至无人问津。顾亭林曾将自己撰著《日知录》的过程比作“采铜于山”,其实近代文献的考据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需反复寻究、苦苦思索、细细审视,才能在烟海浩卷中寻得些眉目。近年来学界对近代文献的整理工作鱼龙混杂,成果虽然层出不穷,但质量良莠不齐,大多成为申报项目或课题的脚注。最近看到闵定庆先生主编的《文廷式全集》,可谓在沉闷的学界炸响了一声惊雷。
我们与闵先生同事多年,对闵先生的治学之路有一定的了解。一方面,闵先生作为管林教授《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研究团队的成员,自入职之日始就专注于晚清旧体诗词研究,出版专著多种,发表论文50余篇,可谓斐然有成;另一方面,作为赣籍学人,他对自己的乡邦文献怀有浓烈的情感,正如《文廷式全集前言》中所言,他很早就萌发了收集研读乡邦文献的兴趣,渐渐形成了若干江西作家专题资料库,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在《文廷式全集》立项之前,他主持的《曾巩研究书系》就获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该系列对北宋赣籍大文豪曾巩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涵盖家世、诗文、文化思想、文献成就等多个领域。而在正式启动补遗校订《文廷式全集》的同时,闵先生还参编江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工程——《江右文库》。文库分为“书目编”“文献编”“方志编”“精华编”“研究编”五编,计划编纂出版1600册,总计约8亿字,是对秦汉以来至清末江西学者著述进行系统收集、整理、研究的大型丛书,是赓续赣鄱文脉,提振古今之江西文化自信的重大工程。
基础研究厚植学术根脉,而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走向纵深的重要路径。此次他领衔主编《文廷式全集》,既是对《江右文库》的承接,又是他幼闻庭训及其乡关情怀的具体表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蒙安平秋、许嘉璐、孙钦善、倪其心、杨忠诸先生信任,闵定庆教授先后参加《全宋诗》《二十四史今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重要文献编纂工作。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期间,又先后师从朱祖延、钱仲联、杨海明诸先生,接受了严格学术训练,对文献辑考逐步走向了自觉。岁月淹忽,三十年过去,闵先生为学界贡献的成果终于出版,个中艰辛唯有“采铜于山”者方能知晓。但先生平时常以乐观微笑的一面示人,于个人得失毫不介意。长期以来,我们因从事清代诗学的研究工作,对近代学术及诗词也粗有涉猎。就学术史的脉络来看,钱先生及其培养出的一批清诗研究者,贡献了新时期第一批清代文学和诗学研究成果,对学界的影响非常之大。闵定庆先生奋钱门余绪,笔耕不辍,细致绵密,并不求一时之快,而是饱经多年思索,循着中国学术研究传统表达方式,通过校雠学的方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选择具体的作家或经典文本,用注解、札记、校勘、评点等传统文本阐释和研究的路子一步步解决问题,不断深入,率领由兴趣组成的团队创造了能够泽被后世的名山事业,实在让人佩服。去年逢陈尚君先生《唐五代诗全编》著作发布,今又值闵先生《文廷式全集》付梓,实乃人生幸事。
盛世修史,资政弘文。我们应当对那些甘坐冷板凳,默默地做资料整理工作的学者保持特殊的尊敬,他们的精神才是学术的真正希望。而这种精神恰是当代学界相当缺乏的。时蒙闵先生新著惠赠,得有机会以小言詹詹,作简略述评。
基础研究是学术的立足之本,也是创新的思想之源。文献的搜集、整理、考据、笺注、校勘乃是文学研究的根基,此为学界共识,自不必多言。近百年以来,学界对文廷式文献编撰及其研究工作开展十分缓慢,缺乏爆发力和连贯性,其中颇为人称道的有胡先骕、龙榆生、钱仲联、赵铁寒和汪叔子等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对文廷式诗词进行搜集评述,并为其编订年谱,如胡先骕《评文芸阁〈云起轩词钞〉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学衡》1924年第27期)、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暨大文学院集刊》第一集,1931年1月)、钱仲联《文芸阁先生年谱》(《同声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1942年)。后期则是整理和校订作家文集,如赵铁寒《文芸阁(廷式)先生全集》(收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4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2018年新编增订本)、汪叔子《文廷式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陆有富主编《文廷式文献辑刊》(广陵书社2021年版)等。因时代关系,几代学人对文廷式相关文献的搜集不仅尚有可补正之处,而且有关文氏的诸多问题也未得到解决,因而使后来者的研究缺乏更加全面、权威的文献本体,造成文献考证与文学批评的相互割裂,只能将精力集中于“点”的研究,线和面的研究则无从谈起。
闵先生主编的《文廷式全集》恰好能解决上述问题,使文廷式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我们在粗浅翻略间,就已充分感知编著团队的用功之深、体例之细。文氏文集包括学术著作、奏章、诗文创作、书信、笔谈、日记、随笔札记、编目、评点、编译、抄纂等十余种,凡十册、六千余页、上百万字,如此庞杂的内容,编著团队皆附以校勘记、附录与按语。尤可称道的是,在以往整理的文氏文集中,均未见“拾补”“重校集评”“补遗”等内容,而《文廷式文集》中有《知过轩诗钞拾补》《重校集评云起轩词补遗》等,其中所付出的剔掘爬梳、勘误校订的艰辛,是不可计量的。真正做到了他文集有者,本文集则校订重评;他集无者,本文集则拾遗补阙:这是本文集最为出彩之处,亦是后出转精的体现。陆有富曾在《文廷式诗词研究》中提到由于材料的缺乏,对文氏诗词的解读研究尚存在一些误区,如今,随着闵先生团队对文氏日记、笔记等新材料的整理,学界研究的很多谬误也因之有了纠正的空间。
文集前言说,倘若研究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应该从最基本的文献工作做起,尽最大可能收集、整理研究对象的全部著作,将其作品编纂成作品集,再将研究对象的生平事迹、交友、著述等项一一编年,依自然时序,呈现其完整的人生;最后将他人的记述、评介、研究资料进行编目,形成一个较为完整且有序的资料库。三十多年来,编著者穷搜海内外有关文廷式的文献史料,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着上述宗旨,按照“知过轩诗钞”“知过轩诗钞拾补”“纯常子枝语”“重校集评云起轩词”“重校集评云起轩词拾补”“云起轩词拾补”“联语”“芳荪室律赋”“文录”“奏议”“书牍”的顺序,分门别类,有序编排。文廷式作为晚清重要的文人、学人,又是近代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亲历者,其著作之宏富,文学创作成就之高,史料价值之丰厚,与学界对其研究的低迷、漠视存在巨大的落差。将上述内容汇辑成集,不仅有助于重新衡量文廷式的文学价值、文学地位,而且为我们探究近代历史,触摸传统士人在近代化转型之中的心路历程,体验他们身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的微妙情感,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廷式文集的研究投入力度过少,遂难以还原这位在波诡云谲的末路王国中苦苦挣扎的文正君子的内心世界,亦难以厘清他在清代文学史、政治史、社会史中的地位。例如,文廷式的创作以本以诗歌见长,然而他的诗名长期为词名所掩,一是因其词学确实成就斐然,二是由于其诗集流传不广、散佚颇多,且诗风综杂众家、难寻门路,鲜有学人为其阐幽发覆。汪辟疆在《近代诗人小传稿》评道:“道希(文廷式)以文章气节负一时清望,长短句得苏辛之遗,诗则知者甚稀,实则追浣花,有《诸将》《咏古》之遗意。”由此可知,当时的评论家即对文氏之诗了解甚少,遑论对其诗作进行客观评价。文献的形成与整理,正是文学研究的方向所在。有此名山事业,后来之学人才得以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文献整理与文学批评、文本批评结合在一起,进而对文氏作品进行全面系统、客观公允的分析评价。
文献因流传而多彩,因互鉴而丰赡。诚然,闵先生的《文廷式全集》尚未臻于十全十美,但此集的完成度之高,已足以作为一个新的标杆,与其他文廷式相关文献进行交流与互鉴,进而为学界提供更加丰赡的研究成果。近代中国因饱受外敌入侵之苦,“词史”说盛行,不少文人主张“以史入词”“以词为史”,记录国家、民族的屈辱历史,供后代为鉴,文廷式亦不例外。诚如章士钊所言:“云起轩中寸寸愁,山河破碎不堪休。”其词集《云起轩词》便如实地反映了他深刻而痛苦的家国之情。钱仲联在《梦苕庵诗话》评文廷式词云:“萍乡文芸阁(廷式),以词名一代,其词气王神流,得稼轩之髓。于晚清王半塘、郑叔问、朱古微、况蕙风四家之外,别树一帜。”倘对其人不了解,做不到知人论世,则其词中那崇尚性情、师法苏辛、既雄浑又傲郁的情思就难以得知,对其词的研究也缺乏根基,流为无源之水。而《云起轩词》中常有化用楚辞的词句,或言及楚地风物,这自然也是对“骚怨”精神的发扬,以屈原之心为己心,倘不解其人,能得以知之乎?关于上述问题,《文廷式全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近距离接触文廷式其人、其文、其事、其思的门径。此集出版后,相信这位一生坎坷的文人能更多地进入学术群体的视野之中,诵其诗,读其书,且知其人,从而更有利于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地看待清季文学的演化。
潘耒在《日知录序》中曾写过这么一番话:“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闵先生对《文廷式全集》的思考与探索跨过了千禧年前后,而此书能留存的时间也定非一个千禧年能够概括,谨在此对闵先生团队为我们勾勒出宝山的轮廓致以诚挚的感谢与祝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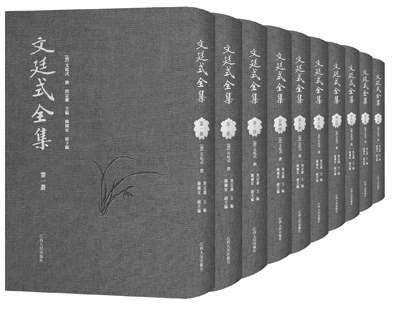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