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升
传统词谱发轫于明代,现存最早者应是弘治年间的《词学筌蹄》,此后各种词谱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当下对传统词谱的整理与研究如火如荼,已然构成词谱学一脉,但稍作反思就会发现,词谱学的研究路径是重文献轻理论,重描述轻解释,即便有理论研究,也多在阐释明人与清人的词体观念。这类研究不是没有价值,但无法揭示词调与词体、乐句与词句、律词与非律词之间的复杂关系,归根结底就是无法展现词体形式的构成历史。如何作出突破? 近读李昌集先生的《唐五代两宋词调体式源流谱》(下称《源流谱》),感觉这是一部回归历史原态的新型词谱,对当下的词谱学研究颇有启发意义。
一
明清两代编纂词谱是为作者提供样板,故而实用性大于学术性;但当现代人将词体视为欣赏和研究的对象时,传统词谱就无法满足相关要求了。
在学术层面,传统词谱无法展现词体形式的构成历史。清初《钦定词谱》提出“必以创始之人所作本词为正体”的思路,倒是可以呈现词体形式的演进轨迹,可惜编者没有严格贯彻。像《洞仙歌》一调,《钦定词谱》以苏轼“冰肌玉骨”一阕为正体,事实上今存此调的最早作品见于敦煌写本歌辞,清人可能不知;但苏轼的前辈词人欧阳修有两首《洞仙歌》,编者不会不知。不立欧词却立苏词为正体,实乃自乱体例,令人无法看清《洞仙歌》一调的演进过程。
在欣赏层面,传统词谱的断句有时会割裂词意。早先词谱不标句读,后来渐以“韵”“句”“豆”来标示韵位和停顿,今人习惯用句号、逗号、顿号来对应。但像“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这样句句押韵的词,是否每句都打句号呢?《源流谱》认为不妥,因为这样会影响对词意层次结构的理解。再如张孝祥《拾翠羽》中“想千岁、楚人遗俗”一句,传统词谱于“岁”后停顿,《源流谱》提出:这是以“想”领起的七言句,当中停顿不仅句意不通,而且破坏了“一字领”的句式。
针对这些问题,《源流谱》取消了“正体”一说,代之以“始词”概念,即每一调的初始作品;再以分句数、复句数、复句型的差异来作变体的区分;始词与三类变体的首作都标平仄,同体式作品则出示词人姓名和作品数,并按词人先后排序。如此,唐五代与两宋的所有词作都按体式被置于时间轴上,每一调的体式演进可谓一目了然。当然,区分分句数、复句数、复句型的前提是正确断句。《源流谱》参酌今古,提出新的标点方式:在注重韵位的基础上参以文意,像“妙谢庭、春草吟笔”“犹有封、狼居胥意”此类有碍句意的停顿一律取消;同时注重语法,只在单句和复句的结尾使用句号,复句内的分句一律用逗号。所以说,《源流谱》是一部既借鉴传统又走出传统、既有学术内涵又便于阅读的新型词谱。
二
《源流谱》在前言里鸟瞰词体体式的历史演变,详述词体构成的相关问题,洋洋十几万字,极具学术价值。
例如变体,表面看只是比始词多几字或少几字,但究竟能增减多少字呢? 变体可以随意“变”还是有限定? 这关涉词之变体的生成机制,传统词谱未作解说。《源流谱》爬梳所有变体后发现,大部分变体的复句数与始词一致,所谓变,主要体现在分句数与复句型上。《源流谱》解释说:一个复句对应歌曲一个相对完整的乐段,如果乐段大变,那就不是本调了,所以乐段的稳定意味着复句数的稳定。同时音乐又有弹性,一个乐句在音乐长度容许的范围内,对歌词的字数没有刻板限定,这就允许分句数与复句型有自由变化的空间。像耳熟能详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如果唱成“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完全没问题,但也不能无限加字,不能超过这一乐段的容量。可见《源流谱》是回归词体早先“活态歌唱”的生存状态,从源头上解开了变体之谜。
如果说变体产生的机制是“源”,那么以后的体式演变就是“流”,此二者都是《源流谱》的题中之意。以《念奴娇》为例,《源流谱》以北宋沈唐“杏花过雨”一阕为源头,苏轼的“大江东去”与“凭高眺远”分列“变体二”的第一式与第二式。耐人寻味的是,北宋照“大江东去”与“凭高眺远”填词者,相差不多;而南宋多数人都照“凭高眺远”填,“大江东去”名气虽大,照填者却寥寥无几。《源流谱》认为:“凭高眺远”一阕的句式比“大江东去”规则整饬,南宋人更多选择这一体式,说明词体建构在走向“规则”。这种分析也展现出《源流谱》的学术特征:在溯源穷流中发现问题,而非单向的逻辑推理;用高屋建瓴的眼光解释问题,而不限于局部。
其他再如宋人为何不制词谱,律词何时成为主流,程式化与弹性化如何有机结合在“词体模型”的建构中等等,都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学术命题。这种阅读感觉,借用《世说新语》的话说,有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三
优秀的学术著作必然在解决问题之外给人以路径与理念上的启示。兹说三点:
第一,重文献但不迷恋文献,要有理论意识。黄侃先生曾对吉川幸次郎说:“中国之学,不在发见,在发明。”所谓“发见”,指对文献的搜罗与发现,“发明”则是在文献中挖掘出义理。在查阅文献已不成问题的今天,黄侃先生的意见尤为重要。若论词谱资料,那是人人可见,但要有所“发明”,则是凤毛麟角。《源流谱》却有很强的理论意识,于词史研究多有“发明”,一方面体现在剖析问题时的理论指向,如谈词之乐体、文体与变体机制等问题时都清晰指向“歌辞总体观念”这一宏大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也体现在长时段的研究路径上,当然,这与其理解为法国布罗代尔“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法,不如说是一种东、西方都有的回归历史原态的研究路径。只有在唐五代到两宋这样一个长时段中,才能看清词体缓慢而层积的演进过程。
第二,重专学但不固守一隅,要有广阔视野。现在古代文学研究大致分诗、词、曲、赋等门类,下面再分各种专学。重视专学研究是现代学术分类的结果,但也会形成学科壁垒,知诗而不晓词,知文而不通曲,已是学界常态,即便研究词,也是宋元明清各守一隅,很难见到融会贯通式的重大成果。《源流谱》于此做出突破:其重心虽在唐五代至两宋,但论及律词演变时,也延至清词;在论述变体生成机制时,引入了音乐视角;在考察词中“联调”“集曲”等现象时,则与诸宫调、宋南戏相比较,实现了词与曲的贯通。这种广阔的视野源自作者多元的知识结构,李昌集先生懂音乐、精吟诵、善书法、会填词,所以《源流谱》既有扎实的专学素养又有广阔的学术视野,这对当下各守一摊、埋头切葱花的专学研究具有警醒意义。
第三,重预流但不急功近利,要有学术宏图。陈寅恪先生提出学术研究要“预流”,通俗地讲就是要关注学术潮流,站在学术前沿。近些年,词谱学研究非常火热,其实早在2011年李昌集先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词曲源流史”时便有编纂《源流谱》的设想。这是利用申报重大项目的机会来引领、参与词谱学的研究潮流。与有些项目用影印文献加几篇论文就去结项不同,《源流谱》历经十余年打磨才出版面世,因为作者有宏大的目标:要以歌辞总体观念为基本立场,以词体结构与历史演变为总论题,对词体源流史予以整体说明和理论阐释。为了实现目标,作者几易书稿,十年一剑,这在重视数量的考评机制下殊为不易,不仅要有深鸿厖大的学术理想,更要有锲而不舍的学术定力。
《景德传灯录》中禅师语曰:“盲龟值木虽优稳,枯木生华物外春。”移诸学术研究,我们不能做盲龟,抱一段浮木就感觉良好,而要像《源流谱》这样,用厚重的成果让相关领域迎来新的春天,此为治学之上乘境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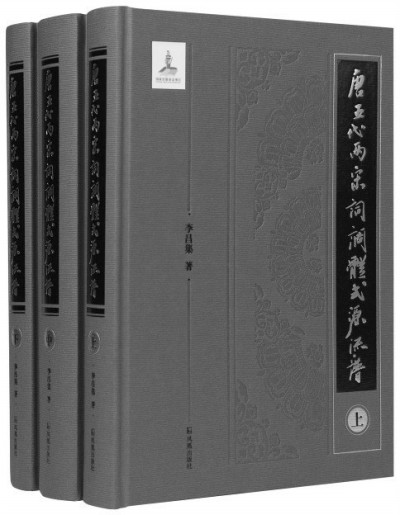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