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林雪 田泥
文学艺术创作是抵达生命内核的探寻,也是以虚构的或非虚构的方式来表达自我感受与思想及价值的。刘建林的近作《问鼎》,就显示出了非虚构历史小说的独特性。他以当代文化视角进入历史叙事,有着惯有历史叙述的真实情境的呈现,也以现代思维展开历史想象,以理性进行历史反思,以感性编织历史抒情。如此,中国历史上唯一被正史承认的女皇武曌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时段,以及那些在历史中浮潜的情感与理性、隐忍与残酷、政治与权术,都被尽可能鲜活地表达了出来。这道投向历史隧道的光亮,为读者照亮了一个具象、立体的女性历史人物生命轨迹,她冲入了男性权力空间,改写了女性在历史中固化的存在模式,影响与重构了当时的政治秩序与社会机制。
《问鼎》讲的是一个历史故事,故事主角是一代女皇武曌,可被定位为一部以女性为主要叙事人物的历史长篇小说。作者从贞观十二年(638)开始写起,这位美丽的14岁女子告别亲友背上行囊走向皇宫,直到天授元年(690)九月九日,那天艳阳高照,66岁的她推翻了李氏的大唐王朝,建立大周帝国。武曌冲破道德伦常、权力结构、政治伦理的深锁,从一个家世平平孤身闯入帝王深宫的少女、一个在感业寺守着青灯古佛的卑微宫女,成长为大周王朝独断朝纲的神圣皇帝,问鼎成功,小说落笔。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史实,在一个以男权意志为主导的封建王朝,女人穿过历史的迷障与重重阻碍,进入男性权力中心,并比肩、超越男性权力,是鲜有的现象,也是不被封建主流思想所认同的。一个女性如何能问鼎成功,作者又将如何叙述这段由女性影响与改写的历史进程,是这部小说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即历史观与性别观的问题。
在《问鼎》的历史叙述中,一代女皇武曌的政治成功首先被剥去了宿命论的神奇外衣,批判宿命论、强调个体奋斗的理性历史观是作者的首要态度。“人的非凡成功并非是上天的旨意,不是随随便得来的,而是用汗水心血甚至生命换来的。”作者褒扬武曌的成功,认为她“是一个不断打碎旧制、冲破传统的人”,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其成功的铸就,除了历史机遇的推动,还极具个人女性智慧与政治智慧。
无疑,以人为本位的历史观影响了小说的历史书写。武曌的个人奋斗史,涉及其作为政治人物和女性存在的两种历史。身为一个女性,她需摆脱女性面对的男尊女卑、纲常伦理等构成的传统文化秩序之束缚;作为一个没有世袭资格的平民,她需以平民身份战胜世袭贵族阶层。小说借助还原人物社会历史处境的方式,武曌生动的两面得以展现。作为政治人物,她拥有雷厉风行的制衡手腕与政治权术,但也慢慢权欲熏心被权力魔杖所吞噬。作为女性人物,她的精神世界几乎是分裂的,她一方面视争宠为战斗,将后宫敌人王皇后、萧淑妃等残忍杀害;另一方面,她也不是生来残酷,也柔软有情,珍惜着如寻常百姓家的幸福,对家人付以温柔。
在介入男性权力空间中,在政治人物的突围之路中,武曌在女性自我本位之下,先用李治的宠爱顺应后宫之道摆脱位卑身份,获得参
政权力。而后拥有兵、钱、权的“外势”,以物质基础支撑自身能力,对待敌人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准则,一边夺权如“秋风扫落叶”,一边迅速建立自己的政治队伍,最后联结天意舆论把握“内势”,以强权、能力、民意、天意瓦解了朝堂上保卫李氏唐朝的“公道”。正如书中所评价的,“武后虽为女子,竟然是个政治高手”。在武曌的雷霆管理下,帝国重新充满了生机活力。但就如权力欲望是武曌奋斗的动力,也使其成为权力的奴隶,滥用法治的酷吏、告密之风的兴盛使大唐进入了惨绝人寰的时代,打破了大唐的最后一道防线。
作者以历史辨伪的方式肯定了武曌作为女性的柔软,认为这位独断朝纲的帝王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拥有基本的母性以及人性。例如,作者认为史官所写的武曌杀害李弘和女儿的残酷行径是错误的。在作者看来,武曌为李弘杀出一条血路谋得太子之位,并无杀子动机,且李治也曾告诉李弘母亲已原谅了他。而把女儿的死杜撰成武曌为夺得皇后之位的筹码也是阴谋论,那时婴幼儿死亡率极高,寒冬的炭火、被褥的不适以及先天不足等,都能导致新生儿的夭折。作者写到,武曌十分珍视家庭,曾因相夫教子的生活感到无比幸福,甚至觉得“只要他们的爱情不死,那她的美好生活就会长久。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然而,她的爱情终究是死了,与大部分女性人物一样,她要经历过哭泣,才能够摆脱依附的美丽幻梦,走向女性主体的成长。也许是帝王亲情注定可悲,又或是“女强人”的感情多坎坷,她即将面对丈夫、姐姐等一系列亲人的背叛,也选择了有仇必报。回顾这些事件,能够发现她处理感情事件的态度:极其认真,也理性冷静。一向擅长“忍字诀”的武曌,只有在遭受所珍视的亲人的背叛后忍无可忍,才开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例如,了结姐姐与外甥女性命的行为均发生在她亲自发现私情之后。面对姐姐的行为,尽管侍女向她告密,但她仍执拗地不相信,直到自己亲眼看见。她将姐姐的孩子视如己出,历史却再次重演,亲自撞破了私情后的她,跑回寝宫大哭一场后设计毒杀。甚至在政治斗争中,武曌面对自己尚有感情的人物,也是先做退让,若被踩到底线,才杀伐决断。面对一手提拔却背叛自己的刘祎之,她有一些不舍,给他定的罪名仅为贪污钱财和生活作风问题,不是丢掉性命的敏感政治问题。为给数年的股肱之臣留一线生机,不用京城残忍的酷吏,而找外地官员审查。然而刘祎之压根不领情,这才触怒她,给他定了个蔑视皇权的大罪。
小说从女性角度肯定了武曌的柔软,具有一定的女性关怀。回顾开头,作者带着明显的女性意识描述了那个囚禁着无数美丽女子的永巷,也多次发出女子被封建思想毒害的感叹。关于女性与历史,以女性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小说还需将女性成长与历史风云恰当联结,多数的方法为以女性的日常生活折射整个大时代,而历史只成为背景。以一个女人的日常成长是否能撬动时代的历史风云、女性人物被动地承受历史的姿态常受到怀疑,而《问鼎》的历史选材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武曌是一个主宰历史沉浮的独特女性历史人物形象,这使女性与历史同时成为焦点,女性的成长背景也变得无比广阔。日常视角下的女性常成为历史的被动承受者,面对种种人生困境,积极的女性姿态多为:出走或逃离。而武曌的姿态则为逆向突围,身在感应寺的她决定回到皇宫,利用规则创造自己的自由,而非逃出感应寺盲目寻找那片不知是否存在于大唐的女性自由天地。
可以看到,比起以历史为师寻找规律,《问鼎》更注重挖掘历史个体的真实境遇。也许,正因作者持有以人为本位、在社会历史环境中还原真实人性的理性历史观,所以在性别观念上也较为中肯。毕竟,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人性。
作为一部以女性形象为主要叙事对象的历史小说,我们同样看到许多男性历史人物的出场。小说曾用专节对高宗李治进行评点。在作者看来,李治虽然懦弱,但“绝非傻白甜而是狠角色”。仁儒人设注定他不能太过强悍,眼泪是他最有力的武器,流进了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的心里,帮助他获得皇位和权贵老臣的支持。坐上皇位后,他不玩铁腕政治,而采取怀柔政策,借后宫风波将朝堂上的外戚势力瓦解,将毫无政治靠山的武曌扶上后位,因为她始终是他的附属。这个女人被他推至台前,顶着悍妇的骂名替他打江山,当她势力独大时,李治先找个理由将忠于她的许敬宗撵走,架空武曌。尔后假意让位,借大臣的嘴让她死心。总之,武曌亦是李治的一枚棋子。李治既懦弱也有谋略,对男性特质的复杂设计,说明这部女性历史小说对待男性人物的态度较为客观。面首薛怀义亦是很好的例子。当我们以吃软饭的目光看向他时,他已经被苏宰相的数十记耳光抽清醒了,意识到男子汉大丈夫只有顶天立地,干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才能扬名立万。在筹建明堂的尘土飞扬中,他找到了一种真正拥有阳刚之气的男人的感觉,“那种感觉太美妙,使人不知疲倦”。
历史观同样影响了作者写历史的笔法,比起厚重的历史书写,小说不仅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反思历史,也用一套诙谐的说书语言来讲述历史,这些从目录中就可见一斑。作者对正史中的人物,不以正式名头称之,而根据人物际遇以现代名称称呼。例如,女皇武曌被称为“宫女”“贱妾”“姨妈”,病重的太宗李世民被称为“老去的主子”,偏执的太子李贤被称为“偏执狂”等。在行文时,作者也常现身以说书人语气评点人物言行,在大胆的称呼与解释中,严肃的历史化为人物的家常,帝王将相化为生动个体。
不过,有些遗憾的是,政治主角武曌的文化人格似乎还可更深刻,小说的历史文化图景也可更广阔。例如,作者曾数次写到武曌在永巷文学馆里所读的书籍化成了她身处绝境也能做出最佳选择的智慧,但那些书是什么却无可追溯。这些书如何有机组成了她的文化人格? 对此时的政治文化格局有何具体的影响? 与士大夫的文化人格有何相同又有何悖反?如若展开描述,那么在那对母子之间,即李弘与武曌之间,也将有更多可以细写的微妙之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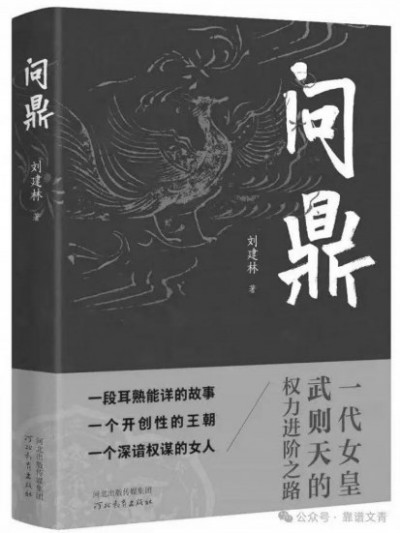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