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南开大学读大三。班上同学议论说,中文系新近调进来的孙昌武先生,一年发表了18篇论文。言谈中,同学们都流露出敬佩的眼神。那时,孙昌武先生刚调入南开大学工作,系里还没有安排他上课。有时会在楼道相遇,我们通常会恭敬地称他为孙先生,他总是微笑着点点头,虽然并不知道我们是谁。那时的孙昌武先生不过四十出头,红光满面,目光炯炯,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他个头不高,嗓音洪亮,走起路来腰板笔直,略微仰头,自信满满,气宇轩昂。在我眼中,有似超凡拔俗的仙人。1981年8月,孙昌武先生为全系学生开设“唐宋古文运动研究”专题课,我终于抓住了接近“仙人”的机会,第一时间选修了先生的课。这也是我读大学本科的最后一个学年课程。
1982年1月4日,“唐宋古文运动研究”专题课还有最后两节课。第一节课上,孙昌武老师谈到自己在“文革”动荡期间,仍然没有放弃读书。他谆谆告诫我们说:人的一生,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一念之间。很多人随波逐流,被淹没在时代的大潮中。而孙昌武先生却坚持下来,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学术发展和贡献。第二节课随堂考试,题目是:试评韩愈“修其辞以明其道”理论与实践。答题内容全然不记得了。但是孙昌武先生的教诲却牢牢地驻留在心间。当时,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一定要向孙昌武先生那样,不论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咬定青山不放松,决不放弃读书。
一
孙昌武先生1961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被派遣到辽宁营口农村当农民。他在《忆旧二 则》(《随笔》2024年第2期)一文中说,就在教育局人事科给他开去农村的派遣证的时候,碰上营口师范学校缺教师,校领导到教育局要人,听说来了个大学生,就把孙昌武先生抢去教语文。他说,人生真是奇妙,如果校领导晚来1分钟,他可能就拿上派遣证下放到农村去了。这是孙昌武先生大学毕业后遭遇到的第一次命运转折。
孙昌武先生酷爱古典文学,在营口师范学校教书时,他开始研读手中保留不多的古代文集,《四部丛刊》本《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就是其中一部。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包括文字训释、写作技巧、思想内容、作品系年等,同时,还受邀公开讲解《封建论》,在全市有了名气。后来,他将自己的研究心得略加总结,写成材料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们提供参考,结果得到出版社的重视,编辑回信建议他写成系列文章。这是孙昌武先生大学毕业后遭遇到的第二次命运转折。
1979年,年逾不惑的孙昌武先生为母校所关注,调回南开大学。他根据在营口多年坚持研究柳宗元积累的文稿,完成了30万字的《柳宗元传论》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请著名作家茅盾为该书题签。这是孙昌武先生毕业后遭遇到的第三次命运转折。
孙昌武先生说:“柳宗元帮我大忙。”又说:“我读佛典,是从研究柳宗元开始的。”读文学,读佛典,“使我懂得感恩和戒惧、宽容与谦卑,也让我对人性多一份信心,对人生多一份热情”(《中国佛教文化史》后记)。从此,孙昌武先生一发不可收,从柳宗元研究开始,研究韩柳,研究唐代古文运动,研究隋唐五代文化史;又从柳宗元开始,研究佛教,就这样一路走来,最终完成了这套皇皇三十册的《孙昌武文集》。
二
孙昌武先生治学集中在两个领域——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宗教 文 化,两 者 又 密切相 关。《柳宗元传论》专辟“崇信佛教,统合儒释”一节。研究柳宗元,绕不开韩愈,而韩愈又是辟佛的。韩柳之间的思想差异,是孙昌武先生从古典文学走向佛教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1981年9月,他为我们开设唐代古文运动研究专题课,除了古文创作,宗教问题依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1984年,在讲稿基础上,孙昌武先生整理出版了《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一书。他在后记中说:“由于中国散文创作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注重实用的功能,又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体裁,锤炼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以及对于篇章结构、语言修辞、表达技巧的高度重视;至于对文章节奏声韵、语气文情的讲究,更显示了散文艺术技巧的高度精致。”40年后,今天的学术界在总结中国固有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时,全面意识到中国散文的独特价值。因此,重温孙昌武先生上世纪这段话,不能不佩服他的真知灼见。《韩愈散文艺术论》践行上述主张,从文体、文风、写作技巧、文学语言等方面全面分析了韩愈古文的艺术成就,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古典散文艺术,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隋唐五代文化史》分门别类地论述了隋唐五代教育与科举、学术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民族融合等问题,特别是宗教一章,不仅论及佛教、道教,还有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是孙昌武先生从唐代文学转向唐代宗教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在孙昌武先生那一辈学者中,同样是研究佛教,项楚先生从文字训释入手,安营扎寨,逐一攻克;陈允吉先生则以思辨见长;孙昌武先生研究佛教,具有规模效应。三位先生研究佛教,都是从六朝隋唐文学开始,逐渐拓展新的学术天地。
孙昌武先生研究佛教,同时兼顾道教。《孙昌武文集》中《道教与唐代文学》《诗歌与神仙信仰》《佛道文学论集》等是关于道教与文学关系的论著。当然,孙昌武先生倾注精力最多的是佛教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华佛教文学史》《佛教与中国文学》《唐代文学与佛教》《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解说观音》《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佛教》《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佛教论集》《禅宗十五讲》《禅思与诗情》《诗僧与僧诗》《文坛佛影》等均为佛教与文学的研究成果。《佛教文学十讲》《道教文学十讲》采用论述与作品选读结合的方式,系统梳理了宗教文学的发展线索,要言不烦地评骘宗教文学的经典作品,是孙昌武先生对佛教文学、道教文学研究带有总结性的论著。最令人称道的是五巨册的《中国佛教文化史》。该书是孙昌武先生研究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作者从事学术工作具有总结意味的著作。全书180万字,涉猎广泛,内容丰富。按照时代线索,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佛教文化的草创阶段,即从两汉之际到东晋后期的道安、慧远等事佛活动。第二编是佛教文化的中国化阶段,即以鸠摩罗什到长安为标志,再到他的四大弟子研究佛学成就卓著。第三编是隋唐以后至宋代出现了一系列中国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2010年6月,《中国佛教文化史》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学界张总、魏道儒、黄心川、楼宇烈、杨曾文、孟昭毅、王晓平、徐文明等,佛学界湛如、觉灯、理征、向学等,中华书局傅璇琮、许逸民、顾青、尹涛等,媒体出版界董秀玉、祝晓风等参加了这次盛会。我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从孙昌武先生的论著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启迪:佛教文化改变了汉唐文化发展的方向。汉唐之间,由于有了佛教的介入,便有了实质性的不同。
三
在《我的朋友圈》(《随笔》2024年第5期)一文中,年逾八旬的孙昌武先生深情地回顾了自己成长过程中曾帮助过他的一些人,有大学同学鲁德才,有营口师范学校的书记王宪华,有布衣之交的文友王充闾等,这些人“不仅让我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与安慰,也得到了继续坚持读书、做学问的条件和空间”。
凡是与先生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先生一生谦逊,极为低调。我们读孙昌武先生著作的后记,他总是自谦地说自己的学术生涯开始得较晚,中间又长时间与学术界隔离,学术基础浅薄,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学术。从中学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大学期间尽管遭遇批判,依然没有放弃读书。读书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正是这样不断地进取,才会不断地拓展新境界。在他前行的路上,总有贵人相助,总能从前辈和同行中得到教益。他在《他的人格堪称学界典范》(《中华读书报》2016年1月27日)一文中写到:“自己常常庆幸,生平多亏遇到一些好人,给我帮助,给我机遇。”
人生的遭遇往往决定于机缘。孙昌武先生进入学术领域以后,又得到社科院黄心川、黄夏年父子的帮助,逐渐融入宗教文化研究领域,结识了周绍良、楼宇烈、杨曾文、王邦维等,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虞愚先生给了他更多的指导,还为孙昌武先生《唐代古文运动通论》题写书名。他在《师从虞愚先生学因明》一文中写到:“他不但是近代最早系统地研究因明并取得成就的中国学者之一,而且更力图沟通印度因明、西洋逻辑、中国名学,总结其共通规律,阐发其各自特点和贡献。”叫孙昌武先生感动的是,虞愚先生年逾古稀,依然天天挤公共汽车,前往单位给他们授课。“几十年对这样的生活条件安之若素,心境坦然,每天紧张地从事学术工作和艺术创作。”这种苦学的精神,对于孙昌武先生有着巨大的震撼。一方面,他说自己“治佛学本是半路出家,国内治佛学有成的许多人,无论是斯学‘大腕’还是初入门的徒弟,不吝接纳我并给予无私的帮助,对我从事佛教教学和研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孙昌武先生也深深地感到遗憾,尽管虞愚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作出了惊人的努力,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由于种种原因所限,却没有取得本应取得的更光辉的成就。这是更让人痛感凄凉的”。
四
我在大学选修的最后一门课是“唐代古文运动”,对于柳宗元、韩愈以及唐代古文产生了兴趣。大学毕业那年,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吴文治先生联系,希望报考他的硕士研究生。吴先生是柳宗元研究的专家,牵头整理过《柳宗元文集》(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并撰写了带有校点凡例性质的“校点后记”,是我所敬佩的学者。可惜那年不知何故,吴文治先生未能如期招生。我别无他路,只好在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沉潜下来,逐渐转向古典文献学,与韩柳及唐宋代古文研究领域疏远了。
1997年3月,香港浸会大学举办文学与宗教研讨会,我有幸得到邝健行先生的邀请参会。在会上,我再次与孙昌武先生见面。孙先生的论文《唐代文人的佛教信仰——禅与净土》,和我的习作《道教在六朝的流传与江南民歌隐语》同收在会议论文集《中国诗歌与宗教》(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版)。作为晚辈,我倍感荣幸。此后,又有几次机会在学术研讨会上得以向孙昌武先生求教,得到青睐。
2004年以后,孙昌武先生多次邀请我参加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所以,我与孙昌武先生的学生,都比较熟悉,在学术上多有切磋琢磨之乐。2007年9月,我还和同事祝晓风一起专程到天津参加孙昌武老师70寿辰座谈会,孙昌武先生的学生,还有南开大学副校长陈洪夫妇也参加了那次会议。那天,孙昌武先生精神状态极好,年逾古稀,红光满面。他说自己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天天游泳、散步。然后谆谆告诫我们说,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这是革命的本钱。
孙昌武先生年长我21岁,却平等待我,多次把我召回南开,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或者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我们的学术,就是这样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每次回南开,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孙昌武先生给我们上的最后一门课,想起先生的教诲。“唐代古文运动”专题课结束后的第十五天,我正式办理离校手续,离开了南开园。一晃,又是40多年过去。很多事,很多人,如过眼云烟,忘在脑后。唯有孙昌武先生那句话一直铭刻心版:人的一生,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一念之间。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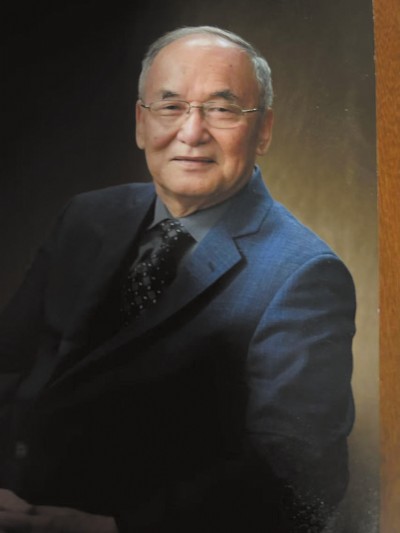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