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志
近两三年,元好问研究迎来一个高潮。国内狄宝心《元好问集》(列入“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查洪德《元好问诗词选》以及拙撰《元好问传论》先后面世,日本学者高桥文治先生《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以下简称《时代》)2021年由大阪大学出版会出版。我们曾用微信公众号推送过该书的封面、摘要、目录等信息,但苦于不懂日文,不能领略其中精彩妙论,所幸这部著作很快由其弟子陈文辉博士翻译成中文,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有幸先睹为快。
从小处入手,细读文本,深入挖掘,是很多日本学 者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时代》也是如此。有些章节直接以某篇诗文为标题,如“《宛丘叹》的真意”“《续小娘歌十首》”。对具体诗句的理解,《时代》往往在看似没有问题的地方提出出人意外的新见。金亡后,元好问一再表达对金史著述的担忧,说“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学东坡移居八首》)。这两句诗明白如话,很容易理解成十年以后,没有人知道金朝历史了。《时代》将“后十年”理解成“正大元年(1224)到金朝灭亡的天兴三年(1234)”,因为这十年的《实录》还没有编纂,很多时事尤其是朝廷大事无人知晓,这样理解显然更加确切。战乱后,元好问回家乡忻州,目睹山中风光:“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园。亦有野人居,层崖映柴门。”(《九日读书山用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韵赋十诗》)这几句也是浅显易懂,我们很容易将“野人”当成普通的村民。《时代》指出,这里的“野人”是指那些“因为战乱和繁重的税金,主动脱离社会团体而失去户籍的农民”,由此可以见出“当时华北地区重大的社会问题”——“逃户”,这才是华北地区的真实乡村。
元好问诗中有些疑难,长期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丧乱诗为例,由于元好问对具体的史实背景语焉不详,导致难以理解。如《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一)尾联“何时真得携家去,万里秋风一钓船”,注家多不出注,以为是元好问抒发其思乡之情,《时代》却揭示出另一史实。天兴二年(1233)正月,金哀宗让皇后的弟弟徒单四喜从归德(今河南商丘)回京城,迎接“两宫”,不料遭遇崔立兵变,徒单四喜只接出自己的家人,置两宫不顾,惹得金哀宗大怒,将之斩首。有此背景,再看这两句,《时代》认为“或许这是元好问在感慨金朝竟然没有像范蠡、严光那样——在实现了国家再建以后以隐逸的方式韬晦于江湖——的人物吧”。再如这组诗第三首的后两联:“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字面意思并不深奥,可以将“地行仙”泛泛理解成享乐之人,但《时代》在施国祁旧注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考索,认为这是批评“金朝将领移剌瑗、移剌粘古兄弟也像五代的张筠兄弟那样,为了自身的安逸,在金朝、南宋、蒙古军之间反复变节自保”。“西南三月音书绝”,通常理解为担忧其家人,但缺少足够的文献支撑,《时代》认为是指担心“出奔西南以后毫无音讯的哀宗、白华等的安危”,因为金哀宗先“东狩”归德,再南逃蔡州(在开封正南方向),白华此时逃至邓州(今河南邓州,在开封西南方向)。这些见解都发前人所未发。
高桥文治先生长期关注金元时期宗教、戏曲,擅长从社会史的角度解读相关文学资料,正如《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书名所示,《时代》尤其注意从时代大背景下来研究元好问,从而得出很多中观或宏观层面的新论断。《时代》以“时代的空白”开篇,敏锐地指出金王朝灭亡后华北地区出现了“约三十年间历史上的王朝空白”,没有王朝,“只有蒙古政权以榨取为目的的税收体系”,元好问等人“经历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深切地理解元好问对撰述金朝史的执着与焦虑。他担心,可有人来撰述金朝史? 金史会不会被当成边缘化的“载记”?金史当然最好由金王朝的遗民如元好问、王鹗等人来撰写。也只有结合“蒙古的战后体制”,尤其是税收给广大民众(包括文人)的巨大压力,才能真正理解在佛、道界纷纷获得税收豁免之后,元好问、张德辉等人为何要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地奔赴开平府(后来的上都),给忽必烈奉上“儒教大宗师”这样可笑、奇怪的称号,其目的就是请求豁免文人的税收,真是用心良苦。
《时代》最让人称奇叫绝之处,是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在记录的东西中寻找没有被记录的东西”。初看此语,似有无中生有的冒险,但是在他有意留心元好问“不想写也没有写的又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之后,通过研究,会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时代》发现,元好问“有时对他眼前切实存在的东西,好像是在故意地‘视若无睹’,或者说是‘故意地漏写’”,“充满了丝毫不愿直叙新体制的制度或实情的‘倾向’与‘意图’”。《时代》举《中州集》中李天翼小传及选诗为例,指出元好问没有记载他熟知的李天翼生卒年和死因,“只是用一篇充满了个人主观情感的煽情文章来代替了他的略传”。更典型的是《金史·白华传》以及相关诗文。《金史·白华传》应该取材于元好问收集的原始资料,用超长的篇幅,只写他十二年间的事迹,对其他人生阶段的经历,一笔带过,甚至连其卒年都没有记载。《时代》指出,《白华传》实际上相当于一篇“辩亡”,“在金朝的历史中搜求着他心中的中华王朝应有的理想状态”,忠实地向后世传递中华传统。元好问与白华交往的诸多诗文,“对于亡国后的白华的生活,元好问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原因是白华的降宋经历是元好问不愿意面对的污点。类似的还有张汝明墓表和张汝翼神道碑。《时代》发现,张汝明墓表对其亡国后的十七年生活只字不提,只留下“其他尚多可称,弗著”这样暧昧的表达;在张汝翼神道末尾,元好问同样留下了“君尚多可称,弗著”的话。对此,《时代》做出诛心式的解释,认为元好问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不能够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写出来的不端行为,那是要多少有多少的’”。由此可见,元好问“的确是一个有节制的,在文字表达上不去刻意揭短评恶的人”。
总之,《时代》胜意纷披,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读者如果阅读该书,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和有益的启示。
当然,《时代》也有个别可商之处。如对《宛丘叹》题目命名的疑惑:“为何会用金朝区划下与南阳完全不属于同一地区的‘宛丘’来做诗题呢?”那是因为李国瑞、刘从益是“皆家宛丘”的县令,元好问比较他们两位县令的不同作为,目的是思考自己如何当好南阳县令这一现实问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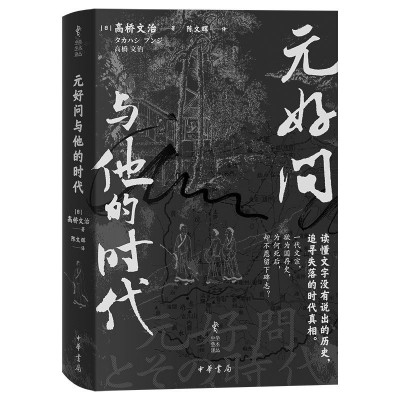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