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冯友兰在他的《新理学》中提出,哲学研究有“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区别,在《三松堂自序》中他又解释道:哲学史研究重在说明前人是怎么说的,哲学创作则是强调自己是怎么想的,此即为“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中国学术研究历来有“照着讲”的传统,对“接着讲”则常加以排斥,视为对传统的背离。因此,“在中国,学问家多,思想家少;学者的作品中,评点感悟式的多,自创一格、自成体系的少。”(陈波语)
其实,何止哲学研究!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生态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出生于晚清、留学美国的胡适和留学日本的陈独秀,分别以《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发起的文学运动开启了现代中国文化社会的巨大革命。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它代表着从那时起,曾经在相当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担当文艺输出国的中国,沦为了文艺理论的输入国。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照着西方18、19世纪的文论讲、照着前苏联文论讲、照着西方现代文艺思潮讲,照着整整讲了一个世纪! 整个文艺理论的现代进程,几乎就是照着西方模式讲的历史! 以至于有学者惊呼中国文论患了“失语症”。
一百年后的今天,人类进入“传媒时代”。由现代“技术”所产生的图像文化正在诱惑人类不知不觉地走向“娱乐至死”(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语)。与此同时,文学正经历自“口传文学”转变为“文本文学”以来的又一次根本性的改变——语言文本的图像化、传媒化,于是也就有了“文学遭遇图像时代”(因在诸多媒介中,图像无疑具有最强势的影响力,因此亦将“传媒时代”称为“图像时代”)的新问题,这就是文人志士们惊呼的“文学命运的终结”。“文学危机”与“符号危机”的双重夹击,不得不让人们重新思考“文学”与“图像”在新时代到底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关系,文艺工作者需要对这一时代之问作出回答。
面对这一片“广袤而诱人的处女地”(著者语),一些具有现实人文关怀的学者开始思考这一时代课题,尝试提出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其中,从事文论研究的学者赵宪章以极大的学术勇气从形式美学、文体研究转向文图关系研究,先是主编出版了八卷本《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2021年7月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学者陈明誉为是中国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后又编撰了通识本《中国文学图像简史》(我国首部阐释中国文学与图像关系的通识著作,俄文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3年度“丝路书香工程”立项项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取义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形成“文学图像论”(所谓“文学图像”,简而言之就是指与文学有关的图像,著者语)这一原创性学术新论域。
《文学图像论》从亚里斯多德“文学是语言艺术”的文学观出发,围绕“语言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图说’”和“视觉图像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言说’”两个范畴,运用“语图符号比较学”方法,在鸟瞰“语图一体”“语图分体”“语图合体”这一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将文学本身之“象”通称为“语象”(语言之象),大量运用西方哲学、语言学、文学、图像学、美学等跨国别、跨学科的学术资源,从语图互仿论、语图指称论、语图传播论、语图在场论、文学成像论五大基础理论和诗歌图像(俗称诗意图或诗意画)、小说插图、文学书像(书法艺术)三种最具代表性的静观文学图像(影视被称为是现代施为图像)展开研究,提炼出诸多具有“中国元素”的新概念:“语图漩涡”“语图切换”“统觉共享”“文学成像”“叙事折叠”“插图逃逸”“顺势与逆势”“实指与虚指”“静观与施为”“字像与书像”……这些看似“自造”的概念、论题、方法,构建了文学图像论学理体系的基本面,成为文图关系新理论的开拓奠基之著(杨剑龙语),既实现了与西方学术的对话交流,又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融通性特点(朱刚语),形成立足中国诗文书画传统的一门“新学”,筑就了文学与图像领域的学术高原(于德山语),真正避免了成为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因此,“文学图像论”并非要推翻传统命题,而是紧密接续传统,沿着维特根斯坦的足迹继续前行。换言之,“文学图像论”是“借题发挥”以面对我们时代的新问题。
“文学图像论”立足中国传统文图关系的现实呈现,利用现代理论和方法,阐释了“照着讲”的时代未曾弄清楚的文图关系上的诸多“悬案”“疑案”。著者研究发现:包括“诗画互仿”在内的整个“语图互访”,在艺术效果方面普遍存在非对称性的模仿态势:图像艺术对于语言艺术的模仿是“顺势”,语言艺术对于图像艺术的模仿则是“逆势”。所以,大凡先有诗而后有画,即很多模仿诗的的绘画作品,很多成了绘画史上的精品;而先有画而后有诗,即模仿绘画的诗歌作品,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则很难和前者在画史上的地位相匹配。进一步研究发现:之所以存在“顺势”“逆势”之别,就在于语言是“实指符号”,图像属于“虚指符号”,两种符号的不同意指功能导致了文学“崇实”、图像“尚虚”的艺术风格,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评价标准。沿着上述思路继续追问,语言和图像之所以具有实指、虚指之分,在于二者有着“可名”与“可悦”之别。语言为世界命名是其基本属性,即通过语言认识世界;而图像对身体(眼睛器官)的诱惑并使其愉悦是其本体属性,这也是当今社会“网瘾”形成的根本原因。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两种传情达意的符号——语言和图像,不仅可以为世界命名,还可以用来叙事、表意。中国传统文图并置的共享场域,图、文、书三者交相呼应而又圆融一体,“图说”被赋予了“言说”的“画外意”,由此创制了图像艺术再现文学叙事的审美理想。晚近以来中国画之所以备受诟病,对这一传统的藐视和疏离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书法艺术可谓至今较少被西学侵染的一块传统艺术领地,作者对“文学书像论”的新发现可谓将“文学图像论”推向高潮。“文学语象延异为字像,被书写的字像就是书像,被欣赏的书像就是艺术——这就是语象、字像和书像的异质同构,前者依次孕育后者并隐匿在了后者的肉身中”——这即是书法之为艺术的学理基础,真可谓语破惊天! 这既避免了对书法艺术纯技术视角的分析,又打破了大而化之的“书学即人学”的窘境,对中国书学的现代转型无疑探索出一条正途。上述理论,均是言他人之未言,但又毫无违和之感,成为对前人言说的自然推进。
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日益普及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近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价值取向以及研究方法。文学艺术既是时代的花朵,又是社会的镜像。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与图像”有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母题。数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与图像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文学由印刷文学变成网络文学,具有了数字化、网络化等特点,图像也由平面二维静态变成立体多元动态影像;二者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主次、并重等固定关系变成深层次、互动性、超链接式关系,甚至文学图像不只是用来被解读和欣赏,更可能用来与人进行交互,其背后无不是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兴起。在对文学图像的研究方法上,不仅限于印刷时代的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文体学等方法,而且由于文学图像都可能被数字化、数据化,因此也增加了数字人文、数字计算等分析方法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文学新时代之“新学”“实学”,赵宪章尝试建构的“文学与图像”关系基础理论,虽“建构了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新论域”,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填补学术空白的原创之作”(陈明语),但也只是勾画了“文学图像论”的大体轮廓。这条展现在我们眼前真实、遥远而又美丽的地平线,既引诱着赵宪章以“文学书像”的身份继续“接着讲”,言说文学图像的另一种样态;同时,作为“铺路石子”,赵宪章的“文学图像论”也召唤着更多学者奔赴前方:将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沿此继续讲下去!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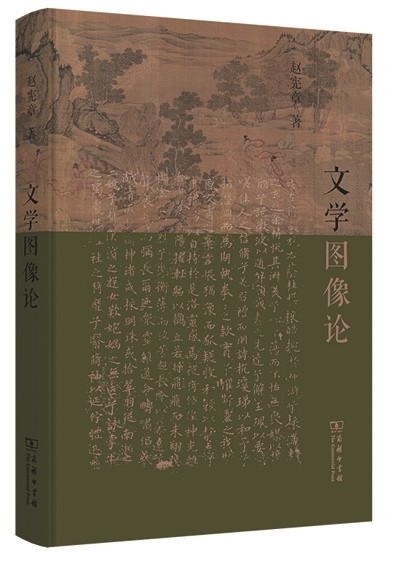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