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
嘉庆二十二年(1817),54岁的湖广总督阮元(1764-1849)调任两广总督,开启了他一帆风顺的仕途上升通道。这一年,春风得意的阮元入手了残存十卷的宋刻本《金石录》,这简直是上苍送给他的一份厚礼。《金石录》是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学名著,历来与欧阳修的《集古录》齐名,人们之所以将金石之学称为“欧赵之学”,就是因为欧赵的这两部名著。据目前所知,《金石录》一书在南宋曾刻过两次,一次是宋孝宗淳熙间(1174-1189)的龙舒郡斋刻本,一次是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浚仪赵不謭刻本,前者为完整的三十卷本,后者为仅存十卷的残本。此后,元明两代将近四百年漫长的岁月,《金石录》一书竟然没有重新雕版,只有钞本流传,天壤之间仅存的这两种宋刻本,因此显得异常珍贵。年代略晚于阮元的清代书法家何绍基(1799-1873)曾经书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明月同行如故友,异书难得比高官”。此联表达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共同心声,传诵甚广。1817年的阮元,既升了高官,又买到异书,二难相并,双喜临门,是多么难得啊。
面对纷至沓来的机缘和好运,阮元恐怕会有这样的想法:宋刻本十卷《金石录》能够成为他的收藏,是冥冥之中对其数十年酷嗜金石之学的回报。八年前,也就是嘉庆十四年(1809),有人问阮元:您致力金石学,究竟有何作为呢? 阮元屈指一算,举出如下十件大事:编纂《山左金石志》、编纂《两浙金石志》、编纂《积古斋钟鼎款识》、模铸周散氏盘南宫盘、摹刻天一阁北宋《石鼓》拓本、发现扬州甘泉山厉王冢西汉刻石、新拓琅邪台秦篆一行、重立曲阜汉府门之倅大石人、摹刻四明本《华山庙碑》、摹刻秦泰山残篆与吴《天发神谶碑》。如果有人在嘉庆二十二年之后向阮元提问,阮元一定会将其收藏宋刻《金石录》十卷列为十件大事之一。从保存稀世珍籍与传承“欧赵之学”的角度来说,收藏宋刻《金石录》十卷,其中的光荣与自豪要比上述十事大多了。
在阮元之前数十年,这部《金石录》就已经成为扬州人的收藏了。藏书家潘祖荫在《滂喜斋藏书记》卷一中说,此书在乾隆年间被仪征江玉屏收藏。江玉屏就是仪征诗人江立(1732-1780),字圣言,号玉屏。江玉屏卒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这意味着,至迟在乾隆四十五年之前,此书就已经归仪征江氏。那一年,阮元才17岁。阮元是江玉屏的同乡后辈,他与江玉屏之子江安(字定甫)是总角之交。阮元为本书所撰第三条跋语回忆往昔:“余童时即与定甫往来,其书室内有‘金石录十卷人家’匾,问其故,出此书相示。”可见,江氏珍藏的宋刻《金石录》十卷阮元早就寓目,不过,17岁的阮元绝对不会料到,三十几年后,这部“异书”会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也没有想到,他本人会成为新一任“金石录十卷人家”。
在友人江安的书室中,阮元不仅看到了宋刻《金石录》十卷,还看到了“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匾额。作为主人,江安(或者江玉屏)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向客人解释这个匾额文字的由来。据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清代初年,杭州藏书家冯文昌意外收藏到一部宋刻本《金石录》,虽然只残存十卷,但毕竟是一部宋板名著,极为珍贵。冯文昌特地为此镌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章一枚,以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自从收了这部珍籍、刻了这枚印章,冯文昌每逢书写“长笺短札”,或者收藏了珍贵的碑帖古籍,就要钤盖这枚印章,惟恐外人不知。他没有预料到,此举竟然成了前贤树立的标杆,后来的收藏家无不见贤思齐。
乾隆间,此书转归江玉屏所有。著名篆刻家丁敬的弟子张燕昌(号芑堂)自言,江玉屏曾请他用最擅长的飞白书体刻一枚印章,印文也是“金石录十卷人家”。很显然,此举就是为了步趋冯文昌,致敬前贤。与印章相比,江玉屏在书室内悬挂的“金石录十卷人家”匾额,不仅体积更大,视觉效果更为突出,其所要表达的珍惜自得之情也更为强烈。
在被扬州人收藏之前,这部《金石录》有一段时间归属于时居杭州的藏书家鲍廷博。著名金石家黄易《秋盦遗稿》中有《题卢刻金石录》一文,说到鲍廷博收藏此书时,也曾刻一印曰“金石录十卷人家”。后来,鲍廷博将此书转让给江玉屏。可以说,使“金石录十卷人家”落户扬州的关键人物,就是鲍廷博,这可能是因为江玉屏与浙江有较深的因缘。一方面,江玉屏在移籍仪征之前,曾经长住杭州,另一方面,在诗词方面,他又是杭州著名诗人厉鹗的传人,有《小齐云山馆诗钞》《夜船吹笛词》等。总之,江玉屏与浙江文士及藏书界交往很多。
“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至迟嘉庆十六年(1811),这部《金石录》就从江玉屏家中散出了。这一年,有一位来自吴兴的书贾带着这部宋本《金石录》,找到汪中之子汪喜孙(1786-1847)。这部异书在汪喜孙问礼堂只寄存一夜,就被书贾拿回去了,汪喜孙为 此怅惘 不 已。嘉 庆 二 十 年(1815),此书再次易手,赵魏购而得之。赵魏,字洛生,号晋斋,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平生喜好金石收藏,撰有《竹崦盦金石目》。阮元编撰《两浙金石志》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时,他曾帮助搜访考证相关材料,见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四。赵魏对这部《金石录》“源流洞悉已久”,购入之时,他正在扬州从事《全唐文》的编纂,与扬州学人往来正多。是年五月至六月间,他邀请扬州本地学者吴应溶、江藩、汪喜孙等人以及同在扬州《全唐文》局的苏州学者顾广圻为其题跋,这些题跋留存至今,可于书上一一覆按。
两年后,也就是嘉庆二十二年,赵魏即将此书转让阮元。阮元在题跋中明确表示,“嘉庆廿二年,余从晋斋处购得之”。考虑到赵魏与阮元的关系,以及阮元在当时政界以及学术界的地位,赵魏将此书转让阮元,不足为奇。阮元初得此本,立即“以书寄至京师,呈翁覃溪先生鉴赏”。翁覃溪即翁方纲,这位精通金石学又擅长作诗的前辈,那一年已经85岁。收到这部《金石录》之后,耄耋之年的翁方纲欣然命笔,为之校阅、题跋、赋诗,兴致勃勃,精神铄,令人赞叹。翁方纲“校之玩之累月,作跋数百字,手书册后。复撰《重镌金石录十卷印歌》见赠”。跋语长达数百字,作于丁丑冬十二月十六日,翁方纲亲笔书写,此时距离翁方纲去世仅40天。《重镌金石录十卷印歌》是一首七言古诗,长达36句,作于嘉庆二十二年腊月,一个多月后,翁方纲就去世了。最为难得的是,嘉庆二十三年正月初七(人日),翁方纲还在家中召集同人聚会,共同观赏此书,那时距离翁方纲去世才19天。雅人深致,终生不渝。
按照阮元的说法,嘉庆二十二年腊月的题跋题诗可以称为翁方纲的绝笔。在我看来,嘉庆二十三年人日的苏斋聚会,很可能就是翁方纲生平参加的最后一次金石学活动。翁方纲《重镌金石录十卷印歌奉赠芸台制府》诗写道:“今晨阮公札远寄,秘笈新得邗江边。阮公积古迈欧赵,苏斋快与论墨缘。”从“秘笈新得邗江边”一句可知,阮元是从当时还在扬州的赵魏手里购得此书的。参加翁方纲人日聚会的同人中,叶志诜(1779—1863)是翁方纲的门人,字东卿,晚号遂翁、淡翁,湖北汉阳人。叶氏学问渊博,长于金石文字之学,收藏金石书画古籍甚富。他奉翁方纲之命,为阮元“补镌‘金石录十卷人家’印文印于卷首,以纪墨缘”。翁方纲题诗中所谓“恰逢叶子仿篆记,宛如旧石冯家镌”“叶子篆样又摹副,其一畀我苏斋筵”,说的就是这件事。至此,递藏这部《金石录》十卷的人家,已有冯文昌、鲍廷博、江玉屏、赵魏以及阮元五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有一枚“金石录十卷人家”印章,无一例外。这是他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文化符号,也是他们共享的名号。每位收藏家都可以称为“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家长,而参与传承宋刻十卷本《金石录》的人们,包括观赏者与题跋者,都可以称为“金石录十卷人家”的亲友。
在历任家长中,阮元是最具“金石录十卷人家”意识的那一位。为了推广这部珍异古籍的影响,扩大这个大家庭的亲友数量,阮元自觉采取了一系列活动。首先是将此书寄呈翁方纲品鉴和题跋,其次是召集门生弟子为之题跋,第三是动员家人知交为之题跋,第四是亲自撰写跋尾和钤盖印章。嘉庆二十三年在书上题跋的朱为弼、洪颐煊、程同文等人,都是阮元的门生,次年题跋者陈均,也是阮氏弟子。
嘉庆二十四年,阮元还将此书借给姚元之、姜宁等人传钞披览。借阅此书的桐城姚元之称赞此书为“稀世之宝”,自有他的理由。在我看来,此书的“稀世性”之一,是它与宋清两代三位才女结下的不解之缘,宋刻十卷本《金石录》的流传史遂有了突出的性别背景。第一位才女自是北宋才女李清照,她不仅与夫君赵明诚同为《金石录》的编著者,也是《金石录后序》的作者。在收藏此书的明代学者朱大韶看来,李清照的《后序》“委曲有情致,殊不似妇女口中语,文固可爱”,可惜的是,十卷本《金石录》却缺少这篇《后序》,于是,朱大韶“勒乌丝,命侍儿录此序于后,以存当时故事”。尽管朱大韶未留下这位侍女的名字,但此举已足以为此书增添一层女性背景。第二位才女是阮元之妾刘文如(1777-1847),字书之,号静香居士。刘文如能诗,兼工绘画,有学识,曾在阮元指导下编撰《四史疑年录》。她为本书作跋,大抵出于阮元授意。跋文仔细梳理《后序》文字,考辨赵、李两人联姻背景以及年寿岁月,虽未挑明,其意图实是替李清照晚年再嫁张汝舟之事辨诬。顺带说一下,阮元妻子孔璐华,字经楼,山东曲阜人,孔子第七十三代长孙女,著有《唐宋旧经楼稿》;阮元另一位侧室唐庆云,字古霞,吴县人,著有《女萝亭稿》。她们虽没有题写跋尾,却各在书上钤盖两三枚印章,也算登台亮相了。第三位才女是当时的著名词人顾太清。她是乾隆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孙多罗贝勒奕绘的侧室,原姓西林觉罗,本名春,字梅仙,号太清,别署西林春、太清春,著有《天游阁集》《东海渔歌》。顾太清为此书题咏一首《金缕曲》,其下阕为:“芸台相国亲搜校。押红泥、重重小印,篇篇玉藻。南渡君臣荒唐甚,谁写乱离怀抱。抱遗憾、讹言颠倒。赖有先生为昭雪,算生年、特记伊人老。千古案,平翻了。”作者于词题下自注:“芸台相国以宋本赵氏《金石录》嘱题”,又于词末自注:“相传易安改适张汝舟一事,芸台相国及静春居刘夫人辩之最详。”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处自注仅见于词集,而不见于书上跋尾,顾太清词后来又被况周颐擅改,几致面目全非,杨焄曾撰有《李清照“再嫁”与顾太清“出轨”》(《文汇报》2020年9月2日)一文,叙说此中详情,委曲有致,读者可以参阅,这里就不细说了。
翻阅十卷本《金石录》,顾太清题词的落款是:“俚词呈云台老夫子、静春居伯母同教政。西林春”。这几句文字不见于词集,从中可以看出,顾太清是奉阮元之命而作此词的。与此同时,顾太清的夫君奕绘也为本书题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夫妻二人同为此书题跋,除了奕绘顾太清夫妇,就是阮元刘文如夫妇。由于《金石录》出自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之手,夫妻双双题跋一事就格外引人注目,别有意味。紧接阮元之后收藏此书的韩泰华在其《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说:“阮文达有宋椠十卷,即《读书敏求记》所载。文达自抚浙至入阁,恒携以自随,既屡跋之,复为其如夫人作记,盖窃比诸明诚、易安云。”阮元抚浙之时尚未收得此书,韩氏谓阮元“自抚浙至入阁,恒携以自随”之语未免捕风捉影,但他说阮氏与阮刘文如作跋,有“窃比明诚、易安”之意,却是有趣的观察,独具只眼。
确实,自从阮元收藏这部《金石录》,他就珍若拱璧,从两广总督到云贵总督,从回朝任职到致仕还乡,无论到哪个新的地方,换了哪个新的职位,他都随身携带这部珍籍,一有闲暇,就拿出来玩赏。他先后在书上题写了五条跋尾,钤盖了近三十枚印章。嘉庆二十三年(1818)六月十四日,阮元在南海节楼为此书题写第一条跋尾。道光十八年(1838)三月望日,阮元“直文华殿,夜宿内阁”,他打开随身携带的这部《金石录》,再次翻阅,不禁想起二十年前题写第一条跋尾时的情景,抚今追昔,思绪万千。他一定联想到了欧阳修和赵明诚。
当年,欧阳修也曾致力于收藏拓本,在“了却公家事”之馀,他常常偷闲把玩手边的石刻拓本,不止一次的赏读,留下不止一篇跋尾。这些跋尾是欧阳修日常生活美学化与人生诗意化的体现。时移世异,欧阳修的跋尾手迹大多佚失,其中有一部分竟被赵明诚收藏。赵明诚在闲暇之时,也曾多次阅读玩赏,并留下了跋尾。几百年后,阮元又通过这部《金石录》与赵明诚遥遥相对,满纸的跋尾和钤印,尽是对赵李的追慕和怀想。
阮元写第四条题跋那天晚上,正在文华殿值班,事后,他将此事告知奕绘,于是有了奕绘的题诗:“相随滇粤廿余年,今春携入中书省。惟日丁亥三月望,殿阁参差月华静。灯前亲写第五跋,不似东坡醉酩酊。闰月丁亥索我诗,此固愿焉不敢请。”阮元题跋在三月丁亥,奕绘题诗在闰四月丁亥,相隔六十天,却是同一干支,故奕绘视之为吉日良辰。
书上还有金石家沈涛的跋尾,据落款日 期推算,在道光癸卯(1843)元日之前,《金石录》这部“稀世之宝”已归藏书家韩泰华所有。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说:“一日书贾来售,惊喜欲狂,古色古香,可宝贵。余得之,亦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小印。”刻一枚“金石录十卷人家”印章,早已成为收藏家的仪式化行为,不刻这样一枚印章,似乎就无法在这一传承脉络中立足。
同治十年(1871),这部奇书转归原籍苏州的藏书家潘祖荫所有。潘祖荫将各家题跋和钤印录入自己的《滂喜斋藏书记》卷一。抄录之时,他注意到这样一个突出的现象,并引为佳话:“冯氏初得是刻,镌一印曰‘金石录十卷人家’。其后江氏、阮氏、韩氏递相祖述,皆有是印。”(《滂喜斋藏书记》卷一)知行合一,潘祖荫立即请著名篆刻家赵之谦为自己刻了一枚“金石录十卷人家”印,时在同治十一年春,距离此书入藏滂喜斋才几个月。光绪十六年(1890),潘祖荫病逝,与他同乡、同龄的好友翁同龢撰写挽联表达怀念:“《金石录》十卷人家,叹君精博;《松陵集》两宗诗派,剩我孤吟。”显然,在翁同龢看来,潘祖荫一生最称得称道的收藏,就是这十卷宋刻《金石录》。
此书同治、光绪时代的题跋,只有顺德李文田、中江李鸿裔和长洲叶昌炽三家。与嘉道时代相比,几乎如晨星寥落。回首数百年历程,这部珍贵古籍每隔几十年即一易手,只有冯文昌自鸣得意的“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名号,一直如影随形,追随着这部奇书,由杭州、扬州流转到苏州、上海,最终成为上海图书馆珍藏的宋刻之一。翻开书页,但见“鉴定印记累累”,证明“异书到处,真如景星庆云,先睹为快”(《滂喜斋藏书记》卷一),难怪阮元要感慨“人实不朽,书亦增重”。可是,除了钤在卷首的那枚叶志诜为阮元所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之外,冯文昌、江玉屏、鲍廷博、韩泰华、潘祖荫等人所用印,却全都杳无踪影,这是为什么呢?
202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将上图珍藏的十卷宋刻《金石录》以高清影印的方式出版,先后推出仿真线装本、平价精装本。此一珍贵古籍得以化身千百,普通读者皆得以购藏坐拥,并由此跻身“《金石录》十卷人家”,书实不朽,人亦增重,岂非天壤间之书林佳话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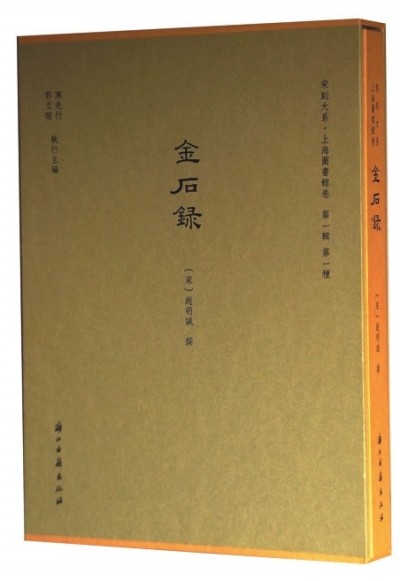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