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丰
正如学界所一般认为的那样,虽然丝绸之路研究如火如荼,但是传统意义上的青藏高原并未被纳入其中,将丝绸之路与青藏高原考古有机地联系起来,显然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以《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为题的这部新著。青藏高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以往的考古工作非常薄弱,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界和公众对这一区域古代社会发展的认知。该书是利用文献与考古材料系统地论证和重建跨越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的首次尝试,通过对大量最新的考古资料的分析和统合,实证了青藏高原并非一个孤悬于世的闭塞地理单元:高原的北部和西部两个区域是汉唐时期与丝绸之路主干道关系最为密切的区域,通过种种途径与中原汉地、西域、中亚等其他地区建立起了密切的文化联系;同时佐以地理学、民族志、历史学等材料,初步建立了青藏高原的古代交通贸易和文化互动网络,这些广泛的互动网络使得这一区域与周邻其他文明的发展保持着基本相同的步调。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促进了青藏高原的技术进步和社会演进,是西藏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本书是作者2008年德国蒂宾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The Silk roads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from the Han to Tang Dynasty) as reconstructed from archaeological and written sources(《中古早期青藏高原北部的丝绸之路:依据考古与文献资料的重建》)的基础上形成的,不过在许多议题上进行了扩展。
书中通过对整个青藏高原近年来所见的大量考古新材料进行全面搜集、系统分析和深入解读,首次提出并论证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当然这一概念并非向壁虚造,它是青海境内的丝绸之路以及西藏境内的唐蕃古道等一些跨区域、跨文化通道的贯通和综合。这个视角并不是全新的,因为在很早以前学者们已经关注到丝绸之路的青海道(或称唐蕃古道)。但作者以考古材料为线索,来讨论这些发现所具有的意义,显然较过去的研究有较大的推进。从整个欧亚大陆的视野来看,青藏高原上的这些交通路线并非仅仅是局限在高原内部的局部或片段式的通道,而是向外辐射延伸的跨地域、跨文明的系统性联系网络,并没有将青藏高原内部之间相互割裂分别审视和考察,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全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上编为“青藏高原北部的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共有七章,讨论的地域范围大致限于今日青海省。以青藏高原的自然地理为开篇,描述人类的生存状况。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已经踏足青藏高原。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又发生了人群第二次迁入青藏高原的事件。这一时期氐羌部落人群进入了青藏高原,并与此前生息于此的人群融合,最终形成现代藏族的人群格局和遗传背景。
接着对青海地区汉晋到吐蕃时期的考古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尤其对吐谷浑和吐蕃时期的遗存进行了甄别和讨论。吐蕃时期青藏高原北部丝路沿线的考古发现包括墓葬和遗址,遗物则有金银制品、丝织品、铜铁锡器物、半宝石、砖石木泥制品、漆器、文字题记等。作者揭示出它们的空间分布、类型、艺术风格、来源等,尤其是所反映的跨地域文化互动与交流情况。这些问题的个案研究虽限于体例有点到为止的倾向,但相较以往的讨论明显有所深入。
举例而言,青海省目前已发现多具彩绘木棺,郭里木彩绘木棺和私人藏彩绘木棺等材料表明,这些棺板画上的叙事手法,自右向左,大致完整地描绘了吐蕃时期苯教丧葬仪式的几个重要环节。各画面在空间上连续,时间上先后有次,构图上错落有致。迎宾献供、灵帐哭丧、动物献祭和骑射祭祀,都是围绕停尸灵帐来进行。丧葬宴是丧礼的最后部分,占据了整个棺板的左半部分。棺板画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大部分为典型的吐蕃服饰且涂有赭面。另外还有戴黑色风帽及山形毡帽的鲜卑人物。整体显示出吐蕃文化、鲜卑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此外,棺板画中还有着丰富的中亚粟特、萨珊波斯等异域因素。这些细节折射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具体情形。
此外,吐蕃时期考古的若干专题也是本书的重点之一,作者尝试解决部分重要墓葬和其他遗存的性质和年代问题。从热水一号大墓封土和墓室的结构和规模来看,与吐蕃赞普王陵比较接近,而高于吐蕃大论(地位约略相当于汉地宰相)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这与文献记载中吐谷浑邦国小王在吐蕃官僚体系中的地位也是相符的。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的考肖图遗址,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一处吐蕃时期墓葬。但通过对考肖图遗址的选址、主体建筑的形制结构、配套设施的规模与布局、出土器物所显示的使用功能和宗教内涵的分析,作者认为它与吐蕃时期的墓葬特征具有很大区别,很有可能是一座吐蕃时期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而与墓葬无涉。同时,遗址出土物中也蕴含了可能属于吐蕃时期苯教的因素,显示了当时的宗教文化特征,这无疑是一个深具卓识的判断。
下编为“青藏高原西部(即西藏阿里)的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亦有七章。通过对西藏西部(尤其是阿里地区)考古新发现的分析,结合周邻国家和地区的考古新材料,重建了穿越喜马拉雅的古代丝绸之路的路网系统。这些研究大体复原了西藏西部丝绸之路形成、发展和兴盛的历史,同时也对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初步的分区、分期和跨区域文化因素分析,初步建立了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以墓葬为例,青藏高原西部及周邻地区所流行的墓葬,从小型石室墓到石丘墓、洞室墓、婴幼儿墓葬和大型竖穴石室墓,反映出随着时代的演进,墓葬形制由简单到复杂、由小型到大型、由浅表到地下、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趋势。随葬物品也由简单粗陋逐渐到复杂多样、组合完备、质地精美。这实际上反映了自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后数个世纪之间青藏高原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过程。
与南亚等区域的贸易是下编讨论的另外一个重点。青藏高原西部对外贸易模式主要有两种:“垂直贸易”和“长程贸易”,前者是指利用高原地区的动物产品交换河谷地带农民的谷物粮食;后者讨论的则是游牧人作为运输者或中间人参与到不同定居区域之间的贸易,主要依赖牦牛、犏牛、山羊和绵羊提供的运输能力,往往长途商队贸易有时比直接用畜牧业交换农产品更有利可图。从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来看,青藏高原西部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中,最重要的是狮泉河通道和象泉河通道。此外,通往我国南疆地区的羌塘高原通道以及通往北印度和尼泊尔的卡利甘达基河通道和吉隆沟通道,对于青藏高原西部古代文化面貌的形成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发展的最巅峰阶段,作为一个国际化通道,它首次实现了东亚和南亚之间的直接官方交往,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唐王朝及吐谷浑、吐蕃政权与尼泊尔、北印度官方合力打通的穿越喜马拉雅的通道,促进了东亚和南亚在宗教、商贸、政治和文化上的直接交流。在藏传佛教的后弘期,这一通道对于西藏的佛教传播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丰富详实的资料是本书值得关注的一个亮点。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大量的文献资料,尤其集中于对青藏高原北部地区汉唐时期古代交通拓展进程的梳理。二是对散见的青海地区汉唐时期考古资料进行了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这部分资料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但缺乏完整的考古报告和简报。作者通过大量的实地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弥补。三是西藏西部地区大规模考古发掘所获大量第一手新材料。作者本人自2012至2018年带领团队在高海拔的西藏阿里地区对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进行了为期五个年度的考古发掘,收获成果非常丰富,这些成果被充分解读和吸收。此外,最近数年来国内外一些博物馆陆续以展览和图录的形式公布了一大批吐蕃时期遗物,也为本研究增添了新内容。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创新。将各个时期各类遗存和遗物置于当时宏大的时空背景中进行联系、比较和阐释,这一方法的实施难度很大,需要积累大量的相关资料。实际上对于每一类遗存和遗物的深入探讨基本上都可以单独成篇,形成一批专题学术论文。本书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将古代文献与考古出土遗物紧密结合,来复原青藏高原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利用情况。此外,还侧重于多学科综合研究,尤其是对于丝绸、金银器、铜铁器、人和动物骨骼等的实验室分析成果的吸收和运用。可以说突破了前人的研究,填补了青藏高原考古的诸多空白点。
霍巍教授在序言中高度肯定了本书在运用历史文献、结合考古材料以复原其历史背景上的扎实学术训练与功力,以及作者所具备的欧亚考古和中国考古双重学术训练的开阔视野和扎实文献基础的能力,笔者认为霍氏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当然,最引人注目也不可不提的是本书取得的新认识和提出的新观点:
1.本书对于近年来都兰吐蕃墓地等新出土的材料有系统、独到地认识和解读。作者将海内外所见吐蕃时期金银器、丝绸等进行穷尽式搜集(第六章第二节和第三节),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来判断新出材料的功能、时代。指出热水墓地出土的骑马射猎、人物等金银箔片,主要是用于漆木棺的外部装饰;考古出土和海内外所藏的大量拱形或椭圆形的鸟禽纹金银箔片,主要是用于丝绸服饰上的缀饰,是专门用于丧葬的丧服;金银器和丝绸上有大量来自中亚和西亚的神祇形象,其中除祆教外,还有古希腊罗马文化圈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海神特里同等形象。由于金银器或许具有某些鲜明的地方特色,所以推测大部分可能为本土制作的,能自成为一体系。
2.对于青海地区的彩绘木棺板画,本书在对棺板画内容进行清晰解读的同时,首次提出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即吐谷浑统治时期(第五章后半部分)和吐蕃统治时期(第六章第六节)。前者多见于收藏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受到河西彩绘木棺的深刻影响,多有征战、耕种等内容。风格较为呆板、人物瘦削,可能来自河湟及其以南的农业区。吐蕃时期主要为射猎、宴饮、丧葬等内容,人物形象上较为饱满流畅、充满动感,主要发现于海西州地区。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3.本书下册以2012至2018年作者带队在西藏阿里地区考古发掘获得新材料为中心,结合周边地区的资料和民族学、地理学材料,对这些新发现考古遗存的功能、文化背景、工艺技术、来源和输入途径进行了全面分析。其中很多资料是首次公布,也是首次得到系统的论述和分析。比如黄金面具的发现和系统阐释(十三章第二节),丝绸的纹样和种类及其与新疆地区的密切联系(十三章第三节),印度圣螺贝饰的分布和来源(十三章第七节),红玉髓珠、蚀花玛瑙珠(俗称“天珠”,同上)、铜容器(十三章第六节)、带柄铜镜(同上)、双圆饼形青铜短剑(同上)和汉式的铁剑(同上)、与茶叶配套的疑似茶具(十三章第四节)等等。本书收集了这些新资料在这个区域的相关发现,分析了它们与中亚、南亚和欧亚之间的文化联系。有的物品还通过比对境外邻近的喜马拉雅山地的民族学材料,来探明它的功能,比如竹筒杯(十三章第五节)、植物种子珠(十三章第六节)、纺织工具等,这也是本书首先发现和提出的新观点。大量搜集和运用境外的考古材料和民族学材料来解释这些新发现,也是本书运用较多的论证方法。
本书还通过对区域历史地理的分析,详细探讨了西藏西部地区古代的交通路线,包括重要的遗址发现地点、山口、河谷、近现代的商道和边境市场等,绘制了清晰而准确的青藏高原丝绸之路交通网络,这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准确的青藏地区古代交通路线图,而且是建立在坚实的考古证据基础之上的。
本书涉及史前至汉唐时期青藏高原北部和西部的丝绸之路考古发现,囊括了岩画、墓葬、遗址、金银制品、丝织品、棺板画、茶叶、珠饰等遗迹、遗物,内容丰富、视野宏阔、阐释也较为细致。或许是篇幅所限,作者针对某些问题的解读和分析,常常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如作者在第六章中对丝绸之路的代表性物品——丝绸进行讨论时,虽已从类别与组织结构、装饰题材、功用、年代四个方面进行了概述,但是对某些具体的纹饰缺乏深入论述,也未详细考证图像纹样的文化来源。将肃南大长岭墓完全归于吐蕃名下,和墓中出土的遗物并未完全匹配,或属他族。
由于本书内容大多并非我所熟悉的领域,以上述介更多是一个年长的“职业读书人”借助“老花镜”所得出的粗疏认识,如果满足于代人读书,行文至此就可以搁笔了。但考虑到学术作品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值得被批评,对这样一部有分量的著作,我认为通过“放大镜”寻找其瑕疵,通过“望远镜”提示其改进空间应当会获得作者谅解。囿于篇幅,仅举二例以塞批评之责:
第一,作者在行文中多次以现代民族称谓指称古代人群,如第47页作者指出“这一次汉族的祖先群体——氐羌部落人群进入了青藏高原,并与旧石器时代的藏族人群融合,最终形成现代藏族的人群格局和遗传特征”。此种处理方式恐有未安之处,除了有将藏族形成时间“前移”至旧石器时代的嫌疑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默认“氐羌部落人群”与“现代藏族”具有生物性的血缘联系,但事实上已有学者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唐代吐蕃真的是自视为猕猴种,自称Bod,那么他应是一个与汉代西羌完全不同的民族,无论两者之间是否有真正的血缘或文化传承关系”(参见王明珂:《什么是民族:以羌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上的关键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4分,1994年,第71页)。这一思路提示我们在梳理古今人群关系时应当注意分寸。此外,将甘青古文化当作氐羌文化的看法忽略了文献中的“氐羌”实际是华夏人群主观的民族认识与分类,许多人类学家已经指出,这种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人群的对应未必不可能,但需要考虑较多论证前提。
第二,尽管作者已经以较多篇幅介绍吐谷浑时期的考古发现和丝路状况,但吐谷浑政权崛起之于“青藏高原北部丝绸之路”的意义或许仍未得到充分阐述。换一种说法,作者需要对“为何青藏高原北部丝绸之路在吐谷浑政权勃兴之后蔚然兴盛”做更充分的回答。之所以强调此点是因为笔者总体服膺王明珂的观点,亦即在汉代河湟地区西羌的经济生活中,对外贸易并没有多少重要性:高山峡谷使得通行不易,不适合进行远途贸易;羌人驯养的主要牲畜马、牛、羊均不适合作为这一地区组成商队的驮畜;河湟西羌的经济贸易主要发生于部落内部而非羌汉之间(参见王明珂:《匈奴的游牧经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1分,1993年,第42—47页)。汉唐之间河湟地区的地理状况和牲畜种类未有大的变易,因此笔者推测,吐谷浑政权的崛起或许是改变当地贸易需求和营商条件最重要的变数之一,其间仍有发覆的余地。
本书篇幅相当庞大,在一些细微处或有疏漏。如第14页注②,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下)》缺少译者“周伟洲”;第67页,“青海汉晋时期”误作“青海时期汉晋”;第120页,“25座墓葬”应为“26座墓葬”;第202页,2002年出土于都兰香日德墓葬的一枚东罗马金币正面侧缘顺时针铭文“DNZENO PERPAVG”13个字母误作“DN⁃THEODOSIVS PFAVG”17个字母,“ZENO(差诺)”误作“THEO⁃DOSIVS(狄奥多西斯)”等。
总之,尽管有这些微瑕,但基本达到了作者所预设的目标,在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研究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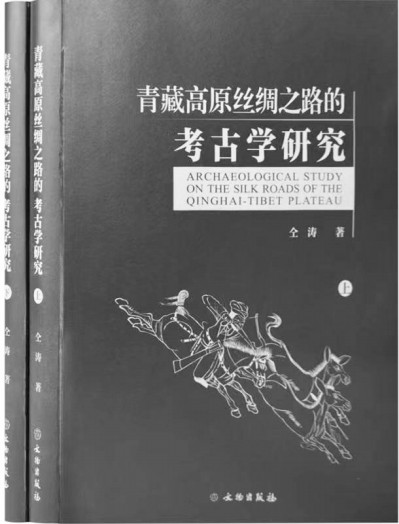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