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颉珉(清华大学语言中心副教授、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阿拉伯文学研究分会理事)
自从1958年萨米拉·宾特·杰兹拉出版其第一部小说《别了,我的希望》以来,沙特的山鲁佐德们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实践,再现着她们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和丰富情感,也构建着属于自己的语言王国,她们发出的声音,让人们注意到了沙特的另一面,一个不同于“石油富国”“保守社会”等固有形象的“阴性”的沙特,那里的生活具体而真实,那里的人们也一样有着琐碎的幸福和痛苦。在宏大叙事日益被消解的今天,她们通过小说,在一个以诗歌为档案的男性世界里,找到了一条“私人化”的突围之路。
宰奈白·哈乃菲在小说《我不再哭泣》的扉页里写到:“致我‘自己’,为了证明其有存在的权利。”娜吉塔·沙耶克在小说《女人的遗骸》中的献词是:“我把这些字母献给那些相信这些字母终会有一天在我指尖悸动的人。”非传统的表达方式,暗示着对整部小说的定位:一份“自我宣言”。其中强烈的自我意识,恰恰反映了在小说之外的世界里自我的缺失,“也许女性所遭到的驱逐和排挤已经到了使她质疑自己存在的地步。所以才有了这部小说或者说是一份礼物,来向她,也只是向她证明存在的权利”。
在沙特女性作家们的笔下,男性往往是软弱、退缩的,而女性则坚强而灵活。她们将传统社会认同的属于男性的各种力量和美德转移给女性,对男性则给予负面的描绘,把他们塑造成家庭以至整个社会迷失堕落的罪魁祸首。所有这些形象都在构建一种新的话语,试图推翻在男性创作中建立起来的话语权,希望借此实现一般意义上的“平等”。但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两性平等,而是一种位置的互换,其出发点是对立和反抗,更像是复仇,所以有时难免狭隘,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广度。而她们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爱”,虽然情感充沛动人,却也往往流于表面,无论是人物的刻画还是情节的建构都颇为单薄。上个世纪60年代才获得受教育权利的沙特女性,对于驾驭各种现代文学技巧还略显生疏,这使得她们的大部分作品现实意义大于文学意义,但拉佳·阿利姆是一个例外。
拉佳·阿利姆是沙特当代小说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1965年生于麦加,目前定居在巴黎。出生并成长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圣城,《古兰经》对拉佳而言既是宗教启蒙也是文学启蒙,不过伊斯兰教在拉佳身上的烙印,主要是通过苏菲主义倾向体现出来的,这应该源自她很早以来对伊本·阿拉比、伊本·鲁米等苏菲派先驱及其哲学思想的着迷。拉佳大学的专业是英语文学,欧美文学对她的影响不言而喻,同时她对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川端康成以及拉美文学的代表人物博尔赫斯和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也十分推崇。丰厚的思想底蕴加上专业的学术背景,使得拉佳在文学创作领域更像是一位职业选手,深谙现代文学的各种技巧,也乐于在创作中进行充满想象力的大胆实践。
拉佳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完全无视小说写作规范的小说,这是她用以瓦解叙事文本,剥离特定的叙事特征甚至写作特征的一种策略”。“她的小说创作是与众不同的。非常适合深刻的文学批评。其能指极为丰富,好像一片肥沃的土壤,适合现代文学批评;而所指亦包罗万象,涉及主流社会文化事件及其相互关联的方方面面。她的作品令人称奇,甚至可以说是传奇性的,综合运用了各种现代写作技巧,尤其是一些在现代诗歌中常用的视觉形象技巧。”
1987年,她在一年之内发表了三部戏剧、一部小说,以一种蓄久而发的姿态登上沙特文坛,凭借比同时代女性作家更加成熟的创作技巧和充满寓言、象征的苏菲式语言风格,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符号世界,引起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迄今为止她出版了包括戏剧、小说在内的十几部作品,她的戏剧《一个女人脸上的360个孔》和《刺尖上的舞蹈》分别获得埃及“阿拉伯国家中心”戏剧创作一等奖和科威特朱赫尔· 塞利姆戏剧创作奖;第一部小说《4-0》获得了伊本·陶菲勒短篇小说奖;2005年,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拉伯女性创新写作奖”;2007年,获得黎巴嫩文化论坛颁发的“阿拉伯创作奖”;2011年,拉佳的长篇小说《鸽子项圈》荣获被誉为“阿拉伯布克奖”的阿拉伯小说国际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2023年拉佳出版了最新作品《巴赫贝勒(麦加多重宇宙:1945-2009)》,入围了今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的短名单。
从2008年开始颁发的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由阿联酋阿布扎比旅游文化局出资赞助,并获得伦敦布克奖基金会支持,奖金丰厚,市场影响力大。每年由各家出版社向组委会推荐上年出版的小说作品,评委们会先选出16部小说进入长名单,然后再从中选出6部进入短名单,最后评出获奖者。多年的成功运作让这一奖项成为阿拉伯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
拉佳的这部最新作品仍然以麦加——拉佳小说的元宇宙——为主要故事背景,聚焦世代生活在此的萨尔达尔家族中一个个鲜活或枯萎的生命,将个人叙事与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融合在一起,描绘了从1945年到2009年的半个多世纪里,麦加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此的芸芸众生所经历的重大社会变革。为了更真实准确地呈现当时的麦加社会,拉佳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当地方言词汇,让很多阿拉伯读者都无法理解,表示阅读过程令人“筋疲力尽”,但仍然惊叹于故事在内容、思想和语言上的独特魅力。
小说故事围绕声名显赫的萨尔达尔家族展开,他们的祖先曾经是麦加的统治者,权势代代承袭,到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年代,家族的主人是穆斯塔法·萨尔达尔。上个世纪40年代的麦加仍处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但身处其中的人们似乎毫无察觉,时间的惯性让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像静止了一样。那是一个女奴仍然存在、驴子仍然是主要交通工具、有身份的女性必须深居简出的年代。
萨尔达尔家是一栋靠近麦加禁寺的五层大宅,穆斯塔法是这里的君王,掌管一切。家中的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他国度的臣民,赞美他并服从他的命令。他几乎抹去了这里其他男性存在的痕迹,因为他是唯一的权威,唯一的“男性”。但被抹去也许是一种幸运,因为对这里的女性而言,“存在”即地狱。终其一生她们只能徘徊在大宅各处,每天的饮食中有一道固定的菜肴——“恐惧”,她们把穆斯塔法称为“独裁者”“斯芬克斯”。“你以为防腐剂是法老的秘密? 我们家的房子里塞满了像我这样的女孩们的标本。”“我们生活中最大的牢笼是‘丢脸’这个词,出门是丢脸,去看去听是丢脸,笑出声是丢脸……你知道什么叫‘命’吗? 大人的话就是我们不可抗争的‘命’。”
这是小说中主要人物之一苏克莉娅对大宅生活的描述。她是穆斯塔法和女奴所生的女儿,母亲生下她后打算将她烧死,因为得不到父亲承认的孩子活着更受罪,但姐姐胡莉娅在最后一刻抢下了已被浇满煤油的小小身躯。在多年的干涉、哀求、自杀威胁后,穆斯塔法终于在一次家庭聚餐时承认了她的身份,但这带给她的并不仅仅是可以在餐桌吃饭的资格,更是一个巨大的牢笼,从此她不可以再随意出门,必须改掉之前的名字,在左邻右舍眼中消失一段时间,直到大家忘记“女奴乌姆莉娅”,当她再次出现,就是“萨尔达尔家的女儿苏克莉娅”,她父亲庞大财富的一部分。
为了阻挠女儿的出嫁,萨尔达尔甚至会故意把女儿嫁给同性恋者,或者在婚礼前找人殴打新郎,让他们最终都把女儿“退”回了大宅里。穆斯塔法最后站立式的死亡也充满象征意味,暗示着“父亲”的权威不会倒下。死亡,从未缺席大宅的生活,但也从未真正降临。在拉佳笔下,死亡或者亡者,如影相随,贯穿始终。死去的人并没有脱离与之相关的事件,没有放弃留下的生者,仍然是一个活跃的角色。“努莉娅穿过笼罩着大宅的浓浓的悲伤……,打开路上的一道道门,‘平安! 这是从至慈主发出的祝辞’她对着每扇门吟诵,也在走过每一条走廊,每一个台阶时吟诵,以便大宅的天使能将她与亡灵姐妹们区分开来,或者确保亡灵访客们在她进入之前退去……”生者世界和亡者世界完全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读者几乎分不清谁还活着,谁已经死去。“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生”的一部分。小说中,像苏克莉娅一样生活在大宅中的众多女性:奋力救下苏克莉娅并安慰她母亲说“无论父亲是否承认,她始终是我们大宅的女儿”的大姐胡莉娅;不蒙面上街,还在清真寺前和男人争辩理论的祖母娜齐克;每次到来都像给大宅女孩们带来“一千盏灯”的姑姑舒尔柏特莉娅……她们虽然活着,却如同死去一般,而那些掌控大宅的男性们,即便死去,却依然存在。
穆斯塔法死后,他的大儿子萨利姆继承了家族的统治权,曾经的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他对着想要去美国学设计的儿子阿巴斯喊道:“自由这个词,你把它从你的脑子里和所有你读的书里删掉,你是萨尔达尔的子孙,这个名字是你脖子上的锁链,它断了,你的脖子也就断了。”但阿巴斯,或者说努里,终究还是离开了大宅,去寻找被禁止的“自由”,因为他是一个“疯子”,是不能继承权力的“白痴”——巴赫贝勒。
巴赫贝勒是小说后半段的核心人物,大宅中唯一一个同女性保持密切关系和情感交流的男性,作为艺术家,他试图拍摄一部关于大宅女性生活的电影,尽管他的姑姑们认为这无异于一桩丑闻,深觉尴尬,但录制和记录还是在她们的同意下进行着,甚至可以说,这种尴尬并没有阻止她们沉浸在成为电影主角的兴奋之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巴赫贝勒的镜头如何调动出了大宅女儿们,尤其是苏克莉娅和努莉娅的冒险和创新精神,她们在演绎自己生活的这些角色中找到了部分的自我,也许还治愈了部分伤口。
“巴赫贝勒”是一个绰号,意思是疯子、傻子。他是萨尔达尔家族的第三代子孙,原名“阿巴斯”,按照助产士的说法,他出生时本是双胞胎,但另一个却神秘失踪了,但她的姑姑努莉娅没有放弃对那个婴儿的寻找,不能生育的她把阿巴斯称呼为“努里”,仿佛他同时也是另一个孩子。所以当阿巴斯和努莉娅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努里”,他的姑姑就成了他的母亲。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读者会发现“努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且他渐渐和阿巴斯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角色。这不禁让人联想起19世纪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长篇小说《化身博士》,只不过阿巴斯的双重人格,并不是正邪对立,而是“雌雄同体”。“阿巴斯”是世俗意义上的正常人,是寻求社会认可的面具,学业优秀、能力突出,在事业上杀伐果断,成就斐然;而“努里”则是他内心的原始渴望,具有女性气质,倾向于音乐、绘画等各种美的艺术,共情能力强;“巴赫贝勒”这个绰号是世人对他不男不女的嘲笑,却也是他自我保护的盾甲,借着“疯子”的身份,大胆表达自己,挑战父权的种种压制。
这不是拉佳第一次在小说中使用“疯子”“雌雄同体”“人格分裂”等具有心理学意义的文学元素。小说《哈提姆》(2007年)中的主人公也是“雌雄同体”。生活在麦加的纳绥布家族生育了五对龙凤胎,但其中的男婴都离奇死亡,无一幸免,“家族诅咒”的阴影笼着每个人,以至于哈提姆出生时的性别变成了不可言说的秘密,这个秘密一直到小说最后也没有揭开。读者可以理解为自己看了两部小说,其一是一个女孩儿在长到青春期时为了家族的需要开始作为男性出现,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身心的变化;其二是一个男孩儿因为家人惧怕诅咒从小把他当成女孩儿养育,在他恢复男性身份后却始终没有从女性经验中脱离出来。每当夜晚降临,哈提姆就会出现女性特征,而白天则表征出男性特征。
在另一部小说《鸽子项圈》中,男主人公之一的优素福也是一位另类的“疯子”,作为天房守护者家族的后裔,他对麦加和禁寺有着特殊的感应,是神性麦加的记录者;而两位女主人公阿宰和阿伊莎,也常常会让读者觉得是同一个人的两种截然不同人格的外化。可以说对于人性矛盾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反传统的叙述方式,是拉佳在人物塑造方面逐渐形成的独特风格,也是很多评论家认为其小说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重要原因。
拉佳本人在谈到《巴赫贝勒》中的这位主人公时表示,“巴赫贝勒”在小说和生活中的存在主要是对主流叙事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通过他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和真实灵魂本能来实现的。“巴赫贝勒是看似消极的外部与因孤立而成熟的内部之间的桥梁。他恢复了我们对生活中失去的魔法的信念。”
“魔法”,这可能是理解拉佳笔下麦加的一个关键词,在她的作品中,麦加身上的神秘色彩不仅仅因为她是伊斯兰教的圣地,更是因为自古以来的各种传说、多神信仰,形形色色朝觐者们的离奇故事……所有这些在麦加汇聚成了一个具有魔法属性的区域,在这里发生任何不可思议的事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在《巴赫贝勒》还是在其他作品中,拉佳在构建麦加这个文学空间时,祛魅与返魅是同时进行的,祛魅是现实不可阻挡的洪流,而返魅则是找回“魔法”的某种尝试。神话的时代早已落幕,但诸神黄昏的一丝余晖却始终斜斜地映照着这里。但当这一丝光亮也消失,取而代之的却不是黑暗,而是灼灼白日,那是在被铲平的山丘上盖起的摩天大楼发出的灯光,站在这里的朝觐者们俯瞰禁寺,他们看到的不会是魔法,只有无所不能的人类现代文明。
石油经济助推了沙特社会的迅速发展,而锐意改革的新一代领军者更是让世人看到了一个想要全面拥抱世界、拥抱现代文明的沙特。身处其中的麦加,或许曾因为其特殊的宗教地位而放缓了变化的脚步,但巨大的朝觐产业,还是全面地渗透进来。就像《鸽子项圈》中的“人头巷”一样,《巴赫贝勒》中萨尔达尔大宅所在的街巷因为禁寺的扩建被拆除,最终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是小说情节,也是真实的现实,只不过名字不同而已。对于这一切的变化,身为“老麦加人”的拉佳似乎是矛盾的,她希望轰然坍塌的是“独裁者”穆斯塔法死去的身躯,而不是承载了几代人故事的老宅,她希望消失的是压抑人性的习俗规范,而不是一条条诉说着古老历史的巷子……但所有这些,就像《巴赫贝勒》里相互交织的多重世界,无法分割。拉佳熟悉并执迷,并一再为之书写的“魔法”麦加,似乎也只能留存在她的文字里:她原本的地形地貌、属于她的神话传说、她代代相传的语音词汇……
当拉佳得知自己的作品入围短名单的消息时,她正在比利牛斯山旁的法国小镇,她把入围名单想象成是小说的另一章,主人公巴赫贝勒未能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他姑姑们的故事,现在却成功地将其带入了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的提名名单。最终,他还是把她们的故事带到了更广阔的地方,而麦加的女儿们,也终究是可以露出她们的面容,行走在世界各地,讲述她们自己和这座魔法城市的故事。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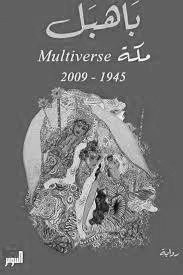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