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明
路过在校园西门的苏州街,旁边小店里播放歌曲: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时光的背影如此悠悠,往日的岁月又上心头……
我不像自己孩子,年轻人作为音乐发烧友,每次听到电台播放歌曲,能够将乐队风格、弹奏技法、背后故事娓娓道来,简直将音乐作为哲学谈论,令人哭笑不得,也无从禁止。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山沟沟的生境没条件接触音乐,自幼即遭到老师批评五音不全,对于音乐一窍不通,也没有追究过这首歌曲到底有何意味,只是觉得其旋律不错,因为借用了鲁迅《朝花夕拾》文集的标题,倍感亲切。
更为微妙的是,近日恰好接到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一篇有关清代秋、朝审中勾决仪方面的论文,即:ZhangShiming,“The Ceremony for Check Marking Criminals for Execution and the Court and Au⁃tumn Assizes under the Qing Dy⁃nasty”,Toung Pao110(2024)1–48。因此,一路上心有戚戚,仿佛觉得这首与学术根本不搭界的歌曲抒发了自己心中一种莫名的情愫。
心田之种
Toung Pao是我1987年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神往与敬仰的学术刊物。当时20岁,因为我最开始研究藏学,藏学属于国际学问,需要懂多种语言工具。我清楚记得我的硕士导师马汝珩先生在张自忠路铁一号寓所斜倚着椅子给我进行启蒙,他讲国际藏学创始人、匈牙利学者乔玛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1784—1842),说国际上有乔玛学会,用外文发音,我听着像“教门学会”。当时国内没有互联网,根本不可能像现在一样轻而易举接触国外文献。但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有些神人,竟然能够将国外学术动态摸得如此透彻。经导师推荐,我找到中国社科院冯蒸先生编著的《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属于1979年内部铅印本,里面将藏文、英文、法文、日文诸多语种的文献、学者、研究机构和刊物等等几乎网罗无遗,成为迷津宝鉴。
在这本指南里面,我看到国际藏学许多声名赫奕的大家在该领域的奠基性论文,每每发表于Toung Pao。据冯著指南介绍,Toung Pao实际上是源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来东方学研究的产物。
遥想当年西方势力向东方蔓延,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势均力敌进行交锋,最终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获胜告终。事实上,西方殖民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于早期东方学的作用是不难理解的。在明治维新之前,当时的荷兰是欧洲科技强国之一。日本模仿的范型是兰学而非日耳曼学,“兰学塾”在江户时代后期的日本风靡一时。荷兰的莱顿大学在17世纪就是欧洲最著名的大学,后来之所以成为欧洲研究中国法的重镇,均是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亚、东南亚开展调查、积累资料的产物。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当年的海上马车夫在英国崛起之后只能甘拜下风,而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获得印度这颗英国女王皇冠上最璀璨明珠之后也无奈风吹雨打花落去,甚至20世纪美苏争霸都已经遁入历史尘烟,但Toung Pao长期以来却在各国学者代复一代的薪火相传赓续努力下厚积流光。现在的老字号往往以百年老店自诩,但Toung Pao被誉为期刊中的百年老店殆不为过。贵族是需要经过三代以上才能养成的,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杂志从骨子里散发出老欧洲的气味,而编辑部目前设在巴黎又使之洋溢着法文作为国际上一度流行的语言所表现出的优雅。
就是在读研究生期间,我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此后又在一些论著中经常可以看到清末民初罗振玉、王国维与当时主编Toung Pao的法国学者沙畹(Emanuel 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ot,1878—1945)等人切磋学术的记述,对Toung Pao的敬仰一直伴随着自己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此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
武树臣之问
这篇文章其实缘起于武树臣教授就拙作中秋审勾决问题的交流。2013年,拙著五卷本《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出版后,第一次报奖是由时任北京市经济法学会会长的王雨本教授按照系统从经济法学会推荐。据先师刘文华教授后来告诉我,这是首届北京市法学会评奖,原本只有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因为我这五卷本当时影响比较大,所以评委觉得两个一等奖显得不符合比例原则,建议特事特办升格为特等奖。当时主持评奖工作的是北京法学会副会长、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树臣教授。武树臣教授在从政之前就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知名学者,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兼具法院领导和北大教授双重身份,后来才专职于法院工作。他恰好是这方面的权威,按照各个评委意见提请北京市法学会党组会讨论将该书评为特等奖。
此后过了大约半年,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平生第一次与武树臣教授见面,互留了电话号码。我当时还没有微信,也没有智能手机,只是一个功能机。后来,武老师把他的一本大作寄给我。在评审之后,因北京市法学会各个评委参与评审,故由法学会每人送一套书以作酬谢。所以,北京市法学会出资购买了大约几十部拙著。武树臣教授会后又专门反反复复仔细看,在大概一年后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说这部书不错,但有一行文字表述值得商榷,就是我在第三卷后面讲到秋审勾决的问题,但他说自己也拿不准。武老师当时刚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岗位退下来,言及曾听一位老法官讲中国学者对于勾决的认知存在错误,皇帝的勾决并不是打钩,而是将勾决的犯人姓名一一连续抄录下来,不加标点,没有空格,这样可以防止官员舞弊,表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是极其严密的。
我虽然迄今与武树臣教授没有多少交往,可能建立联系后也仅仅通过三四次邮件。他从法院领导岗位退下来到山东大学后,就因我换手机之故彼此基本断了联系。不过,武树臣教授年长我很多,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据北大张守文老师说,武树臣教授年轻时,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待遇差,其代表作《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是以木头箱子作为书桌在北大教工宿舍筒子楼里完成的。我在给学生讲课时每每推荐这部作品,起码是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前些年,某出版社准备出版已经绝版的经典作品,让我推荐法律史领域的著作,我仅仅推荐了三部自己心目中的经典:一部是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戴炎辉《中国法制史》(三民书局,1966),一部是亦曾在北京大学任教过的蔡枢衡先生的《中国刑法史》,一部是武树臣教授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戴炎辉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出任过中国台湾地区的“司法院”院长、“司法院”大法官,其命名且整理的淡新档案是最完整的清朝县级行政档案。从阅读经典角度而言,戴炎辉先生最好的法律史作品应该是基于司法实践和整理档案形成的心智结晶《清代台湾之乡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但不符合人家出版社的宗旨和要求,所以提出的书目是戴著《中国法制史》。蔡枢衡先生的这部书是小册子,二十余万字,除了研究刑法的学者外,一般人对此都不注意,但实际上可谓精妙绝伦。武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不是一般讨论法律文化的空洞泛论之作,而是如同书法讲究有骨有肉一般,综摄宏微,贯通古今,基于法律体系的体(外在表现)与系(内在精神)两方面将中国法律实践划分为“神本位·任意法”时代(商)、“家族本位·判例法”时代(西周、春秋)、“国家本位·成文法”时代(战国、秦)、“国家家族本位·大混合法”时代(汉至清末)、“国家社会本位·混合法”时代(中华民国)。其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在中国法律史研究学术脉络中可以说槃槃大才,迄今熠熠生辉。可惜,该出版社最终并没有采纳我的推荐意见。
武树臣教授短信提及的是长期研究法律史的我此前也未曾料想到的图景,令人非常震惊。因为与这样一位学者进行实质性交流不能信口开河,所以武教授发我短信,我当时没有立即回复,因为自己本身糊涂,并不是揣着糊涂装明白,只是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答案才好与之对话。但事实上,武教授这条短信保留在我手机里,直到我的功能机坏了,我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就如此一直留在我脑海里头,挥之不去。在武教授发这条短信半年后,我事实上也曾希望武教授提供一点线索,但他其实也没有确切证据,仅仅属于传闻证据。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遂让我的学生李明去查资料。李明的法史研究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向狠下功夫,查来查去,半年后告诉我无法进行。这迫使我决定亲自“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专门向《秋审条款源流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的作者宋北平请教,宋北平这部专著是基于其2006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其博士论文答辩我当时也是答辩委员之一,很早就看过他的论文,再次反复研读该书却毫无线索,直接问他,也是答复对此一无所知。在此后三年,这一疑难问题刺激我从毫无头绪的档案中寻求确切的答案,一开始也比较难,查原始档案一年,有了一定说话的底气,最终在2018年写成了这篇文章。
上述写作缘起,在这篇文章先行研究梳理中言之甚明。
问世之难
2019年向Toung Pao投稿以后,大概是半年,接到回复,结果还比较不错,没有否定论文,但忧喜参半。三位评议人提了很多意见,要求返修。作者返修是没问题的,但关键在于其中两位评议人的部分意见似乎并不能完全切中肯綮,有的比较正确,但我对其中有一半并不敢苟同。不过,即便内心不认可,也没有办法,只好按照人家的意见规规矩矩尽量修改,当然抵制了一些。
修改完毕,再次投稿。不料,这次匿名评审又换了另外一批人,不知是一些什么专家,但其中一位应该是美国学者,一位估计是日本学者,一位无法推断来自何国何地。这一批的评审学者看上去比前一批学者更为专业精湛,其实把我不情愿按照前一批学者有些意见修改的部分又否定了,成为翻大饼。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责任仍然需要我来承担,后一批评审专家仍然归咎于我的文责。不过,第二批匿名评审专家因为更加谙熟此领域症结问题,提的意见更为深刻到位,对于前一批专家让我删除的一些部分文字直接表示属于应该保留的人所未言的精华。并且比较令人欣喜的是,美国评审专家跟我一样具有后现代主义取向,支持我对美国权威学者德克· 卜德(Derk Bodde)的造反,因为我在批判卜德在哈佛大学演讲论点的资料不是最为典型的,此位评议专家信手拈来美国学术著作中相关资料,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第二位日本学者主要强调要重视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对于一些概念提出不同意见,但看得出来还是非常认同我的研究深度。尤其是大概率为美国学者的专家评审意见中有两句话至关重要,一句是说尽管文章表述还存在问题,但确实对刑法和帝国皇权至关重要的制度带来了崭新的视界(原文为:it really does bring a new vision of an institu⁃tion of a tremendous importance for penal law as well as for impe⁃rial power),一句是说这样的修正主义观点出现在西方备受尊敬的中国学杂志非常重要啊(原文为:it is important that this revisionist view appear in a highly respectedsinological journal of the West)。估计正是这两句话奠定了后来这篇稿件的最终录用。
对第一轮评审返修带有抵触情绪因而略微修改的一个问题,在第二轮评审仍然被旧账重提,成为自己始终无法转过弯的难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不能算学术问题,但对于论文返修而言却是令人痛不欲生。第一轮评审专家即便对于问题本身把握不甚精准,但从西方人角度要求改变行文结构,把论文第三部分有些内容提前并变换写作方式,让普通人也能由浅入深被饶有兴趣地逐步带入预设论证结果。中国学者看来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构,对西方读者而言可能感觉极为吃力,这也是中国人研读外国经典文献经常觉得无法捉摸,甚至直接读外文原著比读中译本更为昭然若揭之故。文章结构变化本来就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如同对一个脊椎弯曲的病人进行牵引矫正手术,不啻一种精神酷刑。西方的历史故事里有“普洛克路易斯忒斯之床”,中国古代也有关于基层酷吏使用非法刑具“匣床”的记载。学术上修改文章结构在精神上经历的痛苦,也是这种类似炼狱般的煎熬。一个学者长期思考特定问题并将其笔之于书,肯定有其丝丝入扣的思维理络,实际上已经形成某种“执念”或者思维惯势,研之愈久,陷之愈深。正是这样,王阳明曾一针见血指出:破山中贼容易,破心中贼难。在医学界,医生不可能为自己做手术,即便遇到给自己至亲做手术也由于难以直面血淋淋的现实而往往退避三舍,转求于他。在学术上,造别人的反容易,革自己的命却难如登天,是必须刀刃向内的刮骨疗毒。将第三部分有些内容按照要求提前并不难,但提前后追慕西方学者的行文风格进行那种炫酷的叙述手法表现就只能说绠短汲深了,最终还是攸赖主编在定稿时亲自操刀发挥类似李鸿章式“裱糊匠”高超技艺补苴罅漏,将文章褶皱妥帖熨平。
这两轮评审修改实际上耗时将近两年。在第二次返修后半年,Toung Pao温文尔雅且博学的主编于2021年4月主动回信,认可该文对清代司法程序提供了重要和创新见解(原文为:your work brings important and innovative perspec⁃tive on imperial judicial processes in the Qing),决定按照排队顺序在一年后发表,算是确定了档期,但说发表之前还要请英美专业学者进行语言风格编辑。第三轮又由编辑部请另外一个英美学者从语言技术上进行修正,又让我返修一次,主要是语言表述的完善,又经历一番伤筋动骨。经过自己和别人数易文稿,最先的初稿已经面目全非,几乎只有六成被呈现于最终稿件。
不幸的是全球蔓延的疫情打乱各种安排,更为关键的是因为毕竟作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话语权是不彰的,所以接连两期都因为稿件积压一延再延,在疫情动荡中不断延宕近乎三年,直到今年终于刊出。但幸运的是,作为这样权威刊物一年两期,这篇文章作为2024年第一期主打论文刊出,也算是对个人而言一种莫大的肯定。
常识之误
小时候,在西北偏僻的小县城,偶尔会看到张贴在大街上比较显眼地方的法院布告,用白纸铅印的大号黑字印刷,上面书列罪犯的姓名、年龄、籍贯、犯罪事实以及被判处的刑罚,印有法院的公章、法院院长名字,除了判处死刑的罪犯名字会被打上红叉,结语“此布”的地方还会打上一个很大的红勾,意思是勾决出的死刑罪犯业已经审判人员验明正身,并无错杀之误。
这种情景和现在许多影视作品里面表现的通衢路口一众百姓围观官方法律布告的情景是一样的,只不过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大都略微描摹以求几份意境神似而已。事实上,不仅普通民众如此想象历史遗绪的渊源,许多学者也往往作如是观。至多就是如同笑话所反映的那样,在天高皇帝远的四川农村的乡民不清楚皇帝如何生活,就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以己度人想当然地认为紫禁城里皇帝会“每天用金扁担挑水”,学者们基于常识认为:清代秋审大典的皇帝勾决之制,与州县官处决人犯大笔一挥来一个花押画勾情景大体相似,只不过规格等级更高一些罢了。
不仅我此前对这种常识没有充分的反省,而且美国权威学者德克·卜德在其影响了许多国外法律史学人的名著《中华帝国的法律》(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Law in Imperial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也基于这种“生死判”常识批评中国传统法律的非理性。德克· 卜德是冯友兰先生的挚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就是其翻译的。他本身是哈佛大学走出来的学生,1938年获荷兰莱顿大学哲学博士,估计在读博士期间就接受了前面说过的作为Toung Pao策源地的莱顿学派中国法研究学风影响。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华访学,曾经见证1948年北平解放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来兼任过美国东方学会主席。卜德的名著《中华帝国的法律》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又在母校哈佛大学士林济济的高端论坛上宣传自己上述对于清代秋审、朝审勾决仪的学术观点,用类似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正义就是法官早餐吃的东西”的“腹痛理论”解读中国传统法律。其实,德克· 卜德的诠释并不是最为离谱,还有英国学者阿拉巴德(Er⁃nest Alabaster)等有关皇帝画红圈的广泛流传的演绎版本。
从最起码的常识来说,我们小时候上学,老师批改作业,对的画勾,错的打叉;用毛笔写大字时,老师认为写得好的画个红圈以示鼓励;用钢笔写作文时,老师认为写得好的句子在下面画一道波浪纹。这些沿袭不替的民间使用的符号肯定与过去法律判决存在联系,但将在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的秋谳制度想象为民间账房先生打钩画叉之举,就不免视如儿戏了。时代的隔膜造成双重误解:一方面,社会制度事实使得我们往往浑然不觉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另一方面,逝如流水的往昔成为无法重涉、难以复现、不可思议的客体。例如,按照写文章引证注释的格式从主原则,日文注释应该如此标注:赤城美恵子「清代における秋審判断の構造:犯罪評価体系の再構成」『法制史研究』第63号、2014年。这样一条注释标注对于不懂日文的中国人而言似乎不可思议,但其间满满的全是中国传统的历史语言符码信息,乃至起码民国时期国人还在使用这一套标点符号体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顾颉刚等点校的二十四史繁体标点本亦是如此,日文中的“、”就是目前中文的逗号,今人将句读(dòu)读作“jù dú”其实就不了解逗号的来历。前引日文书名号“『』”和中文过去的书名号一样,都是勾括弧,即直角引号。这才是勾决之“勾”的字面含义。可以试想,中国古代著名的“勾股定理”中的“勾”和“股”分别含义何在,不会是现代人想象的数学符号里面的打勾。
在古代,“朱笔圈定”“朱笔勾除”都不是一码事,“朱批”与“批红”更不能关公战秦琼。因为这里不进行专门的学术讨论,故而不复申论,但应该肯定地说,清代勾决仪本身与秋审不能被混为一谈,且作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复杂的死刑复核程序组成部分,不是人们想象的皇帝亲自担任法官的一次性仪式而是持续数月之过程,具体讨论可以覆按笔者原文。
意义之维
在每次讲授竞争法经营者集中问题时,我都会援引20世纪90年代波音并购麦道一案讨论其在欧盟进行反垄断法申报审查时引发的法律冲突。众所周知,欧盟、欧共体最初源于基于《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三大条约形成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建立之初就是为了抱团取暖,通过联合做大做强共同体市场的企业,与美国能够平起平坐。美国对其欧洲盟友的联合自然不欢迎,所以当时也是持反对态度。波音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军用飞机生产转向大型民用航空器生产,独步一时,在广袤的蓝天占据垄断地位,使得波音飞机俨然成为民用飞机的代名词。际此之时,欧洲任何一国的航空制造企业对正处于巅峰之上的波音公司均望尘莫及,无力抗衡,因而选择经济利益集团(Groupement d'intérêtséconomiques,GIE)这种法国在酿酒业将各个独立的葡萄种植园联合为一个合作团体加工酿酒并销售产品的法律构架,组建“空中客车”工业联合体,通过各种秘密补贴和免税优惠,三十年卧薪尝胆后,最终在大型喷气式客机市场中坚实地站稳了脚跟,形成与波音旗鼓相当的竞争态势。客车公司首任首席执行官亨利·齐格勒(Henri Ziegler)当时即以极具战略远见的口吻指出:“如果我们在高技术领域没有立足之地,那么我们就会成为美国人的奴隶,我们的孩子们还将是奴隶。”
在中国当下,目前举国上下都在大力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立,但首先要让外国人出自自愿高频引用推服我们泱泱中华的学术国货才能说得过去。但中国学术、中国学派在国际上“说不出”“传不开”的难题,却无疑是当代学人在英语为国际语言背景下避无可避的宿命。中西方文化沟通确实非常困难,尤其是法律史中的许多概念可以说本身具有不可通约性。我自己最近倒腾两篇税法和反垄断法的英文论文,其语言表达难度系数可能远不及法律史的五分之一。
这篇文章属于高影响因子SS⁃CI,和Yale LawJournal(耶鲁法律杂志)、Columbia Law Review(哥伦比亚法律评论)、Studia Logica(逻辑研究)之类都属于所谓外文A刊,从世俗生计言之可以聊充考核之用的租子;从个人学术修行而言,本身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相较于英语国家学者不啻婴儿蹒跚行走与壮汉健步如飞之别,能够在自己尊敬的历史悠久的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可谓九死一生,十年一文,正道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也算作为在芸芸众生的沧海一粟卑微到尘土尽头的自己泥牛一鸣的小小心智标记吧!
父亲在读大学时组织百花园诗社,十年前有硕士论文以此作为研究题目,最近也有人发表相关研究,论述西北校园文学。《百花园诗选》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校园诗歌创作高峰的产物,他自己有本诗集名字即《欢笑与泪珠》,出于怕惹祸上身,在“文革”开始之初的一个夜晚付之一炬,后来长期为此念念不忘,梦牵魂绕。我辈如今的做学问也是如此,有泪水汗水,也有偶尔短暂的欢笑。人生不过如此而已。
古人云:大制不割,大信不约。人与人之间信任即坚逾金石的契约。任何时候,相较于载诸律令典册的法条(即“纸面法”),基于信仰、沉淀于心灵的制度规范(即“活法”)都是更管用的。所谓“契约精神”的“是其所是”之本质,在于这种契约的“精神”而不是体现“精神”的契约。这是不能反经为权,执形忘神的,否则当事人在日常交易时忌惮对方应激反应尚不能肆意妄为,而在法庭上就可以以法之名无语不谎,法官可以在判决书里通过抠字眼道貌岸然任意强奸法律而毫无愧怍。正是因为有信任,家长不会因为孩子将来可能不慈不孝,让读大学的孩子在缴纳学费、给付生活费时签订一份供养自己晚年生活的“契约”,否则属于遗赠扶养协议的家庭外部人关系。在竞争法中,签订卡特尔协议的经营者往往都是各怀鬼胎,一旦有利可图就会背盟弃约,即便墨迹未干也会旋踵变脸,即便存在违约金惩罚也会食言自肥。
十年,我以十年回答“武树臣之问”,这是我对北京市法学会包括武树臣教授在内诸位前贤青睐相加的一个交代,对于这一问题真真切切给予自己力所能及的满意回答,至少让世人不再迷茫于斯,这对我而言恰恰正是真正要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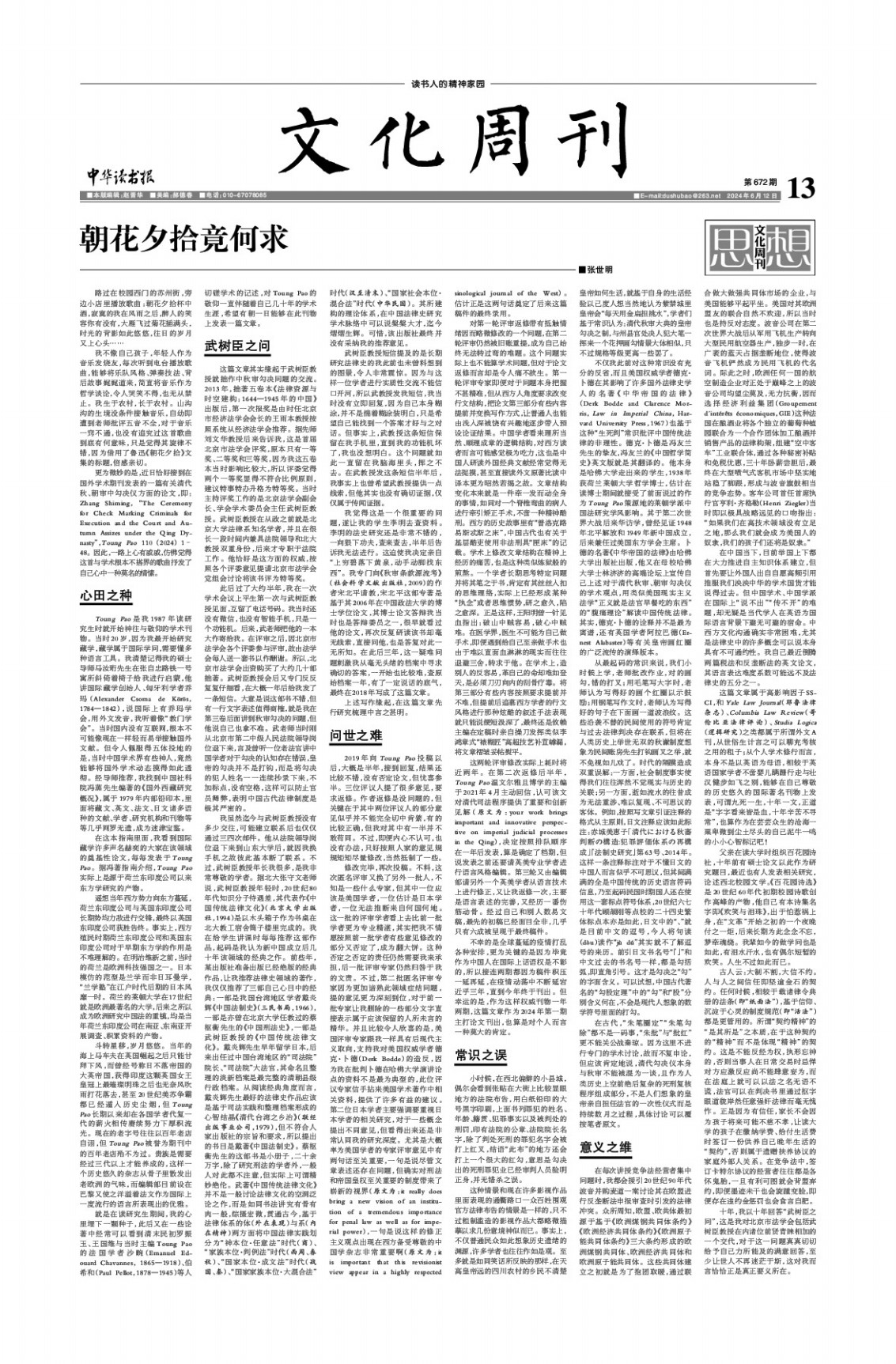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