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川
《试上高峰窥皓月》适合有一定古代诗词积累的读者来咀嚼和回味。该书让人想一气读完,难以停止。这种体验来源有二。
其一是作者的语言。“爽快”,这恐怕是阅读中读者的第一感受。该书评价楚辞:“楚辞都不适合消遣着读,消遣,最宜读六朝文、宋元笔记、明清小说。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孤愤忧闷之情,去国离乡之思,高蹈狷介之性,浓丽琦诡之辞,成就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包,读来并不轻松,故而才有痛饮酒、抚案击节之说。”其评价《古诗十九首》:“在聚会和别离之间,在传说和现实之间,在放任与恪守之间,在享乐与苦旅之间,在伤逝与惜时之间,在游荡与思念之间,说不尽的明月皎皎,写不完的古道悠悠,看不够的草木青青,诉不清的别情依依。江边,楼上,征程,宴饮,情至深,而境绝清。来自民间的吟哦,自不同于‘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造诣,这是浑金璞玉,天生丽质。”该书喜欢用短句、用排比,让人感觉“爽如哀梨,快如并剪”。这其中,有作者抑制不住的情绪,也是他“半掩琵琶”的才情显露。如后段中,“说不尽的明月皎皎,写不完的古道悠悠,看不够的草木青青,诉不清的别情依依”,便分别来自《古诗十九首》中的诗句——“明月何皎皎”“悠悠涉长道”“青青河畔草”“胡马依北风”。叠字既是作者心绪贴切的表达,也是他从诗词中汲取的养分,因为在《诗经》、小谢等章节中,该书明确注意到了诗词中使用叠词的艺术效果,这应该是有意为之。
其二是书中谈及诗人和作品后世影响和传播时,快速的“时代更替”。该书副标题是“中国古诗词的阐释与形象传播”,其中的形象传播必然要跨越时代。如“诗仙、诗圣形象与传播”部分,要用几页纸呈现李白和杜甫的后世印象一定极富挑战性。该书先谈本朝,再从宋到元,自明而清,材料来源有诗话、笔记、戏曲、绘画,以此论及李杜地位升降和二人在后世的评价与形象演绎,虽不全面细致,但也“大体如此”。纵览历史长河,难免“浮光掠影”,但书中每一部分的传播和形象梳理,反而形成“延时摄影”的效果。不知道是作者的广告学背景有意为之,还是篇幅所限的不得已而为之,但在阅读效果上,我们分明看着一个个诗人形象闪现而出,一个个诗人背影飘然离去,纵眼千年,不禁感慨。
该书丝毫不掩饰个人化特征。比如选篇,“把杜甫、白居易打入冷宫,把《长恨歌》《春江花月夜》搁置起来”,舍弃名篇对于文学简史是存在明显的缺陷的,但该书依然“耿直”地选择了个人更喜爱的诗词;又如目录,在“形象研究”“诗歌阐释与传播”的节标题后,既有“何逊而今渐老”“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样的前人名句,也有“惊鸿,又见惊鸿”和“明朝那些不怎么样的事儿”这些对武侠和流行书的戏仿,不禁让人沉思中夹杂莞尔。
最能体现作者古代诗词素养的,莫过于该书中对诗词的阐释和解读。其中颇有些段落,让人到中年的读者也会感动。比如《豳风·七月》,这首诗早有先贤前辈论说多年,该书则称这首诗“妙在‘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样的句子。仿佛千年前的蟋蟀声,穿越千年的旷野,穿越千年的秋风,在我们耳畔回响”。短短几句,耳畔仿佛真的有蟋蟀声起。再如该书解读《郑风·女曰鸡鸣》的“闲言碎语”:在两千年前的农家小屋里,天还未放亮。女主人在枕边轻声说:“鸡叫了。”男主人还在半睡半醒之际,随口答了句:“天没亮呢。”还是禁不住女主人的温柔唠叨,起来看看吧,还有明星挂在天边。女主人说,起来啦,去打个水鸟飞禽,拿回来帮我弄个下酒菜。等我收拾完厨房也和你一起喝两杯,轻抚琴弦,深情款款。
读至“轻抚琴弦,深情款款”八字,让人瞬时心动、会心微笑。
该书对自己深有感触的篇章会尽情挥洒笔墨。如对庾信小诗《寄王琳》的分析的着眼点,该书认真提出:“独下千行泪”在拆信之前,还是拆信之中,还是拆信之后。接着,先荡开笔墨从庾信处境谈起:“思乡是亘古的话题,除非到了现代后现代,人已经失去故乡。尤其是庾信这样,去国怀乡,其思更深,其情更且,何况关山难越,鱼雁罕至。今天突然有故人书信到,内容是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竟然、果然还有人惦记着自己。这封信,应该经过故人反复摩挲、书写,再在邮差身上,几经风尘,方能从江南到达塞北,这不仅是收信的过程,简直是盛大的仪式。”所以,其得出结论,“这一封满载征尘的信”,“瞬间撕开情感的缺口,难以遏制,以至于泪落千行”,“到这时,信中写的什么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千山万水之外,依然有人念着自己”。也只有离乡背井、情感丰富之人才能体察如此细腻,分析如此入微,料想作者也应该是羁旅离家之人。
该书对诗词的丰富感受来源于其极高的艺术素养。论及柳宗元《江雪》一诗,其提出对于“山水”的理解,说明“中国绘画有‘眼中山水’和‘胸中山水’之说,中国的山水画表现的从来都不是一时一地的具体景观,而是画家游历天下、遍览群山之后,经过艺术的整合加工之后形成的山水意象”,非精熟和理解山水画理论奠基者王微《叙画》之人,不能做此论。该书不赞同程千帆先生的“虚构”“并置”之说,只有阅读程先生《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一文后才能有这样的结论。正是在此基础上,该书认为“苍天之下,群山之间,孤舟之中,蓑笠之内,就是渔翁自足的世界”,“这不是诗人的倔强,而是诗人的深情”。这一结论,才发人之所未发。
笔者在大学讲授“古典文学精品鉴赏”课多年,也读过几本批评类书籍,深知批评领域里对作者与作品、作者与读者、读者与作品其间复杂纠缠关系的种种争论。该书对这种争论了然于心,虽然宣称“更希望大家以情感为线,走一遍古诗词的长河,看一看几千年累积让我们感动不已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但即使通过 目 录,也能体会到其“野心”——用自己的理论重写文学史。其重写不在于诗词的选篇,“不刻意回避教科书、文学史上提到的名家名篇”,“不刻意挑选除非专业研究者才可能知道的冷门作品”,而在于努力以这本书实现对“古诗形象学”理论的建构。
该书引《意图谬见》说“以诗人本意解诗,则把对诗歌的研究,折腾成对诗人的研究,实为迷途”,又说强调读者感受是“感受谬见”。我们对此自然会思考:自小在语文课上学习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到底有几分道理? 这作者到底是“已死”还是“未死”?该书花大篇幅阐释“形象学”,“文学人物是形象,诗集、流派、时代都是形象,形象包含接受学和阐释学意义上丰富的信息”。其不满于当代文学史在写作中“纪传体”和“例证法”的相加模式,以尧斯的接受美学为思考起点,自伏尔泰、伽达默尔处得到启示,从巴柔、王一川的形象学演绎出“古诗形象”这一概念。
中国诗歌发展史,本身也是形象不断建构的历史,“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塑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这是对地域和地域文学形象的精彩概括;“曹操如幽燕老将,曹植如三河少年”,这是对诗人形象的诗化表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这是对诗集形象的精准评价;“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这是对时代形象的鸟瞰批评。
这段话是我们理解全书最直观也是最便捷的钥匙。无论诗人、诗作抑或是时代、地域,批评史呈现给我们并在内心留下的印象,往往是一句“一言以蔽之”。这种标签似的概括,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却能标志性存在和快捷式传播。
著作的每一章的标题都是一句“一言以蔽之”,也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先秦遥深”“秦汉巍峨”“魏晋风流”“南朝春意”“盛唐气象”“宋元写意”“明清悲喜”,虽然对特征的概括都只有简单两个字,但却完全合乎世人对于这一时代的印象。正如同刘熙载评价唐代边塞诗代表人物岑参和高适的特征是“岑超高实”,虽然简单,却已恰切。每一章的第一节,该书都郑重地称为“诗歌形象研究”。其中有《诗经》这样的作品集,有“竹林七贤”这样的群体,有“宫体诗”这样的诗歌类型,还有明清这样的帝国王朝,该书都在力求从后世感受上描摹出他们给人的印象——虽然片面,但却生动的印象。
客观说,书中对于诗人形象的描画最为成功。比如“宋元写意”一章写苏轼,该书引仁宗、神宗、胡寅、陆游、鲜于必仁、袁中道等人的评论和作品,基本呈现东坡在后世的剪影。但对于“宋诗简史”的大笔勾勒,就显得有些潦草,未能呈现宋代诗词内容的丰富和风格的多样。统观全书,人物、群体或者相对时长较短、特征集中的时期,容易呈现形象,但对时段长和人物多的繁复形象,则会挂一漏万,这也是全书追求“痛快淋漓”的阅读感受中必然承受的,作者想必也有思想准备。
古往今来,人们尝试着无数条探寻中国古代诗词幽深奥秘的道路,这一本充满个性的论著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书的作者说,金圣叹点评《六才子书》,冯镇峦称“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读完这本书,对于笔者而言,也是如此。包括笔者在内,每一位读者恐怕都会对该书的一些篇章、段落或者话语“心有戚戚”,实际上作者成功达到了写作目的,因为这本书的形象——也已经建立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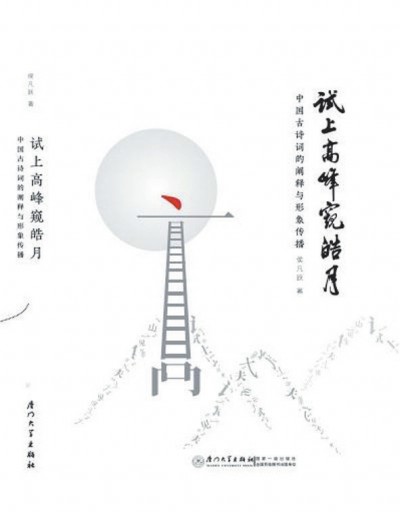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