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需要许多驳杂的识见,需要对社会的透析,对作者而言这些是极为重要的考验,毕竟故事由细节组成,情节展开要有不同环节,这些都是生活中所见所闻的再现。十多年前我在书店读过一段《古董局中局》,感觉马伯庸对细节和故事有较高的把控能力,很能引人入胜。若从技巧来讲,写小说最难的是人物对话,因为人物讲话的语气很难用文字来复原,高明的小说家都善于处理故事中人物对话。如果说作品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相比之下,生活中的对话则是高于作品,许多影视剧作品中人物对话十分做作,阅读和观看都不够精彩,正可说明其难度。据说好莱坞电影中人物对话有专职人员来写,这是一部电影成功的关键,小说可以通过文字描写来介绍人物及其背景,电影则只能靠对话来完成,可见其重要。我曾在文章里谈过关于写作的话,写随笔散文,需要大量的藏书或阅读笔记,有无社会生活并不重要;但写小说,可以家徒四壁,需要极高的想象力,需有社会经历,或曾被社会伤害,譬如高尔基,譬如张爱玲。由此可见,写作是天赋,时代不同,展示的天赋也不同。
若从马伯庸《古董局中局》说来,由现实社会小说进入到现实穿越写作,这些年一气呵成《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太白金星有点烦》《大医》《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风起陇西》《三国机密》《龙与地下铁》,大约每年一部小说的写作速度,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历史,用现代的眼光重新构建历史事件,同时也印证了“历史即为当代史”的名言。在古代的故事中,穿插当今社会和现代职场的种种现象,使之读懂古代即看清当下,因此,他的小说或写作形式,很符合今天的现实,能够获得大众的共鸣。常言道士不可以辱,贩夫走卒也不可以辱,早年读《增广贤文》有言“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殷殷可鉴,倒是应该时时提醒自己,保持内心的谦逊。马伯庸的新书《食南之徒》依然借古说今,他在《后记》里说:“本文的起源,是《史记》的《西南夷列传》里的一段记载”,由区区百余字阐发出一本长篇小说,背景放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将赵佗拥兵自重、独立为王的南越国,意图借美食来讲叙地理和疆域,故事的发展、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叙,都为作者面壁虚构,但所有的古代叙述读起来都与现代平行交替,看到的是现代的景象,像“吃到嘴里的遗憾,总比吃不到嘴里的完美要好”这种现代流行语,出现在古人的对话中,打造唐蒙美食家的身份,是颇为大胆的人物设计,用古人的做派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没有阅读障碍,给人轻松之感,也可坦白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凡是让人阅读轻松的书,都存在畅销的理由,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即所谓“抓住点,发现梗”,有悬念,有答案。畅销书作家的作品能够畅销,一定有符合大众心理和大众阅读的需要,这是一代人对同时代的观察,也是不同时代所具备的不同需求。马伯庸《太白金星有点烦》也是如此,从职场的角度重新捏拿西游记,但凡普通阶层的打工者,都会从中读到现实里的痛点,发出会心一叹。
从时间推移来说,我对现代这类现实穿越的小说阅读不多,主要还是与所处的阅读换代难于衔接。毕竟事物是立体且复杂的,不会只有一个正面。这样说来,马伯庸这些古今穿越的写作方式,反而能够成功抓住公众的痛点,将一些社会问题替换成大众的平常心,不激励不张扬,给你一个故事,讲点平实的道理。这也可以谈及写作和阅读的目的,作为一名畅销书作家,对题材的把握和处理,在书籍已成快销品的今天,还是印证了那句老掉牙的话,生活是最好的创作来源,经典是永不过时的教材。每一代的人都以自己的价值尺度重新解读经典,寻找生活的意义,活着的意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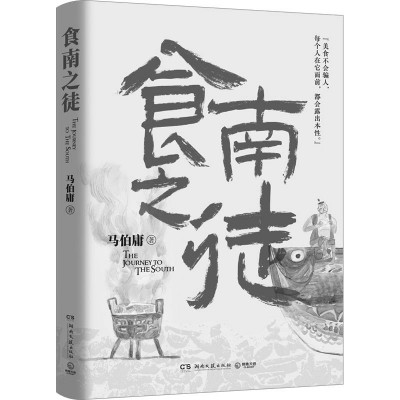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