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婉约
得知自己荣获2024年中国翻译协会评选的“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自是欣喜。第一部译著的出版至今竟然已经25年了,不禁回忆起翻译往事和点滴感想。
互为表里的学术翻译与学术研究
1999年,我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译著——吉川幸次郎的《我的留学记》。那时,我正在准备博士论文《内藤湖南研究》的写作。作为内藤湖南的学生、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的第二代重要学者,吉川的学术生涯和著作,早在五年前我访学京都大学时就很受吸引。我从二十多册的《吉川幸次郎全集》中选辑编译了这本书。以他晚年学术对谈录《我的留学记》为主体,加入一些他的学术性回忆小品文,以及关于中国文学史、诗史的经典论文组成,书名就沿用了主体部分的《我的留学记》。这本书的编译,让我对吉川的学术概要和风格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而且吉川晚年对京都大学老师们为人为学风采的回忆叙述,帮助我对京都学派的学风特色有了更真切的体会。我随后撰写博士论文时,对相关内容亦有引用和辨析。
就《我的留学记》的编译而言,选定了翻译文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工作的大半,至于翻译本身,因为已经初步读过,我记得只用了一个寒假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连在由武汉到南京的长江轮上,也在埋头写下译文,悠缓的水上旅行因而变得富有效率而有意思。这本书出版后,叶兆言、韦明铧等专家及不少其他读者,都写了读后随笔和推介文章。这让我知道,翻译出版此书帮助的不仅是我个人的学术。体会到这一点,对我此后继续做翻译是一个鼓励。
2006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这也是一部学术性的辑译著作。书中收集了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
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日本学人来中国做学术踏查、访书购书的文字。内容比较有学术性,偏向古籍版本、文献流传等专题,但同时,因为有访书者本人在中国的经历和感受等游记色彩而增强了可读性。说起来,做这本书的缘起是时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北大校友徐雁教授约请我翻译长泽的《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当时他正承担着“中国古旧书业研究”的国家项目,我也想借此机会深入地接触、了解长泽这位文献学家,所以就一口答应了。翻译完长泽,我被这类文字所吸引,于是在北大图书馆、北外日本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处寻寻觅觅,以来华日本学人为目标,借阅他们的全集、著作集或单行本,搜集关于学术调查和访书买书的记录,渐渐凑齐了书中的这六位访书人物,“近代日人来华访书”也一时成为我的研究选题。翻译此书时,我正在给北语研究生上课,课上的宋炎同学主动请缨,也想练手承担翻译任务,我就把搜捡到的待译资料分给她一半,她都认真完成了。经我审订,统一文字,书稿很快定稿了。
没有想到的是,此书出版以后,受到相关领域的专家好评,南开大学文献学专家来新夏前辈写了书评专文《他们不仅仅是淘书——读〈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并将这本书
作为他博士生培养的必读书。马敏、董炳月等专家学者也写了书评在报纸上刊出。此书在出版界和藏书爱好者中也很受欢迎。后来,此书的增订再版本在九州出版社出版时,孔夫子旧书网买进二百册,请我签名售书,孔网缔造者和老总留饭,并请我去他那收藏丰富的藏书楼(公益开放的“杂书馆”和收藏功能的“国学馆”)参观交流。聊天时,我目睹他当场检阅、鉴定刚收来的一册古籍。
我还翻译出版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通论(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桑原隲藏的《东洋史说苑》(研究生王广生承担一半翻译初稿,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研究生贾永会承担部分翻译初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每一种都与我的教学科研有关,可以说是我学术积累的一部分和学术推进的原生力。
跨文化的桥梁与学术的结晶
身为大学老师,在当前中国大学的教学科研氛围中,多少都能感受到来自各个管理层级的“唯著作论”倾向。对于不是外语类专业的老师来说,更是这样。教科书和译著通常都不认定为学术成果。出版了两三种学术翻译著作以后,不止
一个前辈老师都从爱护我的角度出发,建议我少在翻译上花工夫,那只是“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但我自己仍有点乐此不疲,做了日本中国学研究这个专业,对于日本人中国研究的经典著作应该有深入的研习和把握,这是从事研究的基本功与出发点,翻译正是达成此项基本功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看到令人敬佩的日文研究成果至今尚未介绍到中国,感觉有可能的话将它翻译到中文世界,能够做这样的学术文化桥梁,自己也不无满足感。这是我选择译介《长安之春》和《东洋史说苑》的原因。
《长安之春》考据繁博、文字优美,在日本的东洋学发展史上影响很大(日本东洋学,指明治中后期以来日本人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学问领域。此书增订版为《东洋文库》第91种),更是有关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经典著作。这样一本书,在中国,除了民国时期有两三篇译文发表在期刊上外,始终没有中文译本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帮我解决了向日本岩波书店商购版权等事宜,促成了本书在国内的顺利出版。书中所涉及的西域各民族语言文字及专有名词、近现代欧洲汉学家西域研究成果等,包括作者文后所附的繁博注解,对我来说,难度超过了此前的翻译。我有一个习惯,在翻译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会“第几页第几行”地将原文记录在笔记本上,不时拿出来再琢磨琢磨,积攒到一定多的条目时,统一请教相关专家或日本友人。《长安之春》翻译是积攒问题笔记最多的一次,还请教了东语系、德语系的教授。
《东洋史说苑》是京都大学教授桑原隲藏的讲演录,在日本中国学发展史上可谓里程碑性质的著作,也曾是一本学术畅销书。在日本近代研究中国的学者中,就所体现的西方学术视野和批判意识,桑原隲藏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对于东西方文明的态度、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论点,鲜明地体现在书中关于中国文化、习俗、人物、宗教、时事等的一系列讲演中。翻译过程中深入玩味、体察作者的观点,为我撰写发表新时期以来国内最早的桑原隲藏论文奠定了基础。
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
近年来,机器翻译越来越普及和便捷,在日常交流、工作沟通等方面,确实表现出解放和超越人工翻译的趋势。社会上学习外语、报考外语专业的热度似乎因此而降低不少。那么,熟练掌握外语,进行人工翻译,还有社会需求和文化学术价值吗?
在多年翻译实践的过程中,我
也比较关注前辈学者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家的经验谈。翻译涉及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在概念运用、理论表达与情感表述等多个方面的传递,尤其是翻译“文学性”较强的,如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独具个性化风格的作品时,涉及译文的文风问题,前辈翻译家与翻译研究者多有提到。从“信达雅”的评价标准,到选择“归化”或“异化”的手法,广为人知,也规范着从事翻译的人的目标追求。这些规范不知能否要求机器翻译也如此这般地做到兼顾传递“风格”与“神韵”的程度。在人工智能日益发展进步的今天,这确实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相对来说,学术翻译似乎简单一些,不必太注重词句表达的情感色彩和文风特色,照直翻译就可以了。机器翻译,大概就是所谓“照直翻译”的表率,应该能愉快胜任吧。但另一个问题是,学术著作中大量存在的专业性名词术语、学科性表达、逻辑性推演等,是对机器的另一种挑战。它往往要求译者具有专业理解力,在对原著加以理解性释读的基础上进行翻译传达,必要时,还需要对一些名词术语做专门的注释疏通。能否要求机器也做到这样的理解性释读翻译呢?
诗人余光中也是散文作家、学者和翻译家,曾在大学中文系担任“翻译”一课,积教学和批改学生翻译的所思所得,写成《翻译乃大道》一书,很值得中文系师生一读。翻译是否够得上称为“大道”,就目前学术界的认知来看,恐怕还未能乐观地说一定就是。或许只有视文字表达、语言艺术为终生志业的专业人,才更能体会那种心怀敬意、辛苦耕耘、字斟句酌的“达道”历程吧!俗话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书既出,其中的错误、欠妥、不够完善之处,也是白纸黑字地难免存在。所以,我把这篇小文题为“翻译得失寸心知”。
(本文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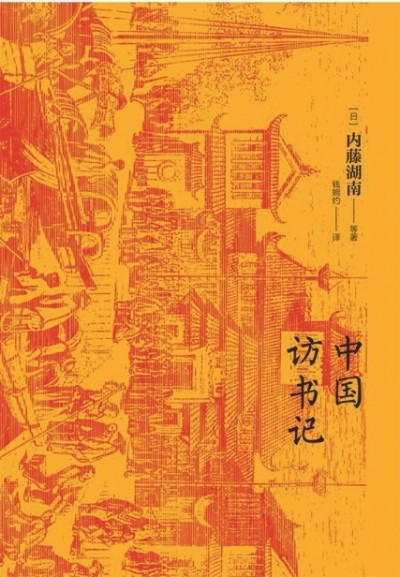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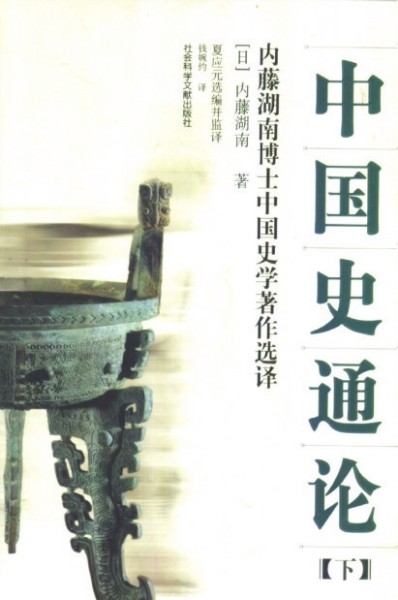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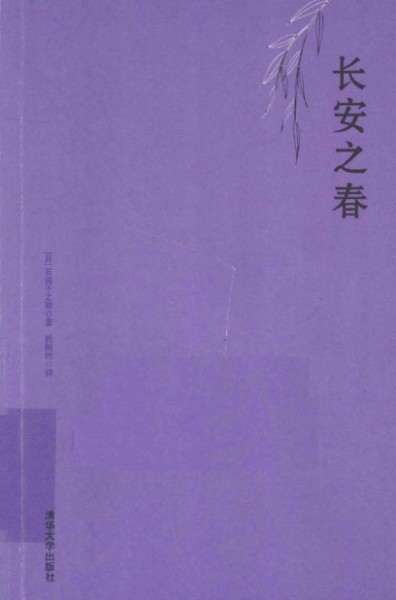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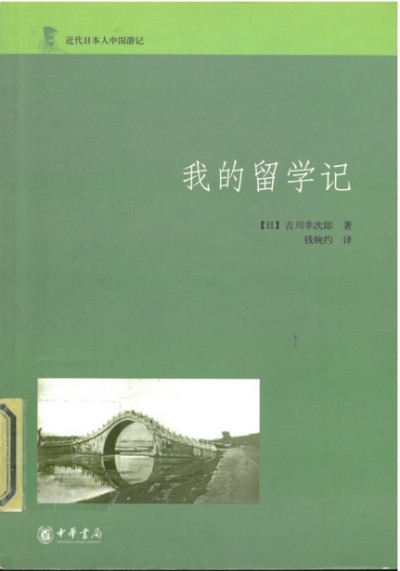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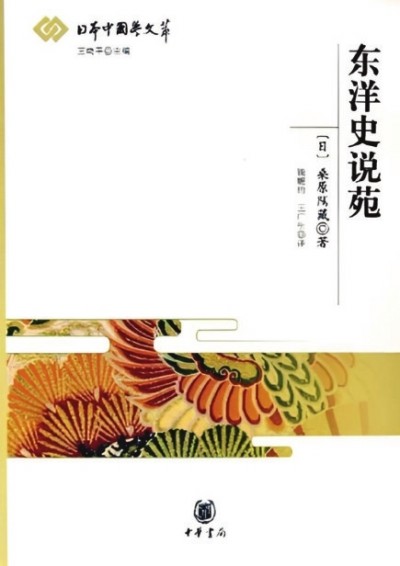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