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刘兵
江:
虽然这本书是讨论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无知(ignorance),而且虽然作者努力采用通俗表达,但他似乎打算“将抽象进行到底”,书中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案例,纯粹从概念到概念,当真是一本非常“哲学”的书。不过,由于“无知”这个概念通常不会被人们注意(我们一般只在修辞的意义上使用“无知”一词),更难想象有人竟会为此专门写一本书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所以此书还是有它的吸引人之处。
为了冲淡本书的抽象色彩,我决定不再循序渐进,而是尽可能选择书中某些通俗易懂的内容出发,来进入讨论。在本书第三章第4节,作者居然引用了一段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 Rums⁃feld)的话:
存在着已知的已知: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存在着已知的未知;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还存在着未知的未知——那些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虽然本书译者潘涛编审(哲学博士)一定在译文上已经绞尽脑汁精益求精,但上面这段话念起来仍然很像某种绕口令(这既不能怪译文也不能怪原文,要怪只能怪作者讨论的内容太抽象太冷僻)。当然,这段话的意思还是可以正确理解的。作者认为,拉姆斯菲尔德关于某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断言是正确的,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但不可实例化”,因为“根据定义,我们甚至都不能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但是,我们真的无法提供这样的例子吗?
刘: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说很有意思,倒不是说作为哲学讨论作者的论述是否特别出色,而是说在阅读它的时候,觉得会带给人们很多启发,让人们去思考以前很少甚至不会去深思的一些问题。
以往,在最常见的观念中,人们通常会认为无知是不好的,人要学习,就是为了要改变无知的状态。而一般的哲学的认识论研究,也主要是关注如何去知的问题。此书作者在书中应该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有关无知的各种研究和各种观点,作为哲学讨论,我觉得作者还是尽量努力以通俗的方式来进行介绍的,但毕竟哲学总还是烧脑的思考,要完全彻底地讲通俗故事,那肯定难免庸俗或是戏说。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当哲学家们把无知当作直接的对象来思考和研究时,这个对象的复杂性要远远超过对如何获知的讨论。你上面引用的那样看上去像绕口令般的说法,其实在书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其中仅就对无知的分类而言,类似的讨论就极其复杂了。
对于你引用的“未知的未知”,你提问说“我们真的无法提供这样的例子吗?”从逻辑上讲,似乎也还是成立的,否则,如果真能提供具体的例子,那就不是“未知的未知”了。
在阅读时,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即此书出现在“哲人石丛书”中的原因。当然,对于认知的哲学研究的普及,也可以归入到最广义的科学传播的范围。不过,像这样的哲学理论,作为一个视角,一种工具,也还真是与科学传播或普及有着很直接的关系呢。比如愚昧背后隐藏的不就是某种“无知”吗? 而当我们像此书作者那样去思考无知问题时,自然会发现结论显然不是“是”或“非”那么简单。
江:
不过,只要我们不局限于本书作者设置的“第一人称”思路,为未知的未知(无知)提供实例还是有可能的。出路即在于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的视角转换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样的例子在学术翻译中就不难找到,下面是我十几年前就注意到的一个实例(那时我还没关注过对无知的分析):
史蒂芬·霍金在《大设计》一书的第三章中,讨论外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他表示,他认同一种“mod⁃el-dependent realism”。在最初发表的译文中,这句话被译成“依赖模型的现实主义”,这就构成了一个“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的案例。
假如译者不认识“realism”这个词,他去查字典,在一些常见的小型字典中确实只有“现实主义”一个义项,但如果去查稍微大一点的字典,就会看到第二个义项:“(哲学上的)实在论”。然而因为“realism”是一个相当常见的词,译者早已熟知它的“现实主义”义项,他不认为自己还有必要去查字典,同时他不知道它的“实在论”义项——如果知道,那么此处霍金是在讨论外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哲学问题,显而易见应该使用第二个义项“实在论”。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就是一个“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的实例。霍金这句话的正确译法应该是“依赖模型的实在论”。
不过,“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和“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毕竟不能完全等价,因为对于某人知不知道某事,最权威的依据通常被认为是他本人的陈述。当他本人说他知道或不知道某事时,通常总比旁人的判断更可信(审讯犯人的情形除外)。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提供了一个本书作者认为根据定义无法提供的可能的实例,这对于我们理解“未知的未知”好歹能够提供一点帮助。
刘:
你举的这个例子确实是很有趣的。不过,在此书中,作者确实针对无知的各种分类组合进行了很详细的说明,并且都给出了有关各家不同观点的介绍和评论。在我们这里有限的篇幅中,实在是无法一一说明这些,而且那样做也未免有些过于烦琐,过于哲学化了。在这里,我还是更关心可以在哪些科学传播的问题上将这些对无知的研究诉诸应用,以及可以带来一些什么新的思考。比如,前面我提到的问题即是其中之一。
又比如,其实,人是不可能“全知”的——通常人们认为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能力。而人既然不可能全知,就包括了必然存在无知的部分。我们的科学传播,过去强调知识,现在强调素质,但无论如何,就算是关注素质,也还是不可能完全摆脱知识这个脚手架。即使在知识之外,也还是存在着对更多的知的追求。
那么,在传播中,在教育中,是否知的越多就越理想呢? 如果人们一定会对许多东西无知,而且知识的部分总是有限的,那又应该如何确定知的理想限度? 如何选择让受众知道哪些,以及对哪些无知? 这里既涉及知的量的限定,又涉及对需要知的内容的选择。也许,对于后者,选择正是不同的科学观和传播观所决定的。对于前者,也即要知的东西的量,似乎在默认中,往往被想象为知的越多越好,但真的这样就合理吗?
从无知的视角来看,这种在教育和传播中对于要知的量,以及要知的内容的选择,就成为可以深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了。这样,问题似乎就不仅仅涉及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而是延伸到价值观了。
江:
你关心的问题虽然不是本书作者致力于讨论的问题,但确实也很有意义,这应该就是本书的启发功能的表现了。
毫无疑问,人们有权选择自己想要获知的知识,也有权让自己对另外一些事物保持无知状态。考虑到对每一个个人来说,他无知的事物永远大大多于他能够获知的事物,这种权利就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了。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经常处在行使这项权利的状态中——比如选择不学什么专业(这在本书中被称为“理性无知”)、不从事什么职业、不阅读什么书籍、不接受什么信息等等。
你一直对科学传播有着浓厚兴趣,本书又让你思考一些与科学传播有关的问题了。对于你上面提到的问题,我感觉首先要解决“科学传播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将直接导致对科学传播内容的选择。
让我们假定,科学传播的目的是“唤起受众对科学的热爱”(这肯定是许多传播者都乐意认同的目的),那么显然,传播的内容中,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中所揭示出来的许多与科学有关的负面内容就不宜传播了,科学中那些过于抽象或非常复杂的内容也不宜传播了,传播者就会希望受众在这些方面保持无知,至少自己不去打破这些无知。传播者可以毫无道德负担地认为:让受众在这些方面保持无知是应该的,是有利于科学传播的。这就给出了你上面提到的问题的一种答案。
刘:
关于面向公众的传播回避涉及科学的负面内容,还有不同的情况。其一,是传播者本身就不关心这些,因而也不去知晓,这也就形成了一种无知,那么,在向公众传播时,当然就不会去传播这些对传播者来说是无知的东西,这样的传播结果,也就造成了公众在这方面的无知。其二,也许传播者是知道这些内容的,但因为怕影响公众“对科学的热爱”或其他一些理由,刻意地不向公众传播这些内容,颇有些“不可使知之”的刻意“愚民”的意味,当然,最终的结果也还是使得公众在这方面保持无知。在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况下,传播者自身的知或无知的背景,以及其立场和选择,都带来公众的某种无知。
于是,这里就带来了价值选择。在前一种情况下,传播者是否可以被原谅呢? 难道我们在确认传播者的资格时,不应该要求他必须对此有知吗? 在后一种情况下,传播者刻意不传播某些他知晓的内容从而导致公众的无知,这在伦理上合理吗? 由此可知,讨论无知的问题及相关理论,就不仅是认识论的纯哲学问题,而是肯定会牵扯进来更多比如价值判断、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目的、手段等一系列的复杂因素。
江:
确实如此。例如本书第七章“无知的伦理”,在第3节中讨论了“不知情权”,就是一个高度涉及伦理和心理的问题。
我以前在文章中就谈过,世界上有一些隐私,严重到自己也不敢窥看的程度——自己的健康状况及其前景,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隐私。我本来只是从科幻作品中演绎出这一结论的,但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在西方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如本书所说,“不知情权如今很大程度上在生命伦理情境里被表达和维护”。
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Genome and Human Rights) 中说:“每个人均有权决定是否知道一项遗传学检查的结果及其影响,这种权利应受到尊重。”在现代医学过度检测、过度治疗愈演愈烈的今天,“不知情权”这种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被称为“讳疾忌医”的态度(不想知道自身医学检测的结果),居然已经到了需要保护的地步。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作为单位福利的年度体检,似乎也为这种情形提供了旁证。
总体而言,本书虽然比较抽象,但在我们习惯的“求知”叙事之外,从“无知”入手展示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还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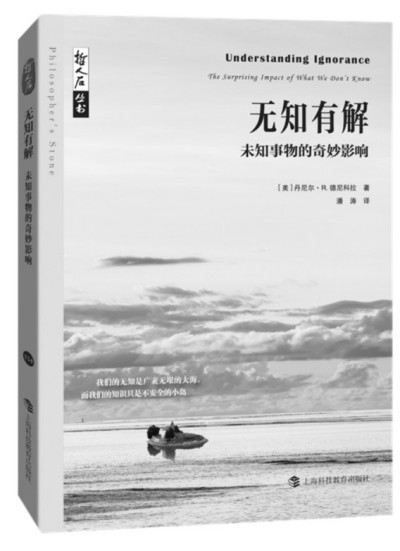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