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巍
在英帝国雄赳赳走向“日不落帝国”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与堆满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报告的英国外交部、殖民部、海军部、陆军部、商务部和皇家地理学会不同,也与同一时期的英国小说和游记的层出不穷的“海洋题材”和“域外题材”不同,英国的历史编纂学似乎退回了简·奥斯汀的时代,开始像这位女作家一样关注英国本土人物和风物,要在“两寸见方的象牙板”上仔细书写“一个村子的三两户人家”的故事。
英国历史编纂学的这一转变,与英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此前,英法争霸多年,但欧陆(尤其法国)的历史编纂学对英国历史学家发生着重要影响,把英国史视为欧陆史(即“世界史”)的一个延伸或边缘部分;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一跃为霸主,不再忍受英国的历史学家们言必称希腊、动辄说罗马。1838年,在英印政府担任殖民高官多年的托马斯·麦考利返回英国,次年便着手五卷本《英国史》的写作,但到1848年才出版前两卷。这不能完全归结为他公务繁忙(先后担任军务大臣、财政部主计长等职),因为直到他动笔两年后,他才找到一套有关“现代史”的史学理论,来颠覆此前一直深刻影响英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认知方式的欧陆历史叙事传统。1841年12月,三卷本《罗马史》的作者托马斯·阿诺德被钦命为“牛津历史教授”,他在就职演说中呼吁英国历史学家要以英格兰为中心来撰写英国史,认为“现代史”就是当今的国家史,“在古代史与现代史存在一道真正的界线”,这一界线就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当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发端于西罗马的灭亡”,“此乃活人的传记,而此前均为死人的传记”,然后他谈到英国:
“这一点,最清晰地见于我们这个岛国。我们的历史开始于萨克森人到来之时。布列吞人和罗马人曾居住在我们的国家,但他们不是我们的祖宗;作为人类,我们的确与他们有着某种联系,但就民族来说,凯撒的征服史与我们不再有任何联系,正如那时栖息在我们森林里的动物的历史与我们毫无关联。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其种族和语言已经从地球的一端扩张到了另一端,但它们是在萨克森人的白马在特威德河与塔马河之间[即英格兰——译者]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时候开始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血缘、我们的语言、我们国家的名称及其区划以及我们的一些制度的起源,追溯到彼时彼地,我们由彼时彼地扩大我们的民族认同,历史到彼时也才是现代史,因为从彼时发端的历史至今没有泯灭。”
“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其种族和语言已经从地球的一端扩张到了另一端”,指当时正在进行的鸦片战争,英帝国藉由这场战争,将自己的殖民势力从印度殖民地扩大到“地球另一端”的东亚。作为罗马史专家,托马斯·阿诺德深知,帝国迅速扩张将带来一个问题,即越来越远的帝国边缘对帝国中心的认同衰减,因此,“英国史”的目标是要使分散在地球各处的英国人不仅要心系帝国的中心,而且要在帝国的边缘——那些遥远的通常互不相连的殖民地——复制帝国中心的语言、习俗、趣味和制度。这后面一点,麦考利可以说是先行者,他在担任印度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次年(1835)即在《教育备忘录》中提出“东方教育计划”,终结了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英国人对“东方语言”的痴迷以及东印度公司以“东方语言”作为进入东方贸易的语言门槛的做法,将英语作为印度教育语言和官方语言,以“尽我们所能,在印度培养一个在我们与我们统治的千百万当地人之间充当翻译的阶层,一个印度血液和肤色但在趣味、意见、道德和智识上英国化的阶层”。
印度岁月对麦考利的《英国史》写作也是一种助推力,作为殖民官员,他必须考虑如何在帝国的边缘产生并维持一种对帝国的中心的向心力。这一点也直言不讳地体现在1848年出版的《英国史》前两卷的前言中:
“在许多人内心,在君主的伟大与其统治的国家的伟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强大的联系。英国的几乎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带着一种兴高采烈的心情,对英国的外来统治者们的权势和荣光不吝笔墨,并哀叹他们的权势和荣光的式微是我们国家的灾难。这太荒诞了,他们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海地黑人,出于一种国家自豪感,浓墨重彩于路易十四的伟大,并带着一种爱国主义的遗憾和羞耻,谈论着布伦海姆战役和拉米伊战役。诺曼征服者及其直到第三代的后裔都并非英国人,他们大多出生于法国,在法国度过了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光,他们的日常语言是法语,几乎每一个高位都被法国人占据,他们在欧洲大陆获得的每一个东西都使他们更加疏离于我们这个岛国的人。的确,他们当中最有能力的统治者之一曾试图以迎娶英格兰公主的方式来获得他的英国臣民们的好感,但他底下的贵族们看待这场婚姻的方式,与当今的人们看待弗吉尼亚的一个白人农场主与一个混血女子之间的婚姻不相上下。”
这哪里是英国史,分明是欧陆史或法国史,他因此断言:“在诺曼征服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不存在英国史。”英国史只能始于当今英国人的祖先萨克森人来到英格兰之时。值得玩味的是这里突然提到“我们时代的海地黑人”,以比喻当今那些“法国化”的英国历史学家。海地1804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获得了独立,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如果海地黑人在当家做主之后,还继续使用当初殖民统治者的历史叙事,那将是荒诞的。不过,对麦考利来说,这种比较只是一种修辞策略,因为他本人提出的“东方教育计划”就是要在东方推行“英国化”教育,让东方本地上层阶级的子弟日夕沉浸在十六到十八世纪的英国语言和文学中,日夕诵读莎士比亚的剧本、弥尔顿的长诗和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以这种古风盎然的英国文学,使受教育的印度人日益疏离于印度语言、说印度当地语的印度人民以及印度和世界的当代问题。
不过,以这种方式谈论“帝国”与“民族-国家”,还只是点出了“帝国史”与“民族-国家史”发生的分离,不是《帝国的想象: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一书的关键意旨,正如该书《导言》所说,该书侧重于挖掘“仿佛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纪’”的二十世纪的“帝国与民族-国家的纠缠”:
“历史学家往往以孤立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叙述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抹去民族-国家的帝国印记以及它与帝国相互重叠和纠缠的‘前史’,来服务于民族主义政治的现实需要。然而,近年来的史学研究则尝试在全球史网络中考察东西方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掘它们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彼此连接构成的复杂关系,并对过度依赖民族-国家视角的历史编纂学原则,即所谓的‘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做出质疑、反思和挑战。”
英国左翼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习惯于给法国大革命后的每个“年代”贴上一个鲜明的标签,于是“1789-1848”是“革命的年代”,“1848-1875”是“资本的年代”,“1875-1914”是“帝国的年代”,“1914-1991”是“极端的年代”。正如梁展批评《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严重缺乏国际视野”一样,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学”不仅严重缺乏国际视野,而且严重缺乏一种“历史地层观”,不能处理当今每个民族-国家都是此前全部历史阶段的“交叠”,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篇所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例如“帝国主义”并未随殖民体系的瓦解而终结,而是越来越以维多利亚时期与“坏的帝国主义”(军事征服、经济掠夺)形影相随的“好的帝国主义”(所谓“自由帝国主义”,以“人权”和“扩大文明”为帝国的殖民史提供一种“新的道德基础”)的一面,在“民族-国家的世纪”大行其道。对此,梁展指出:“自由帝国主义终究是一项殖民治理技术,其理想的政治效果是通过殖民地与宗主国在共同的民主和自由原则上加强思想和文化上的联系,最终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
就英帝国而言,这种“自由帝国主义”形成于保守主义者艾德蒙·伯克1775年3月在英国议会的发言《与美洲殖民地和解》。自1760年代以来,英国议会对美洲殖民地反复课税,而美洲殖民地的英国殖民者们则坚持英国的“无代表,不课税”原则,起而反抗,独立情绪日益高涨(到1775年4月正式爆发独立革命)。与主张武力镇压的同僚不同,对美洲事务更熟悉也有亲身体验的伯克持一种政治现实主义,认为英国劳师远征,对付大西洋彼岸的一个比英国自身面积辽阔得多的大陆的几百万反叛者(同样是英国人),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违背英国自身的“反叛”精神(1641年新教革命)及其建立的“自由”原则。如果英国自己破坏这一原则,将不仅使英国在美洲以及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殖民地的统治失去“道德基础”,还会波及英国自身。出于军事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计算,他主张与美洲殖民地和解,承认其独立,这样才能在这个新兴国家保留英国的制度,将其纳入英帝国的制度体系之内,形成一种联盟而非敌人的关系。
伯克预见了维多利亚时期开始出现的“帝国的负担”,他考虑的是一旦英国的殖民体系瓦解,如何在英国的前殖民地继续维持其文化殖民,以实现武力殖民难以实现的目标。对此,1900年的美国评论者威廉·克莱恩心知肚明,在指导学生分析伯克的这个演说时说:
“伯克的政治生涯和政治原则以及后来的一切政治行为,其核心可概括为:他是人类自由的一个虔诚的信仰者,但他所谓的人类自由必须建立在英国宪法的原则的基础之上。他是改革的敌人。他孜孜以求人类的自由和幸福,但他同样激烈抵制英国制度的任何激进改变。他坚持认为,要带来自由和幸福,所需要的不是改变政府的形式,而是在既存制度的原则之下实现政府管理的公正和公平。人们常说,当伯克强烈反对法国大革命时,他的政治原则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变化。这是误解,他只是在维护自己的既定原则,即一种制度的良好的公正的管理。与其说他反对法国人追求自由,还不如说反对法国人鲁莽地推翻一切既存的宗教和君主制度。”
关键在于“英国制度”。换言之,伯克反对的是法国人没有按照英国方式进行社会实践,同时也顺带批判了英国内部那些“法国化”的改革者们。不过,美国独立最终不是以和解而是战争的方式实现的,“伯克方案”更多地见于美国建国之后,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美国在文化上依然是英国的“外省”,直到1960年代才最终完成自己的文化去殖化,开始高扬“美国文化”,并以此作为冷战的用具,在世界各地推行“美国化”。“伯克方案”也以麦考利的“东方教育计划”方式渗透于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租界”和势力范围,而这些本身就有着广泛地区联系的地方,交替受到过多个西方宗主国(也包括日本)的殖民影响。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条块分割,更典型地见于“半殖民”的中国,正如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中所说:
“在整个晚清和民国时代,英、美、日、法、德及其他数个欧洲国家都曾在华展开经济利益的争夺。它们沿着海岸和河岸‘切分’中国领土,将之纳入治外法权的范围,在那里依靠那些受到武力保护的资本家们的投机活动来聚敛财富,然后将其运回欧美的中心大都市。由这些经济活动提供的通往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直接通道,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十分重要。正如中国是一个可供经济剥削的巨大资源地,中国也向西方提供着充满活力的文化灵感,而这一灵感反过来又服务于帝国主义扩张。”
与印度等完全殖民地不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多个殖民帝国的并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帝国可以单独控住中国,也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帝国的语言和文化能够单独控住中国。这种多元并存的格局,使各个殖民帝国之间在中国必然存在着一种时而竞争时而合作的关系,同时也使任何一个殖民帝国不必像它们在各自的完全殖民地那样,为中国承担任何的道义、政治、社会和经济责任——除非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例如在1900年之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殖民帝国使用中国多赔付的庚款部分,在中国展开了一场争夺中国教育主权以培养各自的代理人的办学运动,其中又以日本和美国最为突出。多个殖民帝国及其语言和文化的存在,尤其是其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关系,产生了众多的“缝隙”。史书美说:
“我选用‘半殖民主义’一词来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的条件,以凸显中国的殖民结构的多元的、分层化的、强化却又不完全和碎片化的特征。‘半’在这里并非某物之‘一半’的意思,而是指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破碎化、非正式、间接的和多元分层的特征……这种半殖民主义的定义有着多重含义:第一,作为外国势力与中国的一种不对等关系,半殖民主义意味着列强不曾获得对中国的‘完全的支配权和正式的统治权’,列强对中国的支配主要经由一些不太正式但破坏性和改变性却不因此减弱的渠道得以实施;第二,对中国的不完全控制意味着,无论在经济渗透方面,还是在种族偏见层面,抑或是在地区司法制度层面,半殖民主义都更接近于新殖民主义,而非正式的制度化了的殖民主义;第三,外国势力的碎片化和多元化意味着,每一种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文化想象中分别占据着不同位置,例如许多中国人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欧美帝国主义之间作着区分;第四,对本书主体更为重要的是,当并存的多元殖民势力对中国的控制和剥削呈现出条块分割的状态时,它们也就使得自己对各区域内的本地居民活动的殖民管理和控制不可能是密切配合的和统一部署的,这就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立场上的态度远比正式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更加多元化的局面。”
不过,“半殖民”中国的这种共时性或空间上的“条块分割”,使史书美未能看见那些“完全殖民地”的时间上的“条块分割”,也即“历史地层”,例如菲律宾依次受到西班牙、美国和日本的殖民,印度尼西亚依次受到荷兰、英国然后又是荷兰、最后是日本的殖民,每一个殖民帝国都试图将自己的语言、景观、制度、文化和风俗在殖民地进行复制,过往的殖民者也在它们的前殖民地的土地上和人民内心留下了它们各自的可见的印记和不可见的印记,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兴起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呈现出远比欧洲当初的“民族-国家”建构更为复杂的面向,导致独立建国之后频繁发生的内乱。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的全球化: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不过,西方殖民的全球化,在其东方殖民地带来了“阶级关系”的一种改变,即产生了一个受过西方殖民教育的本土中产阶级阶层,而从这个本土阶级中将产生民族独立的领导人。由此可见,东方民族主义的产生不仅因为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带来的一种屈辱,还与西方帝国主义自身包含的民族主义息息相关。当建国后这同一个阶层的历史学家开始撰写国家史时,也同样受到前殖民宗主国的历史编纂学及其断代方式的影响,倾向于以“民族主义的方法论”来书写本国历史,而事实上,从“现代”开始,就已经不存在脱离于东西方关系的“本国史”。这样的“本国史”因切断了众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关联,失去了全球史的视野,也就失去了对西方殖民史的批判的广度和深度,失去了批判的复杂性。
就晚近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的兴起,梁展评论道:“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家们大多将‘帝国’和‘帝国主义’用作贬义。然而,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家分别被赋予了非常不同的含义。”考虑到英国“现代史”书写标志着“民族-国家史”与“帝国史”的开始分离,那么,这一评论也同样适合于“英国史”,正如A.G.霍普金斯在1999年的论文《重返未来:从国家史到帝国史》中所说:“现代英国史研究的最为惊人的特征之一,是把英国史与英帝国史分离开来。”安德鲁·麦柯克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纯粹是英国的国事么? ——十九世纪英国的历史编纂学中的帝国的边界》中也谈到,“在过去三十年左右,就英国史与英帝国史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历史编纂学的问题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代‘新帝国史学家’挑战据认为已过时的民族主义方法论,寻求扩大帝国史的边界,承认宗主国及其边缘[殖民地]之间的相互联系和重叠的历史”,发掘“帝国内部和帝国之间的历史的‘纠缠’,从而说明帝国内部与帝国之间的互动的复杂的多层性”。
如果说“英国史”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开始出现,是英帝国在日益扩大从而将越来越多的异质性空间纳入帝国版图之际建立一种以“英格兰”为核心的认同,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史”写作,则如安德鲁·麦柯克所说,“意味着,如果帝国的计划遭遇了失败,民族-国家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其焦点的自由——为英国在英帝国分崩离析之后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途径”。
当然,还存在着一种对已失去的英帝国的追魂之作,例如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而且,正如《英语国家史》试图在英帝国已然分崩离析之际,以“说英语的民族的共同历史”来为英帝国招魂一样,查尔斯·奥格顿和I.A.瑞恰兹在1920到1930年代发明“Basic English”(所谓“基本英语”,但“Basic”一词实为“Brit-ish-Amercian-scientific-interna-tional-commercial”的首字母缩写,意为“英国的、美国的、科学的、国际的、商业的”英语),试图以“Basic English”来为当时已摇摇欲坠的英帝国提供一种更为便捷的语言纽带。顺便提一句,瑞恰兹1929年来中国,本意是为了推广“Basic English”,以取代中国不同产生的“偏离标准英语”的“洋泾浜英语”,按罗德尼·柯奈克的说法,瑞恰兹试图以“Basic Eng⁃lish”来建构“心灵的帝国”。
“美国之音”(VOA)就采用了“基本英语”。不过,为建立“美国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美国还必须对此前“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重新空间化。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创立“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这一学科,其核心目标之一是削弱或割断欧洲宗主国与其前殖民地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纽带,按照地理空间的接近原则而不是前殖民地与其欧洲宗主国之间的政治-语言-文化的联属关系,将欧洲前殖民地分别置于一个个“单元”(unit),研究这些单元或“区域”内各个社会的内部动态关系,而这些被重新划定的“单元”因为当初欧洲殖民帝国的条块分割,往往不具备统一的语言、统一的制度和共同的文化记忆,容易滋生内部矛盾,从而为美国的介入(设立各类机构、设立军事基地等等)或“接管”提供了方便,同时,削弱欧洲宗主国与其前殖民地的纽带,也削弱了欧洲,增强了欧洲对美国的依附性。例如就“东南亚”这个新出现的“区域”概念,拉维·帕拉特在《碎片化的景观》一文中评论道:
“一些例子可以说明,地缘政治学对全球的随意划分,是经由区域研究的进展而被制度化的,例如‘东南亚’这个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蒙巴顿勋爵1943年在那里指挥盟军,把那里命名为‘东南亚’,才流行起来,而在此之前,即便人们图方便而把这一介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带称为‘东南亚’,也难以让人相信生活在这片从缅甸一直到菲律宾群岛、从印度尼西亚一直到中国的区域的多个彼此宗教不同、语言相异、被多个殖民宗主国分别管理的民族是生活在同一个相互联系的地理文化区域。”
作为“区域研究”的主要方面,是为这些新兴独立国家大量撰写“国别史”,尽管这种“国别史”写作出自美国重新划分世界空间的帝国主义动机,却与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国家史”写作形成一种合力。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何“民族-国家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其代价则是“全球史”的遮蔽。由于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帝国开始,帝国内部就包含了“民族-国家史”写作传统,梁展以下的评论就更加显示出历史辩证法的色彩:“帝国非但没有构成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反而成了民族主义的摇篮。”
帝国一方面要处理“帝国中心”的“内部殖民”(诸如英格兰之于苏格兰),一方面要处理“帝国边缘”的外部殖民,无论其“民族-国家史”,还是“帝国史”,都必须建立起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就此而言,“民族-国家史”只是“帝国史”的一个地方版,而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也可以相互转化(如独立后的一些欧洲前殖民地国家对“地区霸权”的追求),因此,如今所需要的不只是麦柯克所说的“扩大帝国史的边界”,而是将“民族-国家史”和“帝国史”纳入“全球史”。
《帝国的想象: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一书只在《导言》里唯一一次提到“全球史”,但该书以五个个案研究构成全书五章,将“帝国与民族-国家的纠缠”的万千关系的复杂性在“全球史网络中”逐层逐次展开,同时,判断与细节的交织也将理论思辨与考古般的经验研究融为一体,每个案例分析都堪称“全球史写作”的一次示范性实践。
(《帝国的想象: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梁展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8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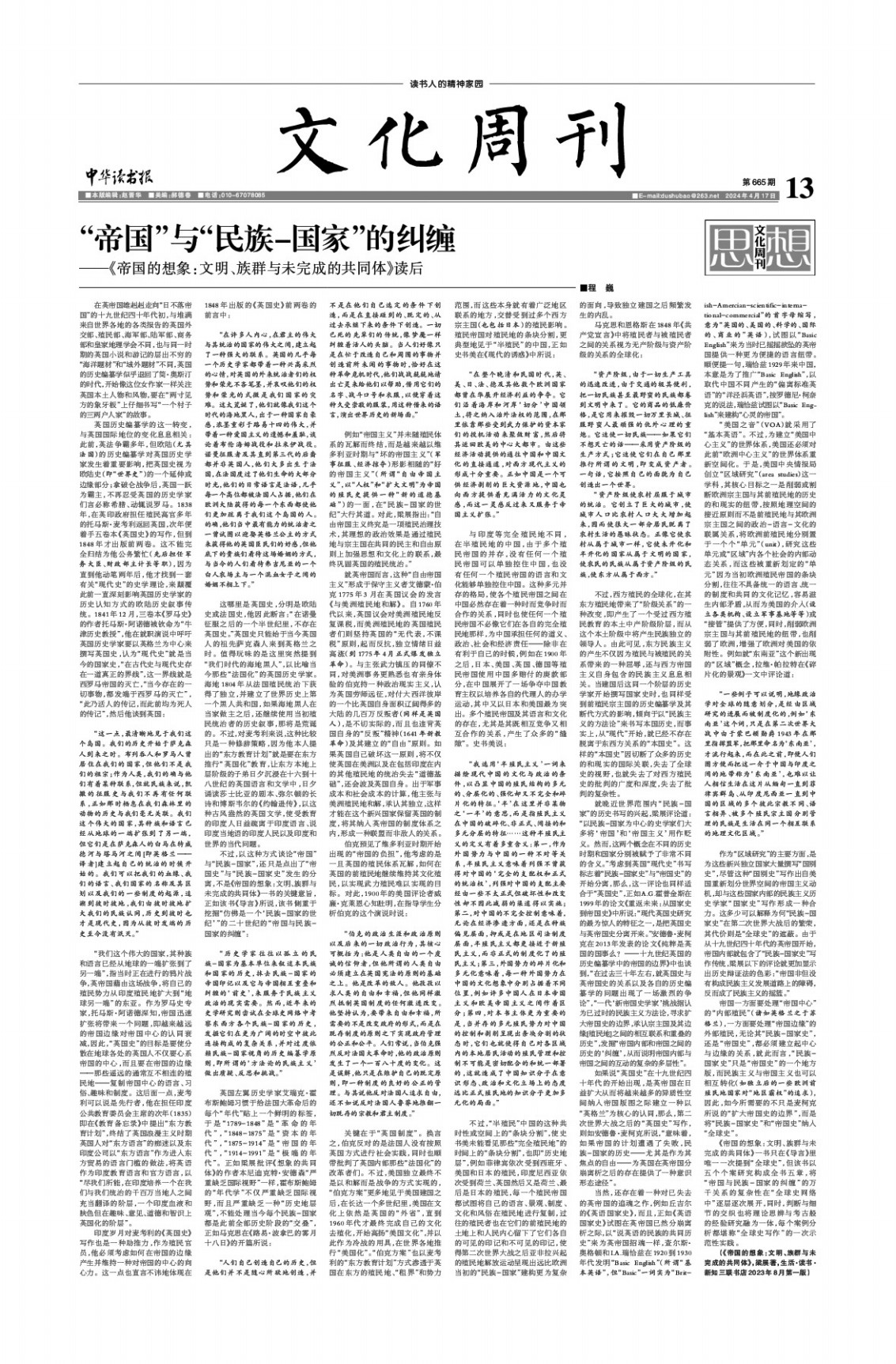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