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汇编了作者近四十年来所撰关于吐鲁番学研究的论文与评介文章,共36篇。全书以“历史与地理”“文书与碑刻”“群书与佛典”“调查与报告”“综述与书评”五个门类加以统摄,“以便读者了解我在吐鲁番学方面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关涉的领域”(《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序,第1页)。纵览全书,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古吐鲁番地区的历史变迁、中古典籍与佛典在吐鲁番的流传、中古吐鲁番文书与碑刻的个案研究、吐鲁番文献的流散与调查,以及国内外吐鲁番学研究论著评介。这些论文虽为荣氏之旧作,且发表时间跨度较大,发表刊物各异,但均聚焦于吐鲁番学整理与研究的诸多关键议题。本书无疑是荣氏在吐鲁番学领域所获成果与成就的阶段性学术回顾与总结。同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与探索吐鲁番学发展历程以及展望未来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敦煌吐鲁番学,历经百余年沉淀与发展,已逐步确立其国际性显学的地位。然而,相较于敦煌学,吐鲁番学之声势略显不足。吐鲁番文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亚及中国新疆等地“挖宝”时才得以现世的“宝藏”,历经流转,部分早期所获残卷或被多次转手,或被束之高阁,且文书涉及时代的跨度自十六国高昌郡至蒙元。故而,吐鲁番文献的碎片化问题相当严重,其流散、查阅、释读、整理与研究等工作之推进远较敦煌文献更为艰难。在此情况下,吐鲁番学数十年来的学术史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一书,便是这个学术史历程的具体展现。
一、整理与研究的草创期
吐鲁番学需整理与研究并行,研究应在大量整理成果的基础之上展开。在序言中,荣氏坦言:“我在敦煌方面历史研究多于文献整理,在吐鲁番方面整理工作多于历史研究,这和我最初的想法是有很大出入的。”(序,第3页)。之所以如此,根据作者自己所划分的四轮经历来看,这既受作者个人学术生涯中自身努力及种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也与吐鲁番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吐鲁番文献零散且持续出土的现状密切相关。
早期吐鲁番文献的出土,多与各国探险队的寻宝活动相关,往往缺乏科学严谨的考古报告,文献出土地与现收藏地分布广泛且零散,学者们大多只能依赖于探险队游记或日记,以略窥部分文献的大致面貌。20世纪80年代之前,欧洲与日本学者率先对吐鲁番文献展开整理与研究。1953年出版的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对斯坦因所获英藏吐鲁番文献进行了较系统整理,1975、1985年施密特(G.Schmitt)、梯娄(T.Thi⁃lo)主编的《汉文佛教文献残卷目录》第1、2卷则对德藏吐鲁番文献进行著录,1978年的藤枝晃编《高昌残影——出口常顺藏吐鲁番出土佛典断片图录》刊出日本人出口常顺早年在柏林所购吐鲁番文献。然而,这些海外成果在当时很难被国内学者获取,日本学者则借出国之便,对这批著录成果纷纷加以吸收。如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和大渊忍尔编《敦煌道经目录编》等。尽管该阶段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文献整体面貌披露不全等问题,往往只能作为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附庸,或仅就个别重要残片加以介绍与研究。这一阶段相当于吐鲁番学发展的草创期,而更为关键的是,此时明显缺乏中国学者的参与。
1980年代以后,国内吐鲁番学研究正式起步,其标志性事件为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出版。在时间上,该书的出版时间也与荣氏投入吐鲁番研究的首轮时间段大致相符。唐长孺先生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平装本自1981年开始陆续问世。这批文书是中国考古队于1959-1975年在吐鲁番地区考古发掘所获出土文书的整理结晶,对吐鲁番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然而,诚如荣氏在本书序言中所云,《吐鲁番出土文书》平装本直至1991年全部10册方告出版完成,且10册平装本实为录文初稿本,1992-1996年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4册图录本才是最终定本。此外,限于时代条件,书中为黑白图版且清晰度稍显不足,录文也有改进空间。
荣氏于1984-1985年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跟随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进修,期间深感资料之不全,而未能完成新出吐鲁番文献的介绍。尽管如此,书中《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一文,实为其1985年2月7日于莱顿完成之作,介绍了此前辽宁省档案馆新披露的六件唐代蒲昌府文书。这些文书虽早在1981、1982年就已公布,但“或许是由于用了较后起的名词‘档案’来称唐代的‘文书’,亦或是因为图版不清,录文残缺不全的缘故”(第267页),并未引起吐鲁番学界的注意,荣氏遂重新对其进行细致过录并解读了其中历史细节。这说明荣氏当年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之外,也对其他新出吐鲁番文书下过功夫。可见,早期吐鲁番学研究实则要滞后于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工作。这既缘于学术信息的交流不畅,也因文献披露与整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图版、录文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这或许是荣氏虽对吐鲁番文献投入了大量精力,但成果仅有《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与《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两文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调研与著录的发展期
对于世界范围内吐鲁番文献的调研与编目,成为推动吐鲁番学研究的又一重要途径。继唐长孺先生后,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陈国灿与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杨文和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十一卷等整理成果相继问世。或许受施密特或藤枝晃等海外学者的影响,荣氏第二轮吐鲁番学的研究目光与工作重心,转向海内外吐鲁番文献的深入调研与编目,旨在推动学界更加充分地认识与了解以往被深藏高阁的吐鲁番文书。
自1984年荣氏赴荷兰深造伊始,其对于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追索始终未曾停歇。在此期间,作者充分利用出国讲学等机会,对海外吐鲁番文献的收藏状况进行了详尽调研,特别聚焦于汉文非佛教文献领域。本书“调查与报告”部分,集结了作者数十年来对海内外所藏吐鲁番文献的调研报告,实现了对国内外绝大多数吐鲁番收集品的调研、叙录与编目。这些调研报告均是在作者的实地考察与亲眼所见的基础之上所编写,涵盖了散藏于欧美、日本和中国各地的大小宗吐鲁番文献,引领一时研究潮流。
其中,德藏吐鲁番文献的相关调研成果尤为重要。在作者之前,国内仅王重民、向达二位先生曾以收集古籍类资料为目的,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赴德国柏林调查过这批残卷。尽管他们对这批文献进行过比对并拍摄了一些重要文献的照片,这些旧照片不仅保留了原件的原始面貌,还保存了现今已不知去向的文献影像。但吐鲁番文献并非他们关注重点,因此相关照片长期在图书馆库房中尘封,鲜有人关注。作者《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德国吐鲁番文献旧照片的学术价值》一文,独具慧眼地重新发现了二位先生相关工作的重要价值,第二次“发掘”了这批吐鲁番文献。
德藏吐鲁番文献为现存吐鲁番文献最大宗之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经济问题和二战本身的破坏,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许多文献和文物被转卖、盗窃和炸毁,不少珍贵文献和文物现已不知所在”(第409页)。王重民和向达两位先生的旧照片均摄于二战前,其本身业已成为了珍贵的文物。作者不仅详尽地叙述了王重民、向达两位先生的考察过程以及这些旧照片的递藏经历,还对旧照片进行了系统编目与解读,使学术界能够全面认识这批珍贵文物的学术价值。如一组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的旧照片就展示了其早期写本形态,而该写卷原件现已不知去向,这些旧照片由此显得更为珍贵。书中《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与《再谈德藏吐鲁番出土汉文典籍与文书》则是作者对于德藏吐鲁番收集品的调研报告与编目,从而接续了王重民、向达二位先生的调查。
由此可见,吐鲁番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文献收藏地零散、数量难以准确统计,甚至部分藏品还难以获取。同时,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使得吐鲁番等地区的新文书仍源源不断出土,这加剧了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难度。“调查与报告”虽不如文献整理般全面,图版与录文也无法完全公开,但其对于后续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仍起到至关基础的索引作用。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吐鲁番文献因种种原因流散至世界各地,在整理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文献在哪、去哪和有什么样的问题,亦即文献的早期挖掘史与递藏史;其二,为了对吐鲁番历史做深入的剖析与解读,我们就必须立足于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吐鲁番文献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们将难以全面发掘文献的史料价值。
此外,《日本散藏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一文虽发表时间较晚,但其中许多荣氏调查所得,早已在2005年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的编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欧美所藏吐鲁番文献新知见》的调研与编目成果则基本汇入2007年荣氏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2021年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更是汇集了本轮工作所有调研与文献整理的精华,可供读者做进一步的延展阅读与研究。
荣氏该轮的研究成果,基本收录于本书“群书与佛典”部分。该部分深入探讨了吐鲁番地区《史记》与《汉书》的传抄状况,以及五代洛阳民间印刷业的发展,并对《唐律》《唐礼》及《春秋后语》进行了精细考释。这些内容基本以札记或叙录的形式呈现,是调研与编目工作的深化与拓展。尽管作者在序言中提及,该轮的研究成果因材料限制而显得琐碎,但同时期完成的《唐代西州的道教》一文,则展现了其系统且成熟的研究与思考。
在笔者看来,荣氏第二轮的相关工作对于吐鲁番学第二阶段的推进具有举足轻重的承上启下作用,彰显了其卓越的学术眼光与出色的学术交流能力。书中所收录的这些研究成果,在吐鲁番学学术史中必当占据一席之地。尤其是第四部分“调查与报告”,对于初涉吐鲁番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大宗吐鲁番文献的全面整理期
随着调研工作的持续深入,旧藏大宗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得以稳步推进。自2000年以后,吐鲁番文献的学术价值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大宗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工作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荣氏在书序言称:“到了2004年我接受吐鲁番文物局的邀请,从事‘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也就开启了我的第三轮吐鲁番学研究。”(序·第2页)吐鲁番文献集中出土的时间,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外国探险队发掘为主;其二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以阿斯塔那古墓群、哈拉和卓古墓群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抢救性发掘为主;其三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以新发现的墓葬区为主,如洋海墓地、木纳尔墓地、巴达木墓地以及交河故城附近。2007年出版的《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标志着第二阶段所获文书基本整理完毕。荣氏所言“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特指第三阶段所获文书,“新获”之名旨在与《吐鲁番出土文书》相区别。经过四年的辛勤努力,由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于2008年最终付梓出版。书中《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增订本)》一文,即荣氏对该项整理工作的全面概述。这部成果遵循了唐长孺先生早年确立的完善且系统的整理体例与范式,其出版标志着第三阶段集中出土的吐鲁番文献开始进入全面整理的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
吐鲁番文献的系统性整理,为推动吐鲁番学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材料基础。荣氏在《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中用心颇多,基于这批珍贵材料撰写了多篇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论文,如本书所收《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以及《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籍〉研究》《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的渊源》。后两篇论文均围绕《前秦建元二十年籍》展开。
中国古代籍帐制度极为发达,涉及国家制度、地方社会与婚姻经济等诸方面。《前秦建元二十年籍》这份珍贵的前秦官方户籍文书,于2006年在洋海一号台地4号墓赵货墓中被发掘并拆解出来。在此前,我们对于户籍的了解最早只能追溯至英藏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籍》。通过对《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的整理与讨论,荣氏不仅为我们了解古代纸本户籍的实际面貌提供了更早的实物资料,也为我们深入探究汉唐籍帐制度奠定了史料基础。
荣氏关于新获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贡献卓越,大概因其他分类安排,还有两篇重要论文未被收录,但仍需在此提及一二。一是《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发表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为书中《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一文的延续。该文探讨了新获吐鲁番文书中阚氏高昌王国永康九年、十年(474-475年)的送使情况,揭示了以高昌为交通枢纽的阚氏高昌与柔然、西域、南朝间的复杂关系。二是作者序中曾提及的《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发表于2007年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哥逻禄属于漠北铁勒、突厥系统的部落,主要活动于隋末唐初的金山地区,该文主要针对由36个残片组成的关于处理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的案卷展开讨论。
四、整理与研究的收尾与再起步期
旧藏大宗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已然完备,这既代表吐鲁番学一个阶段的圆满落幕,也预示新一轮工作正式拉开序幕。荣氏将2015年参与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整理项目视为其第四轮工作的重点,该项目成果最终于2020年汇编为35册《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含3册《总目 索引》)正式出版。在笔者看来,《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整理出版是前三阶段出土的旧藏大宗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延续与结束。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为上世纪初日本大谷光瑞组织的中亚探险队所获收集品,与前述《大谷文书集成》同源。这批文书以残片为主,总数逾两万余件。长期以来虽为学界所知,但鲜有学者能亲眼目睹。旅顺博物馆与日本龙谷大学曾合作整理过极少部分。自2015年起,荣氏与旅博王振芬馆长、人大孟宪实教授领衔的整理小组,对这批材料进行了全面且彻底的整理,编排图版并撰写解题。该项目基本将以往出土的大宗吐鲁番文献进行了补全。荣氏第四轮整理工作是对旧藏大宗吐鲁番文献整理的最终收尾,也为吐鲁番学未来发展开启了新的学术预流。
至于研究方面,正如荣氏在序言中所称,“我主要的工作是把握好图录和目录编纂的每个环节,研究工作几乎全部交给年轻学者和研究生们去做了”(序·第3页)。在旅博文书的项目中,荣氏主要担任项目的宏观指导与把关的重要角色,以确保整理成果的高质量。同时,他继续沿用上一轮培养学术团队的成功经验,藉此机会训练更多年轻学者和研究生投入吐鲁番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中。因而荣氏此轮工作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仅《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佛典的学术价值》《“康家一切经”考》与《新见敦煌吐鲁番写本〈楞伽师资记〉》。
以上工作的完成,标志着吐鲁番学发展第三阶段基本收尾,并为其进入第四阶段的再起步期奠定了坚实基础。关于吐鲁番学的再起步期,笔者大致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旧有整理成果的再“翻新”与查漏补缺。如朱雷先生《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的出版,以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刘安志教授负责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整理项目。同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分类释录与研究”,亦是在荣氏等人《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基础上,就录文与研究方面再做推进。此外,早年小田义久主编的四册《大谷文书集成》存在诸多定名、释录等方面的问题,学界同样也应当重启对这批文书的再整理。
另一方面,对新近出土的考古材料进行整理与研究。如前所述,吐鲁番文献第三次集中出土的时间截止于20世纪初。然而,随着近二十年来吐鲁番等地的考古工作取得显著进展,由此所获第四次集中出土的吐鲁番材料(包括碑刻与文书)也亟待得到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墓葬碑刻方面,如202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对巴达木东墓群中11座唐代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北庭副都护程奂墓,是继1984年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后又一重要考古发现,补充了唐代中晚期中央政府对西域治理的史实,以及北庭副都护的相关记载。2023年考古队又在该墓群采集到一件木制“张校部买地劵”,尚属新疆首见。至于出土文书方面,自2010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等单位在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考古发掘所获新出土文书,虽已有零星图版与研究发表,但仍希望这批新材料可以尽快得到全面整理与研究。另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胡兴军先生主持整理的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新出土文书以及由中山大学刘文锁教授负责挖掘的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出土的800余件多语种文书,均属近年来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
余论:国际化的吐鲁番学
综上所述,吐鲁番学的发展,大致历经四个阶段:草创期的初步整理与研究、发展期的深入调研与著录、全面整理期的大宗吐鲁番文献,以及当前所处收尾与再起步期的整理与研究。《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中所收论文,汇总了荣氏在吐鲁番学领域数十年来四轮工作的成果,正是吐鲁番学四个发展阶段的具象缩影,串起了数十年来吐鲁番学发展的学术史。
本书还展示了荣氏致力于推动吐鲁番学走向国际舞台的努力。本书中,多篇论文或先以外文形式刊于海外学术圈,或后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学术界发表。如《高昌居民如何把织物当做货币(公元3-8世纪)》一文,就是与美国耶鲁大学汉学家芮乐伟·韩森合撰,英文稿初刊于国际知名期刊Journal ofthe RoyalAsiatic Society;前述《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的渊源》由西村阳子翻译成日文,与中文本一同收录于土肥义和编《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
本书第五部分“综述与书评”所收录的数篇国内外吐鲁番学整理与研究论著的评介,亦是荣氏国际化视野的体现。如荣氏对德国探险家勒柯克事迹的介绍,可以让我们对于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第二、三次的活动有更多了解;荣氏对百济义康整理的《柏林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佛教文献》第3卷和西胁常记整理的《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印本目录》所作评介,则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当前海外学者对于德藏吐鲁番文献的整理进度与成果。
学术交流不应受到语言的羁绊,推动吐鲁番学的国际化交流,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同时也是检验学者学术水平与成就优劣的重要指标。展望未来,吐鲁番学的发展必须积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也期待吐鲁番学能够真正与敦煌学在国内外学界比翼齐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暨敦煌学研究中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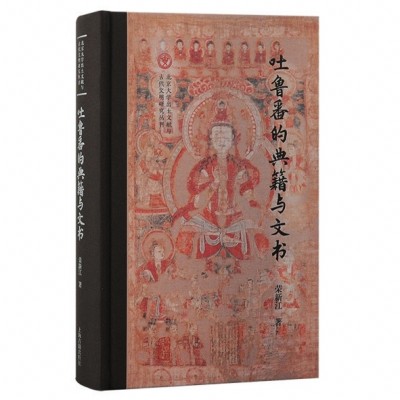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