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琮
在很多情况下,医学史总被描述为进步的历史,医疗旧世界通常被蒙上一层愚昧落后的滤镜。虽然19世纪末之前的美国行医者身份形形色色,但这种松散的传统行医生态,对病人而言,未必如我们想象中那样差。
美国医疗的演变,究竟为广大民众带来了是好是坏的影响,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过这种演变,带给专业医生的好处却是清晰可见的——他们从收入、地位缺乏保障的处境,一跃成为20世纪美国社会中一个强大、有声望且富有的群体。
正如《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所说,在美国所有的专业中,没有一个其他专业能够拥有医学专业这样独特的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威。本书由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斯塔尔所著,他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医疗改革计划资深顾问。整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两个长期运动:医学专业主权的崛起和医疗向产业的转变。
相较笔者之前评述的《癌症传》《止痛药丸》,是从具体的医学分支反映20世纪美式医疗产业化问题,本书则是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更长远的历史跨度,审视美式医学的变迁,以及医学群体为了自身利益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政治、公共政策、经济和民生等问题。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第一个运动可读性更强,斯塔尔描绘了殖民地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医疗生态的图景变化,以及专业医学是在怎样的动机和条件下,从多样化的传统医疗世界脱胎,独霸了美国医疗保健市场,其中不乏精彩的故事和作者独到的见解。
旧时医疗:行医并非康庄大道
尽管对健康的追求,伴随着整个人类发展史,然而并不意味着医生一直以来拥有如今在美国那么高的社会地位。古罗马的医生主要是奴隶、被释放的奴隶和外国人,行医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低级的职业。
在美国自身的历史中,19世纪末以前的医生与今天的医生相比,从地位上来说也完全是天壤之别。彼时的医生不管是影响力、声望还是收入,都要比今天低得多。按照斯塔尔的说法,17和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行医者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并且医生这种角色通常不会独立存在。
第一类是由神职人员兼任的医生,他们行使宗教职能,同时充当医疗服务者的角色。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本就比较高,兼职医生并不会带来太多的附加价值。
第二类是由各种大众行当担任的民间治疗师:售卖烟酒糖茶的食品商贩会开药卖药;假发制造师和咖啡侍女能胜任医生;时装裁缝不仅会接生,还会治愈皮癣、烫伤、痔疮等多种疾病;勤劳的农民、技工、渔民等也可以是具有传奇手艺的接骨师。
他们中有些是为亲朋好友解决疾痛的过程中,逐渐自学成才的天赋选手;有些是从小就接受技艺训练的“世家”后裔;有些是游历四方后,掌握医疗信息差的贩夫走卒。无论哪一种,都是没有受过所谓正规教育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会治病,以及依靠治病、卖药获得主业之外的收入,同时积累起口碑。这类从业者的劳动所得尚属人之常情的合理范围,他们并没有依靠行医,获得更尊贵的身份,也没有恃技凌人的特权。
第三类是与上述大众医学者相对的专业医学者。虽然是专业门类,但是由于行医收入并不稳定,很多人也要身兼数职。这类人群中,少数出身良好者,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前往欧洲留学,通常处于鄙视链的顶端。与在行业内的地位不同,他们选择医学专业,大多会被家人或同学认为“自暴自弃”了。
1851年,美国医学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受过教育的人才”普遍厌恶医学。获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中,分别有约26%的人选择做牧师或进入律政界,只有8%的人选择行医。他们不仅完全不需要依靠行医来逆天改命,还会因择医而为人不解。
专业医学者中的绝大多数则是处于鄙视链中间的人群,他们多多少少接受过“正规”医学培训。鄙视链底端则是那些自学成才者。
总的来说,早期美国医学从业者的身份高低,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行医,而是取决于他们既在的社会阶层;他们的财富多寡,并不主要依赖行医收入,而是仰仗继承或经商。行医在20世纪之前的美国,几乎不是一条阶级跃升和发家致富之路。但是,大量中层人士打破阶级、向上流动的渴望已经蠢蠢欲动。
中层医生:为身份和地位而战
斯塔尔的叙事指向一个关键问题:美国专业医学主权崛起的一股重要力量,正是中层人士对自我身份强烈的焦虑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们追逐自己的利益和理想,从而使得医学逐渐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医学专业的崛起,亦是最近历史上集体社会流动最好的例子。
许多医学正史中,会有意无意地回避“人及其处境、欲望”,对于医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斯塔尔算是比较克制地提出来了,有心的读者定能意会。
由于行医收入不稳,尤其在刚入行时,为了维持生活,大部分中层人士不得已要兼职一些活计,比如照料病人的牲畜、陪病人熬夜;但在心态上,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技术,自认比底层行医者更专业,应当获得欧洲医生那样的体面。
1750年左右,医学群体也试图专业化,但是这股浪潮上涨得不合时宜。受当时民主文化的影响,人们讨厌晦涩难懂的知识和专业医生的疗法,民间和草药疗法则大有市场,同时限于交通和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条件,家庭成员在照护病人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民众对专业医学诉求权威的强烈抵制,家庭医学、民间及草药医学作为专业医学的强劲对手,一直持续到19世纪晚期。这100多年,也充分展示了美国文化中的一个持久性冲突,即民主文化重常识和专业人士重知识之间的冲突。
斯塔尔提到了一本有趣的书:卡瑟尔的《医生本人》,这本“印象管理书”手把手地教医生自我包装,比如举止优雅和彬彬有礼甚于熟稔医学知识、适当拉开与病人的距离有助于保持尊严等。这本书自1881年出版以来多次再版,其受欢迎程度从侧面证明,19世纪晚期专业医生的地位焦虑。
中层医生的尴尬处境,使得他们有强于顶层和底层的冲动来改变现状。1840年代,美国医学会成立初期,吸引的并不是顶尖的精英医生,而是次于他们的从业者。学会成立的动力,其实就是年轻医生对生存状态的不满。他们计划通过发展医疗执照颁发制度,提高准入门槛,强化自我身份,并将他们瞧不上的人排除在外。从此,就有了“正统”和“不正统”医生之说。
按照斯塔尔的说法,医学演变的结果,对顶层人士提高不大,更多的是提高了中层人士的地位,并彻底消灭了底层。20世纪许多传统手工艺者逐渐失去垄断时,医生却正在建立垄断权;其他手工业者成为资本的牺牲品时,医生却成了小资本家。
专业医学:走向权威独霸江湖
斯塔尔指出,一个群体想要让自己的行业崛起,离不开权威的增长。建立权威,需要解决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内部共识,二是外部合法性。也就是团结一致,获取公众的依赖和政府的支持。
“医学专业主权的崛起”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至1930年代。这个时期,医疗行业大洗牌,中层医生在这场斗争中笑到了最后。对于专业医学而言,想要建立权威的外部阻力主要来自公众、其他医学(民间及草药医学)、专利药品。如前所述,这场“外战”在1750年代失败过一次了。
但19世纪末,外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斯塔尔指出,美国人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是医学变为一个权威专业广泛的外部力量。这种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导致人们对专业医学的依赖性增强。交通变革和城市兴起降低了求医的间接花费(通常还是主要成本),使多数人能负担起医疗保健,家庭医学逐渐瓦解。
医学权威的增长,还需要依靠合法性机制。获得制度化的前提是,医学内部要达成统一。这正是权威化运动最困难的一环,团体之间、个人之间纷争不断,通常都是公开而尖刻的。校史作者还曾写下“刀具、手枪、凿子、棍棒、大口径短枪等随处可见”,这都是医学院的真实斗争工具。
除了专业医学内部的斗争,19世纪中叶,与“正统派”对立的“宗派”逐渐庞大,到19世纪晚期,顺势疗法派和折衷派势头最猛,虽然“正统派”的医学院还占据80%的份额,但是他们的权威性遭到了极大挑战。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非正统派”与他们打成了平手。
双方开始走向让步和妥协,甚至“正统派”需要依靠“非正统派”提供转诊病人。由此,双方共同推动了医师执照制度。如今,一位医生在职业身份上内在的权威,已经在一个标准化教育和执照授予系统中制度化了。民间医家,哪怕再有能力,未经系统化训练获得资质,都会被专业医学排除在外,成为新的“非正统医生”。合法性机制确保了权威,也垄断了市场。
但是强制的垄断无法持久,制度保障的社会权威也会受制于时下的政策。医学专业令其他专业艳羡之处在于,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权威。
19世纪,美国医疗还有一个行业在分专业医学的羹,就是专利药品。当医学内部开始团结之后,他们一致对外的目标就格外显眼了。医学专业打通媒体渠道,借助科学的旗号,以理性、公正的形象大力开展“打假运动”。
20世纪初,美国医学会印发了15万份《美国大骗局》,直指专利药品就是“欺诈产品”。这一“打假运动”还被制度化,迫使报刊放弃所有专利药品的广告,不管有效无效的药品,全部被乱棍打死。1920年代,专利药品节节败退,行会不仅将专利药品商收为小弟,还在公众心目中进一步巩固了权威。
科学帮助医学建立了正当复杂性,加强了医学专业的排他性,常识为知识让道,疾病和健康以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占领了日常生活。技术发展让医生日益依赖设备来诊断疾病,病人的口述逐渐变得不再必要——设备在拉近医生彼此的同时,推开了医患双方的距离。
在依赖性和合法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医学权威获得了空前成功。医学权威的回报体现在获得社会和经济特权上。“在美国,没有一个群体能像医学专业这样,在这个理性和权力的新世界占据如此主导性的地位。”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试图极力阻止任何由外部力量控制的医疗计划,包括抵制合理化医疗改革、拒绝全民医疗保健政策;打假和监督其他行业后,他们控制药品的使用和销售,使其他形式的医疗边缘化,却不愿接受外部组织的监督。他们耗费着极高的成本,却没能带来更好的健康服务。
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的确大获成功,但是却丧失了公众的信任——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5个不同商业部门中,医疗保健业和制药业获得了人们的最低评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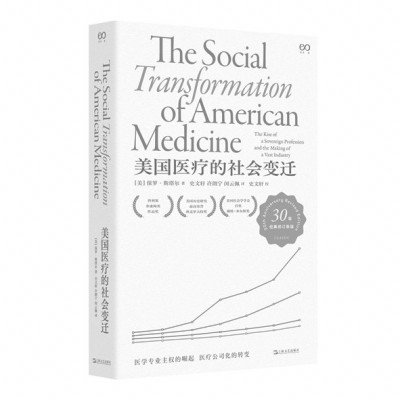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