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明词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被认为是宋词与清词之间的低谷,作为非经典化文类,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一般读者心中,地位都不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元词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整体性关照有黄兆汉《金元词史》(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赵维江《金元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陶然《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版)、丁放《金元词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接受史研究有刘静、刘磊《金元词研究史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个案研究有赵永源《遗山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等,左洪涛(《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重点关注了金元全真教词人群体。陈海霞博士的《元词史》(以下简称陈著)以崭新的论述方式让我们重新审视元代词人的创作风貌,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空结合的论述视角
陈著最为显著的特色是地域性与时间性相结合的论述方式。该书将元词按照南北方加以论述,北方又分为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南方则以浙江、江西、江苏为主。每一部分都用图表统计的方式列出该地区词人创作的基本情况,为之后的论述打下坚实的基础。陈著的这种安排与元词作者的地理分布是吻合的,根据笔者对《全金元词》的统计,元代词人分布较多的地区为浙江、江西、河北、江苏、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对于某些不适合归入地域论述的词人,陈著用词人群体的方式加以补充,比如释道词人、蒙古色目词人和域外词人。不同于之前的各类词史著作,陈著这种侧重地域与群体的论述方式,是立足于元代文学发展的情况,明显受到其老师杨镰先生《元诗史》的影响。
陈著虽然在体例上是以地域为视角论述元词,但并未忽略时间维度。比如在第二章山西籍词人首先论述了元好问与元初北方词坛,突出了元词与金词联系。在第四章浙江籍词人关注了宋元易代之际的词人,将元词与南宋词加以联系。在全书结尾“元词的余响”涉及到由元入明的高启、魏观、杨基、贝琼等词人,他们连接了元明两代词坛。这些论述突出了元词的起点,带有浓郁的史的意识。
在具体论述中,陈著将元代词人的学习对象与风格特征追述到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等宋代词人,同样体现了词的传承与发展。对某个词人而言,同样存在发展变化的过程,比如元好问,“经历了金元易代之际的伤痛,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使其词的情感基调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这是突出朝代更迭对于词人创作的影响。张翥贯通南北的经历使他成为沟通南北词坛的人物,他在游历过程中创作的词作,包含了南方和北方的意象,他既学习南方的王沂孙、仇远等人,也受到元好问、白朴的影响。
二、对元代文学特点的探究
陈著不仅是独具特色的一部断代词史,还是元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近二十年来元代诗文词的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出现了众多论著,陈著无疑代表了目前元词研究的水平。该书在同题集咏、纪行词、南北词风融合等方面体现了元代文学的特点,北方民族词人成为元词的亮点。
同题集咏是元代诗词创作的一大特色,杨镰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刘嘉伟、李文胜等人有具体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诗。陈著从词的角度加以审视,发掘出以往被忽视的一面。比如咏物词集《乐府补题》收录了宋末元初张炎、周密、仇远、王沂孙等14人的37首词作,通过对龙涎香、白莲、莼、蟹、蝉的歌咏,“题旨隐晦而哀感无端”,“充满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寄慨遥深,婉转多讽”。南宋灭亡后,昭仪王清惠北上,在汴梁夷山驿站作《满江红·太液芙蓉》,抒发家国之痛,这首词传遍各地,文天祥、邓光荐、汪元量等人皆作词相和。陆行直写作《清平乐·题碧梧苍石图》,表达自己物是人非之感,得到了很多文人的效仿题写,包括陆留、王铉、郝贞等14人。这次同题集咏体现了文人的共通的情怀:对深厚友谊的认可和“时间流逝中的恍如隔世感”,也是元代文学与绘画相结合的典型例证。
元代疆域广阔,文人流动频繁,纪行文学非常兴盛,以往学者关注的多为纪行诗,陈著探讨了元代的纪行词,其中最能体现元代特色的是大都(今北京)纪行词与上京(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纪行词。元初,第一批北上的南宋文人有宫廷琴师汪元量,他在大都写的《望江南·幽州九日》,“将一个南方人初到大都时的悲伤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忆秦娥》描绘了蒙古草原风光,在思乡的背后隐藏着亡国的苦痛。张炎北上大都同样在词中写下了他的见闻与感受。
此外,涉及到纪行的词作还有胡祗遹送友人出使日本的《木兰花慢》和张之翰《沁园春》。《沁园春》题目为“至元戊子冬,国子司业李君两山以春宫小宗伯,奉命出使交趾,故作此以壮其行”,可见是送别友人李思衍出使安南。元代既有文人出使域外,也有域外词人来到元朝疆土,例如高丽人李齐贤在大都、上都与名公交游,他到四川、陕西等地游赏,用词记录见闻,抒发感想。这些词人词作反映了元朝与周边王朝的政治关系与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南北文学的交流融合是元代文学一大特色,在词的方面同样重要。这种交流融合既体现在词的创作方面,也有理论表述。南北词人通过游历、同题集咏、雅集等方式,沟通交流,比如北方人白朴、萨都剌的南游,在江南各地书写秀美的风光,抒发怀古之幽思。至元十七年(1280),柘城(今属河南)人陈思济游览道教圣地洞霄宮,作《木兰花慢》,李德基、赵若秀、刘元都有和作,其中李德基为平水(今山西临汾)人,赵若秀、刘元为南方人。雅集在元代非常盛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文人汇聚一堂,宴会赋诗、赏画听曲,成为元代特有的文化风景。昆山(今属江苏)人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就是元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文人雅集活动,其中就有词的创作,他的《水调歌头·天香词》得到多位文人的应和,其中陆仁祖籍河南,算得上南北文人的聚会。文学理论方面则有张之翰的论述,作为北方人,他“仕宦南方,希望南北双方能够取长补短”。
蒙古、色目作家大量涌现是元代文学的新现象,陈著辟出专门的章节分析蒙古色目词人,包括畏兀儿人廉惇、贯云石、偰玉立,唐兀人孟昉,雍古部(信仰基督教)马祖常,答失蛮(信仰伊斯兰教)萨都剌等人。作者不但分析了他们的代表性词作,还特别指出孟昉对词的看法,孟昉说:“凡文章之有韵者,皆可歌也。第时有升降,言有雅俗,调有古今,声有清浊。原其所自,无非发人心之和,非六德之外别有一律吕也。”说明孟昉对词的认识非常深刻,体现了其领会中原传统文化之深。这些蒙古色目词人充分体现了一种文化认同,是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细节方面体现新意
除了关注元词的地域性、词的传承发展、元词的特点,陈著在一些细节上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体现了该书的学术性,涉及到词论、元词的曲化、寿词、赠妓词、“词史”等问题。
陈著在重点论述元词创作的同时,也关注元代的词论,重点介绍了陆辅之《词旨》的渊源与主张,还涉及吴澄、赵文、孟昉等人的观点。元词的曲化现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词曲本身就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元代处于二者共存交融时期,区分词与曲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陈著认为,“以词入曲或者用写词的方法去写曲已经是词曲互动中的一种自然现象,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一种方式,张可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比较成功的实践”。由此引发了元词的通俗化,“大量曲语渗入词的创作当中,元词的通俗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文学潮流”。
陈著在对元人词作的分析中几乎涉及到词的各种题材,海霞博士对词作的分析非常细腻,比如吴澄歌咏梨花的词、韩奕节序词、薛昂夫节序词,这种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是得其导师刘扬忠先生的真传。其中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是寿词和赠妓词。
寿词体现了词的交际功能,元代的寿词有何特点呢? 陈著引用张炎《词源》,指出寿词创作的难处,在具体的论述中长于同中见异,指出魏初的寿词“善于融化字面,使语意新奇”,程钜夫的寿词具有“清雅之气”和“北人的豪气”,“将俗语、口语、常语入词”。另外还结合寿词的赠与对象进行分析,比如舒逊写给兄长的寿词、张翥写给自己的寿词、杨基写给妻子的寿词各不相同。
赠妓词的创作贯穿了元初到元末,反映了元代文人与歌妓群体的交往,表达了文人对其歌唱技艺的赞美和不幸命运的同情。这些赠给歌者、歌妓的词可以与夏庭芝的《青楼集》相互比勘,作为研究元代歌女群体的重要资料。陈著分析了王恽、胡祗遹、张弘范、卢挚、张埜、赵孟頫、张可久、吴景奎、刘埙、陆文圭、倪瓒、冯子振、张翥等十几位词人的赠妓词。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陈著提出“词史”的问题,她认为,汪元量的词、谢应芳的词具有“词史”的性质,刘将孙有“丧乱词”,“梁寅经历了元明易代之际的社会动荡,他的词留下了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记录”,类似的还有舒逊,这些问题实际上关涉到词与史的关系。学术界对“诗史”问题、诗与史的关系非常重视,出现了大量论著。词作为一种有别于诗的文体,与历史的关系如何,值得进一步探讨。
当然,作为一部涉及面非常广的断代词史,陈著也存在疏漏。比如将兀颜思忠、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列入蒙古色目词人,不够准确,女真族和契丹族在元代属于汉人,即原来金朝统治区域下的各族人。陈著在论述中常结合词的创作年代进行分析,做到知人论世,如果能做一个元词编年作为附录,读者对于元词的发展及其与元代政治的关系,就会更为鲜明。
作为一部开创式的元词史,陈著提出了很多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比如词的地域性、纪行词、赠妓词、词与史的关系等等,都具有启发性。希望作者以《元词史》为基础,推出更多研究成果,也希望元词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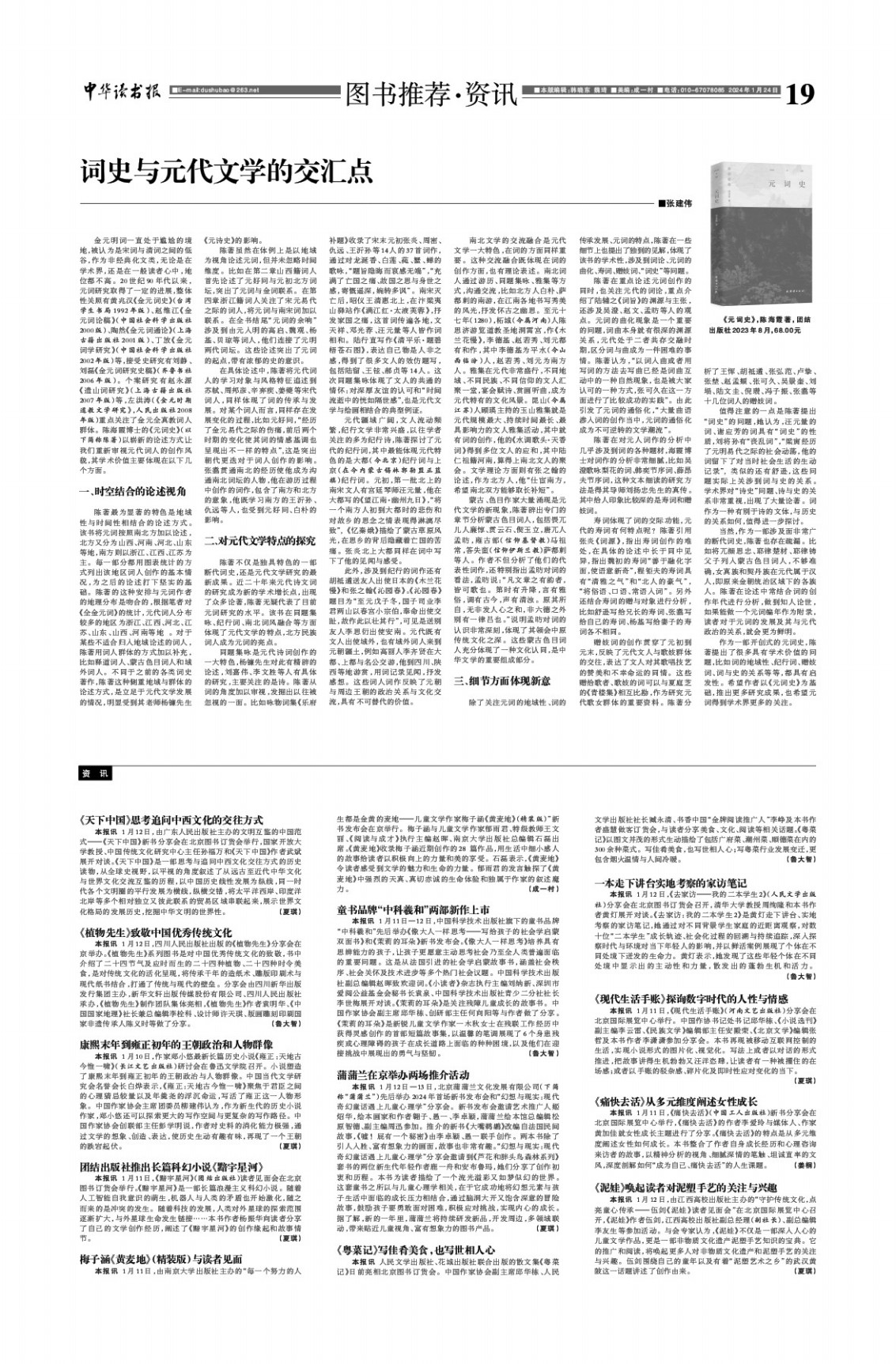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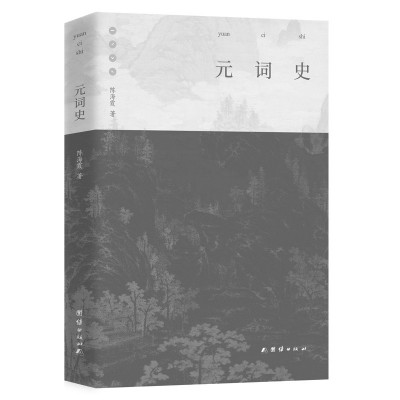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