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郑克晟先生的《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一书出版后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先师的这本书,视角非常独特——是站在他父亲郑天挺老先生的身旁,以仰视崇敬的目光看前辈,即我们师祖辈学人们。同时,又用平视欣赏的目光看待与他同辈的学人们。不过,对学人们的追忆,却并不是用撰写纪传式的正史笔法。虽然书中也涉及到对他们学术成就、道德文章的正面介绍,但更多的是聚焦在生活中,在非学术、非正式的场景中,他们的言行,基本上是轶事的片段、过程的瞬间、人像的剪影。先师以这样的角度,给读者呈现了一个个前辈大师、学人们侧身站立的真实样貌。
风骨
拜时代所赐,前辈学者大师中的大多数人,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往往赋予他们浓浓的家国情怀和坚韧的性格。而带有这样特质的他们,在逆境中,就会表现出不计生死、不慕富贵、任劳任怨的凛然风骨。
《从》一书中,给人印象很深的是两次大是大非之前,郑天挺先生的两次选择。1935年,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华北,北平局势日益紧张。当时兼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郑天挺先生,一方面艰难地操持着学校日常工作,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对同事交代:“如本人不能维持时,则交各主任;各主任不能维持时,则交之与校关系较深之老职员;俾校产不致损失。”而且,坚定地告诉同仁:“有一语可相告,即此身绝不从贼尔!”此时情况是,政府无能,民众时时都有死亡之虞,连诸如宋哲元、张自忠等手握重兵的将领都常常不得不委屈自己,与日寇虚与委蛇。而郑老先生本一介书生,首先考虑的不是自身安全,而是“俾校产不致损失”,坚定地表明立场,“绝不从贼”!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陷于敌手,郑老先生仍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奔走,安排师生转移,妥善保护校产。当时湖南《力报》在《沦陷后之平津》一文中称赞道:“北大之秘书郑天挺支柱艰危,如孤臣孽子,忍辱负重。”
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在即,郑天挺先生既积极参与傅作义等商议北平和平解放的有关活动,又殚精竭虑地在复杂的局面中为保全学校、维持正常秩序而废寝忘食地工作。师生们都看在眼里,学生自治会送给郑先生一面上书“北大舵手”四字的锦旗来表达敬意。同时,郑先生正面回应中共华北城工部通过各种渠道传来的意见,表示自己一生最注重“敦品”,不会离开北大,不会南下。最终把一个完整、秩序井然的北大交到新生的人民政权手中。
在《从》书的字里行间,能看到老一辈的学人们大多十分看重“自由之精神”,同他们并不十分认同的“官”和“官府”保持着距离。西南联大时期,北大的教授们对1945年蒋梦麟先生应宋子文之邀,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的态度,就颇为典型。身为北大校长,在世人眼中虽不位高权重,但地位清贵,人望很高。突然传出蒋氏去政府为官的消息,教授们一片哗然,非常不认同蒋的决定,认为他已经不再有资格留在教育界。其中,尤以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周炳琳先生反应最为激烈,他竭力反对蒋再兼任北大校长。同样激烈的还有傅斯年先生,在重庆为此事与蒋大吵了一架。虽然,两人后来互相谅解、和好如初,但此事折射出当时学人们推崇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群体意识。
在人生的逆境中,不怒不嗔,不怨不尤,初心不改,恪守本分,埋头做事,同样也是风骨凛然。《从》书中,用不长的篇幅,讲述了史学家商鸿逵先生的一段过往。1952年以后,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商鸿逵先生,被政治运动不断冲击,受了不少委屈。虽然身为教师,学校竟然几年都不给他排课。但商先生没有怨言,自己枯坐书斋,专心致志校订整理已故老师孟森先生的遗稿,历经数年辛苦,最终编成孟森先生遗著《心史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了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情分,尽了作为学者的本分。
学养
学养深厚,而且推崇朴学,是我们这些后辈对老一辈学人的景仰的重要原因。《从》书中有不少这样的事例。
上世纪五十年代,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成为史学界的热门课题。而徐一夔《始丰稿》中的《织工对》是此项研究十分重要的史料。郑天挺老先生通过抽丝剥茧般的研究,发现了几个大多数人都没注意到的问题:其一,因为《始丰稿》编排体例是按年分组排列,该书前三卷成书于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前,而《织工对》收录在第一卷。因此,此篇应是元末之作。其二,郑老先生对《织工对》“日佣为钱二百缗”句中的“缗”进行考证,认为“缗”是元末对一千钱的习惯说法,而明初对一千钱则习惯称为一贯。其三,郑老先生还通过比对元末明初钞币贬值的不同情况,说明“日佣为钱二百缗”的现象,应该是元末而不是明初。这一番考证下来,核心史料成书于何时的问题“水落石出”,所谓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究竟起于何时,就该有一个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了。老先生的学养在这里显示出“见微知著”“四两拨千斤”的力量。
先师在书中回忆自己早年北大求学时,用了不少篇幅写向达先生讲课的内容。向先生把自唐宋迄明清的民间结社现象,进行纵跨上千年的考察,并从统治阶级与百姓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对立矛盾的高度来解析。这样的眼光和方法,对于后来者极富启发价值。向老先生认为,唐宋时期,由于商业资本发展,民间出现了不少行会、帮会等经济互助组织,农村也有带自卫性质的各种社。这样的情况对统治阶级很不利,他们从“重农抑商”的传统出发,扶持理学的发展,意在重新建立道德标准,加强宗法观念,提倡“耕读传家久”,把老百姓束缚于土地之上。到明清时期,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知识分子结社更多,统治阶级就利用科场案、奏销案,甚至文字狱等手段打击民间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且,乾隆皇帝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编纂《四库全书》,其目的也是为了禁销民间大量存在的不利于统治阶级的书籍,从而钳制百姓的思想。
饱学的前辈先生们的学问、学养不仅仅在大部头的著述中展现,有时还表现在对并不那么起眼的问题上。《从》书中两个这样的例子,让人印象深刻。
1956年,北京中国书店收来一大批徽州文书,因为数量太大,历史所(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即征询白寿彝等先生的意见。“白先生说,可以连买带抄,抄的就不买了,多数有价值的要买,字数少的可以抄而留下来。”正是白先生几十年前的这一意见,让这批徽州文书成了历史所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并且让历史所成为重要的徽学研究中心。
先师在书中还提到了多年前的一件“小事”:1981年,先师为研究生们开设研究明代庄田的选修课之前,把讲课提纲给冯承柏先生看,征求他的意见。冯先生既有研究美国史的学术背景,后来又转向博物馆专业,知识面广,眼界宽阔。他看后建议:“应当加上明代庄田制与西方庄园制比较一题。”并讲述了西方庄园制的特点及自己的看法。正是这一就中西历史相近题目进行比较研究的建议,让先师感念多年。
交谊
一般人也许会认为,饱读诗书的大学者们在人际交往中都是不苟言笑,甚至古板的样子。其实不然,先师的书中就记载了不少完全不同于一般人刻板印象的事情。
他们也有古道热肠。1934年夏秋之际,著名语言文学大师刘半农先生在北平协和医院病逝。前去悼念、执绋送葬者,个个都是知名学者,几乎是当时北平学术界的“半壁江山”:如蒋梦麟、胡适、沈兼士、陶希圣、郑天挺、郑奠、白涤洲、魏建功、马隅卿、马裕藻、马衡、唐兰等,出殡队伍前导的旌铭题曰: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刘半农,名复)博士。下款: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愚弟蔡元培敬题。将刘半农先生棺柩送至地安门外嘉兴寺暂厝之后,众学者又齐聚一堂共同商议刘先生身后诸事,决定由北京大学、北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图书馆、国语统一委员会、故宫博物院、西北科学考察团等八团体呈请政府褒扬刘半农先生,抚恤其遗属,呈文由郑天挺先生起草,刘先生遗稿由魏建功先生负责整理。
他们也乐于助人。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先生发表了重要的论文《发羌之地望与对音》。文章引经据典,考证“发羌”即西藏土名“Bod”之对音。他根据唐代的有关史籍,以地理证发羌之地望,以古音证“发”字与“Bod”可相对,继而得出“发羌”即“Bod”的对音这一结论。而这一成果更因为得到众先生从不同角度的印证,而更具学术价值。陈寅恪先生为之订正梵文对音和佛经名称,罗常培先生则从音韵学的角度给予证明,卲循正先生根据伊斯兰语为其补充译文。虽然那时他们同处西南边鄙之地的蒙自,极度缺乏图书资料,但众先生以自己的学术专长助人为乐,也成就了一段学林佳话。
他们的谐趣幽默与众不同。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们生活清苦,一有好吃的就会邀请几个好友一起分享。罗庸先生家里做饼,邀请单身在滇的郑天挺先生和罗常培先生一起享用。去之前,郑先生见罗常培先生房间里有客人,就写了上有“於陵陟弓於略居乞必郢”十个字的便条投进罗的房间,罗先生看后很快回了十二个字:“五可背故怯句七梗的盖些夜。”一来一往二十二个字,谁都认识,但别人很难看懂其中意思。其实,他们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汉字读音反切的方法。郑先生写的是“膺中约吃饼”(罗庸先生字膺中),罗常培先生回的是“我不去,请代谢”。这是属于他们的幽默,既风趣又不失学者本色。
他们劝说别人的方式别具一格。1939年12月,时任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先生决意离职,并私下向郑天挺先生透露清华梅贻琦校长有意请郑先生接任此职。郑先生因为行政事务冗杂,影响教学和研究,坚辞不受。傅斯年、周炳琳、杨振声等先生也赞成郑先生的立场。但联大常委会认定郑先生是最佳人选,梅贻琦先生出面劝说,郑先生一再辞谢,并致函校常委会表示只想多读书、教好课。不料,校常委会仍然坚持原议,并派黄子坚、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等先生上门劝驾,大概是没见到郑先生本人,这几位留下了那张著名的字条,上书:“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仅仅八个字,分量却很重。既有对郑先生人品、能力、雅量等的肯定和推崇,又有把郑先生架到高处、逼到墙角的味道,使郑先生看在同事、朋友和学校的情分上,不忍再行拒绝,颇有实施“胁迫”和“绑架”之嫌。
他们对师友既真挚关切又善解人意。王永兴先生曾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当时所长为傅斯年先生,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因此,王先生对郑先生一直执弟子礼,恭敬有加。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天津,时在山西工作的王永兴先生十分着急,分别给郑天挺、王玉哲、杨志玖等诸位先生写信问候,但却没留下回信的地址。这是王先生细心和善解人意之处:一则地震给各位先生生活带来不少艰难,未必有时间和精力回信;二则正处在“文革”期间,大家处境都不方便,以此可以避免给各位先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久,王先生又派子女到南开大学来看望诸位先生,由此可见王永兴先生对师友们的一片真情。
剪影
如果想了解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和学术史,那么,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傅斯年等几位先生肯定是绕不开的。先师的书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当年站在父亲郑老先生身边,或听父亲转述,或亲眼看见几位先生在非学术、非官方的场景中,真实生动的样子,像是一幅幅人像剪影。
曾较长时间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勤勉工作、清廉自持的形象广为人知,但具体情形如何,一般人却所知不多。《从》书讲述的几件小事则很生动。1945年2月,梅先生在离开昆明赴四川公干之前,写信给郑天挺先生交代学校的有关工作,很是细致,包括“工警之裁减,工役伙食之津贴,甚至连一些教室之桌凳未搬,壁报张挂之墙壁已修好”等等细微琐碎的事情都一一交代,不厌其烦。后来,抗战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北返时,各校的箱子运抵北平,梅先生专门嘱咐按北、清、南、联四校分别交割,而且专门致信郑天挺先生,细致到哪些箱子装错了,哪些箱子是个人书籍等等。并提醒“点交各校之箱号码及总数,及有无损毁情形,向各校取得收据”后,一并交给迁运委员会,以便厘清责任,等等。由此,梅贻琦先生工作作风的细致和深入可见一斑。更有梅先生厉行节约的典型实例:北大复员后,梅先生夫妇打算请已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卸任北大代校长的傅斯年先生和曾任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主任的陈雪屏先生等吃饭,为此专门致函郑天挺先生,提出请陈雪屏先生家的厨师烹做,并且特意说明“在不太讲究而又不埋没厨师手艺之原则”下为之。身为大学校长、社会名流却不愿任何铺张地宴请老友、同事,在大批“接收大员”纷纷“五子登科”社会情势下,梅先生无异于一股清流,其所作所为,不能不令人敬佩。
在《从》书中,有关蒋梦麟先生工作、生活情况的直接叙述不多,但记述的1945年蒋受宋子文之邀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事及在北大教授群里引发风波又很快平息的过程,则从侧面反映出蒋梦麟先生的为人。蒋先生自己决定出任新职之前,并未知会北大及诸多同仁,这是北大同人们不理解、不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就职之后,蒋先生在给郑天挺先生的信中戏谑自己:“真乾隆帝打油诗中所谓‘而今不必为林翰,罚你江南作判通’也”,隐晦地表达了似有不得已隐衷的意思。尔后,在傅斯年先生为此事骂上门去之后,蒋本人彻夜失眠,思来想去,觉得“弟深感其言(指傅斯年)之忠直。越日驱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由此不难看出,能执掌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多年,蒋梦麟先生的人品、雅量、识见、练达等等,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及的。
胡适和傅斯年两位先生名字都是和当时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既名满天下,道德文章也是尽人皆知。而《从》一书则是从几件小事展现了胡适、傅斯年先生的生动侧面。在友人女儿的婚礼上,胡适先生身着长衫,斯文儒雅,得体地对新人讲了一番祝贺祝福的话。傅斯年先生风格迥然不同,穿了“一件全是大褶子的浅色西服”,形象也又黑又胖,块头相当于两个胡先生,上台讲教授穷,只吃得起豆腐,所以叫“豆腐教授”,引来哄堂大笑。
在1948年底北平即将解放之际,学人们不得不在“留平? 还是南下?”中做出抉择时,胡、傅二人对于友情的看重和对于故土的留恋,颇让人动容。胡适离开北平前留一字条给汤用彤、郑天挺两位先生:“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为了催促汤用彤、郑天挺等尽快南下,傅斯年先生不断写信、发电报、托人带话。其实,此时大家都心知肚明,是走,是留,已经意味着政治上是同行,还是分道扬镳。虽然分手在即,以后将是各走各的路,但彼此情分还在,不过想做最后的努力罢。但自此一别,多年的同事、朋友,天各一方,有生之年再没能晤面,让人唏嘘不已。
初读、再读、三读先师的遗著(先师郑克晟先生于2022年12月25日因病仙逝,《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一书于2023年2月出版)后,深深体会到先师作为历史学家的深厚功力,他的文字平易谦逊,如深水静流,内中的博大精深,值得后学一辈子学习。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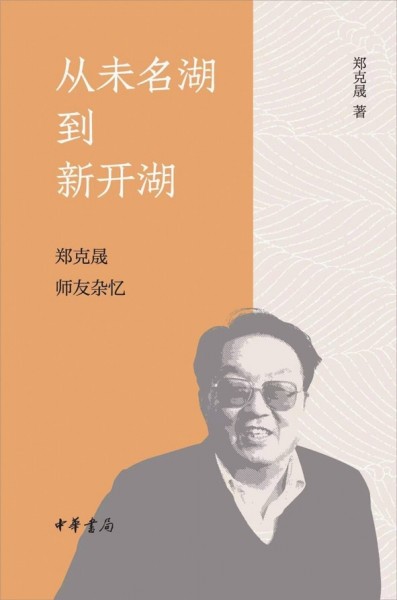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