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传》,[英]唐纳德·雷菲尔德著,徐菡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178.00元
唐纳德·雷菲尔德的《契诃夫传》首度出版于1997年。其后,作者的另一部专著《理解契诃夫:对契诃夫散文及戏剧的批判研究》也于1999年和读者见面。两部作品相继问世,在内容上互为补充,将契诃夫的生平经历与文学创作两相对照,只是后者关注作家如何书写,前者则以作家为书写的对象。
无需赘言,是契诃夫生活的年代让如此详实切近的传记写作成为可能。如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所言,对于大多数早期文学来说,传记作家无法获得足够可供参考的私人文献,因此除了作品资料,只能依赖出生证明、结婚登记、诉讼文书等公共文献。
而契诃夫的生活痕迹,首先在他与同时代人的书信往来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契诃夫像父亲帕维尔一样,“一丝不苟地保存好所有的来往信件和文件”,每年圣诞都要和妹妹玛莎一起例行整理。有时这种坚持会违背其他当事人的意愿——比如他对于友人伊萨克·列维坦临终前焚毁所有信件的请求就并未遵从。无数洇开在信纸上的文字随着作家档案从私人空间流出,成为公开文献,供人审视和评论,而话语的主人结束短暂一生,再也无法掌控它们的命运。
许多读者将契诃夫的书信视为其小说及戏剧创作之外的重要文学遗产。人们从中摘录精妙的语句,映照自己生命中的期许或失意。诸如“天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之类的短句被大家印上手机壳,挂上帆布包。而这一切,包括金句不绝的《契诃夫书信集》本身,都在相当意义上,将那些表述抽离了它们原本所处的语境。成千上万的信件往来,在书信集中变成契诃夫的千面独白,好像出土器物被陈列在博物馆,虽按照时间整齐排列,亦有清晰的信息说明,彼此之间却无连贯,那些妙语连珠也像器物的造型与花纹,失落于原本的情境和功能,读者在字里行间读出的,常常已是无关的含义。
一百多年间,已有若干传记作者将这些“陈列品”重新置入最初的时空轨道,恢复它们与真实生活的关联。雷菲尔德在此基础上,查找、收集并使用了大量未被公开的档案资料,包括近7000封由他人写给契诃夫的信件,尽可能地补全这幅覆盖了44年时光的人生拼图。
此外,雷菲尔德特别提到已出版书信的删节问题:从玛莎对哥哥遗留文本的改动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了避免对作家崇高形象的“抹黑或粗俗化”,出版方或审查部门抹去了契诃夫本人许多不够“得体”的表述,一些有损“伟大”的生活痕迹也被一并掩藏了。而眼前这部《契诃夫传》的十章内容,则恢复了大大小小体面或有失体面的鲜活表述和日常细节。
雷菲尔德对契诃夫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与女性之间关系的呈现,填补了早前被遮蔽或忽视的空白,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窥私愿望。
一直以来,契诃夫留给很多读者的印象都是一位禁欲的圣徒式作者,一生孤独,仅在病入膏肓的生命尽头遇到挚爱的女演员,并在她的陪伴下离开这个世界。雷菲尔德则毫不避讳地写道,契诃夫自十几岁起便开始出入性服务场所,所到之处更有无数身份迥异的女性成为他情感生活中的匆匆过客。契诃夫对女性颇具吸引力,亦曾多次与有夫之妇私通。尽管这种人见人爱的总体印象或许失之偏颇,因为那些在档案资料中留存下来的,仅仅是不可计数的相遇与相识之中,一部分得以建立和深化的关系。
在雷菲尔德的叙述中,契诃夫对女性的兴趣总是转瞬而逝,亲密关系通常只能持续几个星期:“对于女人,安东·契诃夫总是反复挑逗,然后无情抛弃。他的兴趣从一个女人转移到另一个女人身上,他并没有花费心思去寻找心目中的理想爱人”。
1892年3月7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赞同了对方关于女性的看法:和睿智、理性的男人不同,女人最不讨人喜欢的地方就是她们的不公正,她们好像天生就不具备公正的品性。关于女人缺乏理性和正义感的观点,可见于叔本华《论女人》一文。雷菲尔德指出,契诃夫和列夫·托尔斯泰一样,认同叔本华将女性视作次等性别的种种表述,而这种厌女观念在当时的俄罗斯文坛十分风靡。
契诃夫并不压抑情欲,却长期回避爱情和婚姻。关于这一点,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契诃夫的一生》中写道:“蜻蜓点水的艳遇、暧昧的友谊、脉脉的柔情,这就是他感情生活的基调”;“一旦契诃夫感到有人想要拥有他的整个心灵,占据他的整个生活,他就开始逃避,且是以极其温柔体贴的方式逃避,以致对方完全无法对他有所抱怨,那失意的多情人最终变为朋友(但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了伤害)。”
内米洛夫斯基在这本小书中并未展开详述契诃夫的情史,而雷菲尔德则为我们呈现了数不清多少倏忽冷却的激情、一厢情愿的热忱、插科打诨的敷衍。不夸张地说,契诃夫对待大多情人的态度都有着“用后即弃”的意味,当然这种态度有时是双向的,哪怕是他与奥尔伽·克尼碧尔的关系,在仓促来临的告别之前,也不乏紧握稻草般的利用和三心二意的背叛。
有时,女性的爱慕会成为契诃夫文学创作的养料。比如,《海鸥》中妮娜送给特里果林的那枚刻了作品名、页码和行数的纪念章,就来自一位名叫利迪亚·阿维洛娃的女士单方面赠予契诃夫的爱情信物——只是她为契诃夫订做的不是纪念章,而是一枚项链坠饰。现实中,契诃夫对阿维洛娃的盛情冷淡回避,但这枚爱之坠饰却化身纪念章,寄托着“这么纯洁的一个灵魂的召唤”,成为《海鸥》中巧妙的点睛。
在亲密关系之外,冷漠也伴随着契诃夫的一生。由于昭然若揭的指涉和讽刺,他的作品曾多次招致现实中亲友同事的不悦,有时更会让倾慕者深感真心错付,但作家本人对这些却似乎毫不在意。与契诃夫有过长久牵绊的丽卡·米济诺娃一语道破他惯有的冷漠:“无论您说出或做出任何伤害别人的事,其实您都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因为您真的不在乎别人如何看待它。”这份疏离,以及疲惫的淡漠,也该溶入契诃夫所追求的“自由”的底色。在时常被人簇拥的一生中,他却一次次不可抑制地逃离。
契诃夫在亲密关系中的浮躁和退避促使我们将目光投向他的童年和家庭,其中一个关键人物便是他的父亲帕维尔。契诃夫对帕维尔的称呼一向是“父亲”,而非“爸爸”或“爹爹”。塔甘罗格时期的棍棒教育和对唱诗事业强迫性的热忱、初到莫斯科时的无能大家长作风、梅里霍沃时期暴君式的农庄管理等等,都让帕维尔这个固执、强硬、唯我独尊的“一家之主”形象跃然眼前。
1889年,契诃夫在写给亚历山大的信中如此回忆童年的境遇:“我请求你回想一下,专制和谎言扼杀了你母亲的青春。专制和谎言极大地摧残了我们的童年,让人回忆起来只觉得恶心和恐惧。”雷菲尔德在叙事中也提到了这一关键表述。在同一封信中,契诃夫对哥哥说,任何一种个人生活的困境和家庭生活的不快都不应成为专横的理由,宁做受害者,不做刽子手。
雷菲尔德在前言中提到,契诃夫在作品中从不将任何哲学观点强加于人。了解了帕维尔·契诃夫在家庭和社会事务中的行事风格之后,我不禁想到:安东拒绝在作品中进行道德说教或观点输出,是否也和他对父亲角色的态度有关?
尽管成年之后的契诃夫也在自己身上发现了父亲那种固执易怒的脾性,但他似乎早早为自己的言行划下红线,也始终避免成为“大家长”式的写作者,不愿将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任何人。儿时如“小苦役犯”般无端承受的苦痛让契诃夫对世人永远多一分共情,更让他的叹息中少一些居高临下的怜悯。
文学创作之外,契诃夫也是医者仁心。从萨哈林岛返回之后,他在彼得堡奔走游说,为萨哈林的儿童乞丐和雏妓设立收容机构,还为他们寄去书籍;在梅里霍沃,他为当地农民建立学校,帮他们排忧解难;在雅尔塔,他看到贫穷患者的艰难处境,便决意为他们修一座疗养院。1901年夏天,契诃夫起草了一份遗嘱,交给玛莎保管。他在结束语中写道:“你要帮助穷人。要照顾母亲。祝你们平安。”
然而,契诃夫对公共福利的关切与他对自身健康的漠视形成鲜明对比。从母亲叶夫根尼娅的家族病史开始,结核病始终是契诃夫头顶悬着的剑。我们几乎可以将结核病视为这部传记的另一位主人公,或者用雷菲尔德的话来说,“结核病塑造了安东·契诃夫的生活”。
1901年5月17日,契诃夫在莫斯科接受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和病史问询。雷菲尔德为读者呈现了当时的病历记录——幼年记事起持续的咳嗽、20岁起的腹泻、24岁的第一次咯血、37岁的第一次大出血……如此种种,时时威胁,伴随一生。
对于自己身上间歇显露、愈发恶化的症状,以医学为业的契诃夫却表现出回避和不屑的态度。他坚持说自己的症状并不足以支持结核病的诊断,习惯性地掩盖和轻描淡写,也抗拒被旁人问起相关事宜。雷菲尔德甚至写道,契诃夫的藏书之中没有一本是关于结核病的。
1891年11月18日,契诃夫写信给苏沃林:“我继续变蠢,变傻,变冷漠,虚弱,咳嗽,而且开始顾虑,我的健康不会再回到从前的状态了。尽管如此,一切都是天意。治疗和对自己身体的关心让我有一种近乎嫌恶的感觉。我不会接受治疗。我会喝水,服用奎宁,但不会允许自己去看病。”在雅尔塔医生伊萨克·阿利特舒勒的回忆中,一直到1901年,契诃夫才坦然接受,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病人了,然而此时他的病情早已发展到毫无康复希望的境地。
伊格纳季·波塔片科认为契诃夫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只是假装勇敢,担心过多留意便是胆怯的表现。隐瞒、敷衍、拒绝谈论,恰恰是担忧的在场证明。其实他也时常希望到温暖的地方生活,知道那样的气候能让自己好转。也许他只是不愿把时间和精力用来尝试各种未经证实的药物和疗法,深知这一切都是徒然,有限生命中,应当去完成更重要的事。
在这部编年史式的《契诃夫传》中,生活的琐碎几乎吞噬了所有将作家的一生概念化、崇高化的可能。有批评者认为,虽然苦功可贵,但数量不能转化为质量,如果雷菲尔德试图利用海量原始档案资料来还原一个“难以捉摸”的契诃夫,他的尝试终究是失败了。而在我看来,这些看似缺乏提炼、主次不明,甚至略显散乱的人事物,反而更加接近现实生活的本来样貌。这里我们提到“现实生活”,而不是“安东·契诃夫的真实生活”,因为后者始终是不可还原的。雷菲尔德自己也写道,一切传记都是虚构,只是应当符合有据可考的事实。
在纷乱和反复、抵抗和妥协之中,我们仍然清晰地看到一位创作者的生活秩序。他温和平易,但又冷漠疏离,而他所跋涉的一生,既有内米洛夫斯基所写的烟花般寂寞,也还有些别的什么,比如激情、恐惧、单纯的欢笑和朴素的坚持。
如高尔基所言,契诃夫“善于在一片晦暗的庸俗里揭示出它那些悲惨阴郁的玩笑”,他哀痛地目睹种种可鄙可悲或冷酷无情之物,却将它们掩盖在滑稽可笑的“幽默”之中。这部几乎包罗万象的《契诃夫传》或许能让我们更加确信,契诃夫终其一生凝视和诘问的,也正是他不断拥抱和逃离的生活本身。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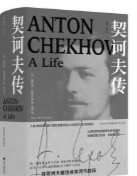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