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记、书信这类私人文献越来越受关注,出版界也很乐于推动它们的出版。利用日记做研究,从史学界、文学界开始到科学史界,逐渐向整个学术界蔓延,但教育史学界利用日记者还不多见。浙江大学田正平教授2008年以阅读恽毓鼎日记为始,开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持久阅读,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我作为田老师的“私淑弟子”,对他这些年来对日记的兴致自是了然,他的几篇近作在完稿后第一时间就先睹为快,还曾就其中一篇“胆大妄为”地提过修改意见。2023年9月,收到田老师签名版《日记里的教育世界》,自然欢欣雀跃。
在近代日记大量整理见刊和影印出版的当下,如何在学术研究中合理利用这类数量剧增的史料,选择哪些阅读对象,自然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田正平教授给出了他的考量标准:“出于专业背景和阅读兴趣,我在选择阅读对象时,大致遵循这样的思路:一是努力把近代以来的一个多世纪连贯起来,做到在时间上不断线,特别是几次大的教育变革,不能留下空档;二是人物的涵盖面尽量广泛,力争做到各个群体都有代表性人物,不留空白。”《日记里的教育世界》一书所关注的13位日记作者,既有晚清朝廷重臣曾 国藩(1811-1872)、皇帝近臣恽毓鼎(1862-1918)、地方学政严修(1860-1929),也有普通塾师管庭芬(1797-1880)、刘大鹏(1857-1942)、刘绍宽(1867-1942)和朱峙三(1886-1967),有新式大学中的管理 者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890-1974)、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1899-1981)和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1898-1948),有民间社会团体江苏省教育会核心人物黄炎培(1878-1965),还有风云人物梁启超(1873-1929)。
这十三位记主,社会地位悬殊,年龄、地域不同,即便同处于大致相同的环境之下,对同一历史事件,日记中留下的个人感受也可能完全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亲历了近现代教育变革——科举停废、新学堂兴办、中西文化之争以及知识分子的定位等,有着异中有同的感受。比如对停废科举的态度,科举世家的恽毓鼎在日记中流露出来的感受和认知,与山西举子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和湖北秀才朱峙三在其日记中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但观念与行动之间的“错位”却异曲同工;比如教育子侄,曾国藩和梁启超虽展示出不同的教育理念、途径和视野,但传统文化的影响却同样深镌心底;同是观察美国教育,临时海外考察的黄炎培和留学七年的胡适,在日记中给出迥异的心得,但“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传统士人担当却一般无二。
利用日记这种承载个人情感的文本作研究,需要学者的学术研究与生命体验的珠联璧合。但在学术操作性越来越强、技术至上的当下,体念记主所说的那些事情,感悟他的内心活动、世态人情,追问那些压在纸背的情怀,已越来越稀缺。《日记里的教育世界——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感动我的,不仅是学识,更感动于作者诠释了压在纸背的士人情怀。作者深情写道:“阅读的过程对我而言是与日记主人一起重新穿越历史的过程,我常常沉浸其中不能自已,有时甚至有一种受到强烈震撼并提升境界、净化灵魂的感受。”“这些年来除必需的教学和培养研究生工作之外,我确实一直沉浸在晚清、民国士人日记研读的苦乐之中,真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阅读日记的过程,仿佛就是跟随记主将其生活体验一遍。也正因为如此,记主一个个从历史深处走来,成为活生生的人。比如作者通过日记,分析身处庙堂之上的恽毓鼎作为正途出身的科举受惠者,在清廷宣布立停科举当日,恽氏不敢流露对皇帝的不满情绪,却对力主此举的张之洞、张百熙大加挞伐,“他日公道犹存,非追削官谥不可”;但道义上的抨击并不等于将家族命运与之捆绑,这位愤懑溢于言表的皇帝近臣,却在废科举的第二天迅速改弦更张,令长子“专一研究政法学,为他日致用之道”,此后又令多位子侄进入政法学堂读书。普通士子刘大鹏面对科举停废,同样表现出思想与行为的严重脱节。作者由此指出,从朝廷高官恽毓鼎到民间的刘大鹏,都在新旧两种教育制度的双重夹持下表现出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理,是清末民初教育变革下的士人中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
再如通过解读浙江海宁的乡村塾师管庭芬的日记,发现鼓浪而来的西方列强没有给其生活带来一星半点的近代信息,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只是进一步加强管氏对圣恩之下享受平静生活的期盼和向往。面对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大变动,面对中国步入近代大门,管庭芬和他的朋友们依然在既有的轨道上踟蹰前行,日常照样结伴郊游、饮宴、对弈、吟诗联句,传统士人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改变。“对绝大多数普通读书人来讲,对待这些变革的态度归根到底是受个人利害得失制约的”,作者写道。
通过对竺可桢、郑天挺和朱自清三人日记的阅读,作者为读者呈现了知识分子特殊时期的家国情怀。执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在昏暗煤油灯下写下的数百万言日记,激荡着他兼采中西、融汇古今的办学理念,“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境界,克己奉公、以身许国的道德情操,一位有风骨的大学校长让人印象深刻。郑天挺作为西南联大的总务长,他的日记则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一位有深厚学术造诣的学者,如何服从大局,为学校发展殚精竭虑、为琐碎校务辛苦奔波的身影,通过日记解读,一位临事以忠、待人以诚、言行笃实、谨慎立身的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形象跃然纸上。朱自清对大学教职心怀敬畏,时时反省,刻苦勤奋,在贫困与疾病的考验中彰显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也是摆在近代士人面前的重大问题。中华民族千百年积累下的丰富教育文化遗产,向来为读书人所服膺。在遭遇欧风美雨强烈冲击下,那些传统的士大夫以及有机会走出国门的游子们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中国本土的教育经验?作者给出了四个不同案例,两两一组,各有侧重。第一组是曾国藩和梁启超:一部150万言的《曾国藩日记》中刻画的读书、修身和治家之道,是中国民族文化哺育下的簪缨家族教育子弟的精髓。而《梁启超家书》展示了父亲对儿女成长的殷切教诲,这些家书,一方面自觉承接了传统的立志、求学、做人、治事的家教精神,充盈着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另一方面,又主动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先进观念、思想融入其中,将“新民”理想和“少年强而中国强”梦想落入育子实践中来。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化,未能改变士人教子治家的文化传统。第二组是胡适与黄炎培,胡适留美七年,个人兴趣却集中在中国古代哲学及宋明儒学论述,在他的日记中多次留下“读《召南·邶风》”“读《说文》”“读《王临川集》”,最终促使他将所学专业从农学改为哲学,青年胡适的自我期许发生了变化:“吾辈去国万里,所志不在温饱,而在淑世”,“旧学邃密”(蔡元培语)唤起了胡适“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的自觉”。黄炎培在1914-1916年期间,国内国外教育考察各进行了两次,出版的四辑《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核心思想便是“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内国考察,寻病源也”,立足国情,明辨择善的态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沉淀之后,读来仍让人感动。
按照作者设想,从2008年开始,每年读一至两部日记,期以十年能有小成,但落实到实际阅读中却甚为艰辛。“有些日记篇幅很大,像《竺可桢日记》有一千三百多万字,一年时间根本无法读完,我只好先阅读他主持浙江大学校政期间十三年的部分;有些日记则是读了几遍后仍觉得抓不住要领,难以下笔,或者是写出来之后,自己仍觉得意犹未尽。”“两句三年得”“捻断数茎须”,在当下“出快活”“跑马圈地”的学术氛围中,这种阅读和产出方式透着强烈的“不合群”。
诚如作者所言,书中的一篇篇札记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阅读量。私人日记作为最有人生感的第一手资料,记主逐日、逐月、逐年的具体琐细记述,宏大的历史被时光流年碎影化,转化为他的言行、见闻、思想乃至情绪,被定格在纸面上。这些日记,动辄百万字篇幅、百卷之巨,要在百万字篇幅的日记中寻找出记主的教育情怀,使其能前呼后应,自成体系,除去高超的写作技巧、条分缕析的考证功力,更需要大量的、沉得住气的经年累月的阅读和思考。可佩的是,作者以学识为基础,以阅历和才情为两翼,配上适宜的写作技巧,“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将这些定格的文字再次转化为“活生生的个体”,施施然从历史深处走向读者。
通览全书,或许会有某种“成功人士”的“踌躇满志”“运筹帷幄”弥漫之感,恍如那种校友回忆录,全是对昔日峥嵘岁月的慷慨激昂。这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题材所决定的。书中所选的十三位记主,尽管境遇和立场不太一样,但基本都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弄潮儿”,在巨变之下或主动或被动,都能有较为从容的应对和转身。那些“落魄江湖”的,或者不愿意或因为后人各种顾虑而日记未能行世的学人(比如绍兴学人周福清临终前一天还在记日记,留下红条十行纸写就的线装、如桌子一般高、两大叠日记,却被1919年回乡接母亲入京奉养的长孙鲁迅一把火付之一炬),或许有和书中所选记主不一样的遭遇和看法。能流传于世的,必定偏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惠风和畅”。说这些,也是提醒读者朋友,历史、私语和阐述之间是有张力的,日记的局限性和它的巨大价值同样值得大家注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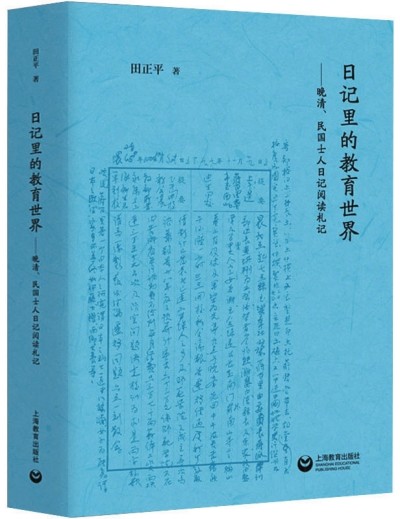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