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按照我的思维习惯,要谈这本有着冗长书名的著作,恐怕先得搞清楚什么是“视觉理论”。但是作者显然是另一种思维习惯,他并没有在本书开头先向读者交代“视觉理论”的基本内容或概要,而只是在叙述中陆陆续续提到了一些与此有关的内容。因此我不得不在这里先冒险将我的理解用大白话尝试陈述一下。
首先,本书讨论的事情,和录像、摄影、绘画等等有实物记录的视觉材料完全无关,而是仅限于用文字表达的关于“看见”某些事物(比如鬼魂)的陈述(虚构或非虚构的)。
自然,在上述研究范畴的约束下,所谓“看见”就会变成一个可以从多方面质疑的、非常复杂的概念了。例如:“看见”的陈述无论多么真诚,都可以是幻觉,而这又可以分成多种情况,比如因视觉器官(眼睛)的病变而导致的错觉、因某些病态的心理活动导致对视觉信号的误读、因正常或不正常的思维方式导致对视觉信号的重构……总之,任何“看见”的陈述,都已经很难承受得起“你真的看见了吗”这样的诘问了。
一旦我们拥有了这样与科学紧密相关的“视觉理论”,持此作为利器,来对维多利亚文学作品中的鬼魂(或吸血鬼等等)叙述文本进行学术操作,则其别开生面、引人入胜的结果,必定是可想而知的了。
刘:
你的感觉确实很敏锐。因为我以前也曾和学生一起做过一些和“视觉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视觉文化相关的工作,比如对视觉科学史的研究进路的编史学研究,或对科学漫画的历史研究,或对与石印技术相关的视觉文化研究等。那些,确实是与从文字转向图像的传播有关。此书作者研究的对象并非实际的图像,而是在维多利亚文学中所表现的对鬼魂的“目击”,但这种在文学中以文字呈现的“目击”,显然也与“视觉”相关。
另外,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因为众多作为近现代科学之基础的“科学事实”,即那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的经验证据,也都来自实验者的“目击”,而科学哲学中也有“观察的易谬性”或“观察参透理论”之类的学说,专门讨论在用眼睛观察中的各种问题,对于人们惯常所说的“眼见为实”等提出反证。这一类的“视觉”理论,应该是和本书中所用的概念比较相近。
但此书还是另有特色,其一,是其研究对象,是维多利亚的文学,而关注的主题,又是“鬼魂”,又涉及像“科学中的视觉理论”这样一些传统的科学文化研究不太关注的东西。其二,是研究者是文学研究背景。这两者结合起来,加上书名,足以引起像你我这样喜欢新视角、新观点的人的兴趣。
此书的总体倾向,我感觉还是唯物主义的,作者试图对各种“鬼魂”陈述给出尽可能科学的解释。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经常想起我父母旧宅中的一些故事。那个旧宅建成距今已逾百年,底层住着三户机关干部,都是数十年的老邻居,其中一户男主人去世后,家父就说他有时在公用厨房或走道上遇见此人。家父叙述此事时十分平静,就像在谈论一个还健在之人的家常琐事那样。之后家父去世,邻居也不止一次说在三家公用的小花园中遇见家父在散步。家父晚年确实喜欢在小花园中散步,还会打理一些他种植的花草。
这些陈述,与中国古代传统的鬼魂学说非常符合。如果想领略一下这种传统鬼魂叙事的风格,在《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之类的笔记中随处可见。鬼魂会回到生前习惯的生活场所,往往并不引起生者的惊恐,他们甚至会“恍惚中忘其已死”而与鬼魂交谈。
而根据本书所讨论的“视觉理论”,上述旧宅中的鬼魂叙事,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更为唯物主义、更具科学性的解释:那不过是旧宅中健在的人们对自己视觉器官获得的视觉信号的误读而已。至于这类视觉信号如何形成,本书作者比较注重从光学的路径来解释。
说起用光学来解释鬼魂的“视觉信号”,中国也古已有之。例如《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方士为了满足汉武帝对已故宠妃的思念,说等夜晚自己作法后,汉武帝就能够见到她,结果夜晚“天子自帷中望见焉”。看来这位方士(齐人少翁)对于利用光影操弄“视觉信号”是颇有心得的了。
刘:
关于“科学与文学”的研究,在西方的STS领域中,已是一个传统比较悠久的大类别了,尽管这类著作翻译引进的并不多,因而本书还是很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
你想到的“对标”中国的情形,也确实是很有某种在类型和内容上的相似性。除了各种笔记中的记载之外,就在当下,人们也确实经常会谈起这样一些鬼故事。而当事人,或者转述者,也经常是信誓旦旦地说这是真的,是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在一些地方的旅游解说中有时也会涉及这样的传说,甚至在目前流行的短视频中,还专门有人做这样的专题。只可惜,我们很少有人专门从学理性的角度对之进行认真的研究。
以你所说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以及科学的原理,当然可以对之做出“科学”的解释。不过从解释的传播效果来看,这样的解释是否足够令人信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否则人们为什么还会经常津津乐道于此类话题呢?
以唯物主义的立场,根据科学的原理给出解释,这是一种类型,前提是相信科学。但解释只是对这类说法的一种说明,与科学中以实验的方式来验证,还有着很大区别。这里不同的理论前提预设,以及不同的文化概念系统,是不是也有着另外一些重要的影响呢?
我的感觉是,本书并没有、作者也未打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的“不同的理论前提预设”,直接导向了这样的基本问题——鬼魂到底存不存在?当我们让讨论进入“学术”层面之后,这个问题就不能以简单的信仰站队来解决了。迄今为止,虽然没有任何被科学共同体普遍认同的证据能够证明鬼魂存在,但是也没有任何关于鬼魂不可能存在的有效证明(例如像对“尺规作图不可能三等分任意角”的证明那样)。类似的状况同样存在于外星人、上帝等等的问题中。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事实上只能各说各话。
本书作者将讨论的时间段限于“维多利亚”时代,从理论上说就是1837~1901年。在这个时代,科幻作品是法国人儒勒·凡尔纳当道,英国的H. G. 威尔斯要到这个时代的尾声中才大举登上科幻舞台。本书所分析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侦探小说类型中,这从书前的“缩略语”一览表中可以清楚看到。
侦探小说当然是讨论“视觉理论”的合适对象,因为里面不可避免地会充斥着真真假假的关于“看见”的陈述。然而奇怪的是,作者却对幻想作品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道德批判。作者认为:“现实主义文学雄心勃勃,想要推动社会改良……而有关鬼魂、精灵或梦淫妖的叙事文学则违背良心、逃避现实,也就是不负责任地逃离真实的世界。”作者甚至援引了马克思主义来对幻想作品进行批判:“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危险的镇静剂。”作者说幻想文学“本质上说一种任性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上的误判”。
但是,同样的道德批判标尺,如果用到作者在本书中如数家珍般论
述的柯南·道尔的作品,或是艾伦·坡的作品之上,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作者对幻想作品的这种奇怪的义愤填膺,不知是不是和你上面所说的“不同的文化概念系统”有关?
刘:
前面你讲的,是科学的信念问题。因为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科学相信没有超自然的存在,虽然无法以科学验证的方式来“证明”鬼魂不存在,但对其不存在给出“科学的”“解释”,也还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科学也完全可以因为其信念而将鬼魂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至于后面,你谈到的则是道德问题。这就更超出了科学的范围。由于不同的初始立场和预设,人们在对道德问题的讨论中,以及批判中,有着不同的判断也是很正常的,但这显然无法成为科学的判据,也不能成为鬼魂存在与否的最终“证明”。
按你所问,同样的德批判标尺,用到作者在本书中如数家珍般论述的柯南·道尔的作品,或是艾伦·坡的作品之上,显然也是可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对于研究的不同类型的对象,当然不能采用双重标准。此书作者对幻想作品的这种义愤填膺,我觉得虽然也可以说是与“不同的文化概念系统”相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与作者的哲学预设立场相关,并且因这样的预设(也是某种哲学信念吧),而潜在地先有了结论。而且,在这里,比如“真实世界”的概念,就并非人人都有同样的理解和认知。
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论证逻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正因此在我阅读此书时,当涉及具体内容时,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我最初的预期。
江:
不过阅读本书还是有启发的,它至少提醒我们注意“看见”陈述在科学和哲学意义上的复杂性。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最初我就注意到作者的讨论完全不涉及录像、摄影、绘画等实物材料,而在本书所论述的那些侦探作品中,警探和作者为了各种“看见”陈述的真伪大费周章,初看起来,似乎只要有了尽可能多的摄像头,有了录像,许多“看见”陈述的真伪立刻就能真相大白了。但再往深处一想,事情还是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这仍和“鬼魂到底存不存在”的基本问题直接有关。即使先搁置这个问题,但因为对鬼魂的物理性质完全缺乏了解,比如鬼魂有没有质量? 占不占空间? 行动受不受万有引力和光速极限的限制? 在许多故事中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如果是这样,那它们无法被摄影设备所记录也就顺理成章了,于是“看见”陈述的真伪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刘:
你说的这两个问题确实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对鬼魂的物理性质“完全缺乏了解”,即使在录像上看不见,也还可以再附加上一些光学性质的解释,比如它是否可以不服从普通光线常规的反射折射等规律。当然这又违反了科学哲学中不允许“特设性假说”的要求。但也让我联想到了物理学中时髦的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那么,问题似乎就回到了更哲学的“存在”概念上。如果鬼魂就是这样一种无法被物理地“探测”(也即广义的“看到”)到的东西,以物理的方式自然就无法肯定地说明其存在或不存在,从而被排斥于科学研究的对象之外也就顺理成章了。问题于是又变成了,世界上是否可以有这样的“存在”? 这似乎就成了一个哲学问题。
而人们(例如那些喜爱或害怕谈论鬼故事的人)对这样的“存在”的热衷,也许就只是因为其有别于科学所依赖的哲学的信念吧。信念,并不一定需要科学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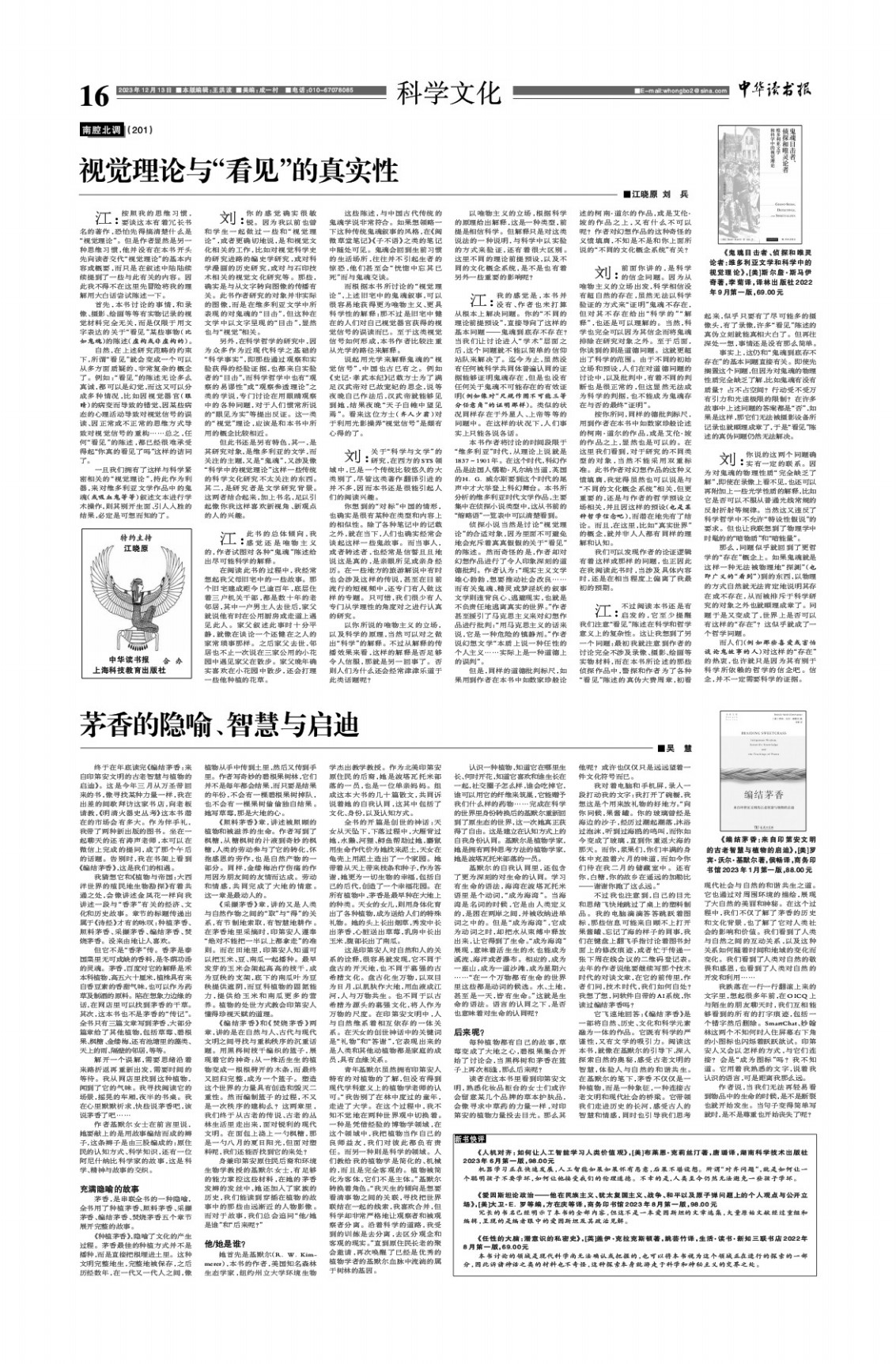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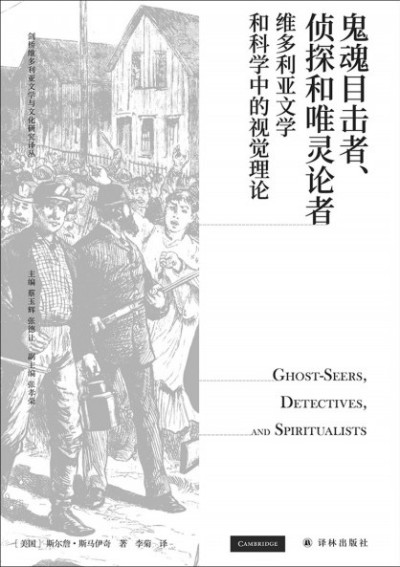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