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宗先生在87岁高龄出版新著《超脱寻味〈红楼梦〉——超脱境界对话录》,实在令人感佩。这部著作在他的整个著述系列中有其特殊性,因而也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黄伟宗先生把他的耄耋之年抛掷在《红楼梦》里,孜孜于求解其中的真味。他提出《红楼梦》的十二个美味境界:憧味、辩味、禅味、恩味、情味、诗味、画味、特味、食味、余味、争味、假味,一一评说。个人认为他研究《红楼梦》有三个特点:一是以“超脱境界论”言说《红楼梦》,将《红楼梦》看作是“超脱境界”最典型的艺术代表;二是对自《红楼梦》诞生以来的三百年红学研究进行了梳理、概括和评点;三是这本书采用了柏拉图式的对话录形式,以虚拟师生问答的方式完成,为《红楼梦》研究中所仅见。
一、以“超脱境界”言说《红楼》至味
黄伟宗先生所使用的作为艺术概念的“超脱境界说”脱胎于王国维的“境界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王国维看来,“境界说”的三重境界既适用于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同时也适用于文学创作,即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过程也一定包含了三重境界的转换与进阶。但黄伟宗认为王国维没有说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写作者或研究者是怎么从第一境界进入到第二境界再进入到第三境界的呢? 其中的动力和途径是什么呢? 在这里,黄伟宗有他的领会,他领会到这个动力和途径就是超脱。不仅从第一境界到第二、第三境界需要超脱,就是每一境界内部也需要有超脱作为动力。比如第一境界,有从“昨夜西风凋碧树”的当下处境与视野到“望尽天涯路”的辽远境界的超脱;第二境界的苦思冥想里也包含着反复的超脱;第三境界则经历了从“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执着到“蓦然回首”时突然发现的超脱,所以“三境界之间及每个境界中都有重重超脱的关系与内涵”。任何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不断地从一个超脱境界再创造新的超脱境界”的过程,“也好似宇宙飞船那样,不断地依托而又层层超脱运载火箭的输送飞上太空遨游的诗意境界”。
我们要注意到黄伟宗先生所说的“超脱境界”包含两个辩证的方面:依托和超脱。首先是依托,然后才有超脱。依托是实,超脱是虚。依托是基础,超脱是超越。没有依托,超脱将成为空中楼阁;而没有超脱,依托成为拘泥,是一只飞不起来的泥鸟。依托与超脱是艺术创作的两翼,它们相辅相成,共同完成“超脱境界”的创造。黄伟宗先生用这样的“超脱境界”概念解释《红楼梦》创作的全过程,从创作的初始到结束甚至到作品的接受传播,超脱无止境,使《红楼梦》永葆魅力。从创作的初始动力来说,黄伟宗先生解释曹雪芹为什么能去写作《红楼梦》这样一部“满纸荒唐言”的小说,这里面就包含着作家对所处处境的超脱。小说在当时的地位不像今日,小说家也常常不留真名,而曹雪芹抛掷十年时光(甚至可说毕生精力)去写作此书,在当时简直可以说“不务正业”,更何况还如此穷愁潦倒,“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举债食粥,在这种境遇下还能以如此毅力完成这部巨著,没有“超脱”之境界如何可能? 但超脱中有依托,他的写作“依托”于他的人生遭际和生活经验,正是曹雪芹复杂的人生经验给了他丰富的写作素材和创作冲动,这是创作初始阶段的超脱。真正进入到创作过程,还需要另一层的超脱。胡适考证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然而作为一部小说,如果只是对自我和家族经历的记录,肯定难以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它必须在多方面超脱于“自叙传”,必得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才能完成一部伟大小说的使命。为什么要这样呢?“一方面,是创作的需要,若全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则不能放开手脚写作,还会影响作品的典型意义。……另一方面,是有所顾忌,以防不测。”这是指“文字狱”。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一部作品必须实现它的普遍意义和象征意义,必须超脱于时世与真假之上。《红楼梦》极其令人着迷的地方还在于其凭借“假语村言”所完成的伟大的想象结构。它一开篇就气势不凡,以一个“神怪的、荒诞的、超脱常理的故事”来讲《红楼梦》这部书的缘起。这是一个“僧道二仙将一块石头化成‘宝玉’,由贾宝玉含着投胎到王公贵族的贾府中,经历了极度的荣华富贵与儿女情仇,最后全都像做梦一般幻灭的故事”。小说以“元叙事”的方式告诉读者,《红楼梦》是一部写在石头上的书,是那块顽石对自己在人间走过一遭的记录,“曹雪芹”不过是抄录者、加工者而已。这一元结构的存在大大拓展、升华了小说的内涵和哲学意味。每个人从这个结构中领悟到的意蕴或许不一样,但是它都会引导读者超越具体而进入普遍意义的领悟。俞平伯因此将《红楼梦》的主题归结为“色空”二字,这是佛教的世界观。黄伟宗则进一步具体化为佛教之六祖惠能禅宗哲学,“石头”从来处来,到去处去,最后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小说对自叙性的超脱。没有这一超脱,小说的意义空间会大打折扣,然而这一神话结构的超脱又建立在对人间生活和俗世情缘的具体细致的书写上,二者缺一不可。
黄伟宗先生曾著《文艺辩证学》一书,论述文学艺术无论是从总体还是具体某一方面的特征、性质来看,都充满了多种层次的对立统一关系(张力),依托与超脱也可以看作是一组基本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组关系也可以用于小说创作与欣赏的多个层面。如上是从总的虚实结构上来看的,而从更具体的某一方面的描写来说,《红楼梦》叙事艺术里也贯穿着依托与超脱相反相成的超脱境界。比如,黄伟宗先生分析《红楼梦》中的“食味”时,就既给我们展示了《红楼梦》如何描写美酒、香茶、美餐、盛宴本身,同时也分析了作品在描写“食味”的同时如何超脱了“食味”。出身诗礼簪缨之族的曹雪芹是真正懂得饮食之美的,那些各式的香茶和美酒、美食是要用什么样的原材料、通过什么方法制作、贮存,用什么样的器皿盛放、食用,他真是如数家珍。比如贾府的“茄鲞”怎么做,妙玉招待宝玉等的香茶来自何处,宝玉被父亲暴打之后想吃的“小荷叶小莲蓬儿的汤”做起来有多麻烦,都写得很精细。但是,这些“食味”的书写既来源于真实,又是超脱于真实之上的。旧时贵族人家的“茄鲞”真的是这样做的吗? 且不说陈年的雨雪埋在地下还能不能喝,光是妙玉给黛玉和宝钗用的茶器,其真实性就很可疑。沈从文先生在1957年就以他的文物学知识证明了那是作者的戏谑之笔。以给宝钗用的“分瓜瓟斝”杯为例,这是明清之际方才流行的葫芦器,而上面镌刻有晋王恺珍玩宋苏轼见于秘府,这不是与“宋版《康熙字典》”一样的“假古董”吗? 再看这三个字的发音,活活的“班包假”。那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无非是渲染贵族人家的奢华或者贵族小姐的讲究。然而仅仅如此吗? 黄伟宗先生认为不止如此,在此之上还有写人的用意。看王熙凤伶牙俐齿说“茄鲞”的做法,那就不只是介绍,还有得意和夸耀。宝玉想吃那个汤,王熙凤趁机叫人做了十来碗,给贾母王夫人等都送了,也是八面玲珑地讨好。至于妙玉的茶与杯,也是写人的好道具。一方面写了她的讲究与清高,另一方面,这讲究里面又有点故意做作,隐含着凡心未泯。而当宝玉开玩笑抗议给钗黛的都是古器珍玩,而给他的只是妙玉日常自用的“绿玉斗”时,妙玉的情感秘密也泄露了,原来妙玉对宝玉是另有一份情意的,因为以妙玉的洁癖,她不可能给一般人使用她用过的东西,刘姥姥喝过的成窑杯(明代古董),她一句话就说扔了,嫌脏,宝玉请求才送给刘姥姥,而之所以答应送,是因为她本人没用过,“若我使过,便是砸碎了也不能给他”。黄伟宗先生在这里的分析独具慧眼,读出了“味外之味”。
全书品读的《红楼梦》十二味,除“争味”“假味”篇之外,都是关于《红楼梦》本身的文本研究的,这些关于《红楼梦》种种超脱境界的精细品读,显示出黄伟宗先生对于《红楼梦》全书及细节烂熟于心、信手拈来的文本功底以及诸多新鲜的见解。黄伟宗先生说《红楼梦》当然不只是十二味,它是“集中华‘美味’大成之大著”,只要细细欣赏,一定可以品味出更多的美味,并上升到哲学、禅学、人学、伦理学、美学、文化学、文艺学等层面的。
二、对三百年红学的精当概括与点评
“超脱”的意思是“不拘泥”,不被陈规、传统、形式等所束缚,不被世俗、利益等各种容易束缚身心的事务所束缚,达到超越所有这些事物的自由境界。“超脱”是黄伟宗先生人生词典里的关键词,他的人生信条就是:“以超脱做事,以做事超脱。”一个人“做事”的时候不要太功利,太功利做不好事情,只有超脱才能专注于事情本身,把事情做好。一个人不做事,会感到十分虚无,所以一定要找事做,在做事中获得充实感,比如研究《红楼梦》就是他为自己晚年找到的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天地间皆有超脱,超脱中自有天地。超脱自有的天地,就是超脱境界。”黄伟宗先生是讲究并实践人生的超脱之道的,而同时他也将超脱看作是艺术之道,是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核心特征,在文学艺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环节、各个层面都包含着超脱境界,没有超脱就没有艺术,至少不会有高妙的艺术。所以他自始至终贯穿以“超脱境界”言说《红楼梦》,这也是他言说《红楼梦》的很明显的个人特征。
所谓“争味”是黄伟宗对《红楼梦》诞生三百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各种派别和观点的论争现象的概括,将论争现象的存在称之为“争味”,也可见黄伟宗先生的超脱立场和境界,就像坐山观虎斗,哪一方都有哪一方的看头,都有可品味咂摸之处,不管存在多少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它们统统说明一条:《红楼梦》是富有魅力的,富有超脱于时间与地域的魅力,正因为有魅力,才会有这么多层出不穷的或深刻或睿智或荒谬或有趣的谈论。黄伟宗发明了“引争力”一词来说明《红楼梦》的这一特色:“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古今文坛上,还没有哪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那样,具有如此持久的引争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引争力”? 黄伟宗的解释是,一是因为它的“先天性不足”,指的是它出世就好像未足月的孩子那样本身有缺陷,比如它未写完,只有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另一作者所续,差异很大;小说版本多,又多有缺失,各版本之间又有差异;甚至连前八十回也有疏漏,尤其是连作者是否为曹雪芹,其出生年月、何时写和怎样写的情况也不能完全确定,后四十回到底是原稿还是谁做的,也不确定。这些不足,原本是坏事,却造成了人们想象和探究的空间,为不同的学说学派提供了驰骋的场域。第二是《红楼梦》超时代的伟大成就。如果不是因为《红楼梦》超越其同时代与具体时代的思想艺术成就,它的“先天性不足”也就无人去理会和探索;而它的思想艺术成就本身也使它成为一个可以无限探究的艺术空间。正是这两方面共同造成了《红楼梦》历三百年至今仍有说不完的话题。这是黄伟宗从总体上解释其“争味”长久存在的原因。
黄伟宗将三百年来红学研究分为五个阶段,从《红楼梦》问世的清朝乾隆年间到五四运动前,是“旧红学”阶段;“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前是“新红学”阶段。当代红学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批判俞平伯到“文革”前为一段;从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为一段;从80年代改革开放到现在,又为一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黄伟宗分为用“谜味”“奇味”“时味”“斗味”“学味”来进行概括。这也是黄伟宗先生的一大特点和长处,他总是能用精准的字眼将事物的特征概括出来,让人过目不忘。而在对每一时期的学派和学人进行评述时,也是富有洞见的。比如对于“索隐派”,黄伟宗并不是一棍子打死,斥其荒唐,而是以慧眼看到其政治索隐出现的原因,他说蔡元培的这些“索隐”,“显然与他当时正在从事的反清革命活动的思想与需要密切相关”,他的那些观点,比如认为《红楼梦》是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只不过因为“文网”而加以数层障幕,“不一定切合作者和作品之原意,视其为蔡元培革命思想和手段体现之一,也未尝不可”。在评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学术贡献时,黄伟宗说它是“以西方哲学美学视野、以全人类的共性胸怀观照《红楼梦》的评论”,既以“人类全体之性质”否定了索隐派的“猜谜倾向”,也对即将兴起的“新红学”的“自叙传”说敲了警钟,指出其“批前诫后”的意义,是新旧红学时代在思想上和方向上的转折界碑,意味着将当时的《红楼梦》研究推向了远超新旧红学的超脱境界,这一见解非常中肯。黄伟宗教授还对鲁迅的红楼梦研究情有独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评说鲁迅对红学的三大贡献:一是对《红楼梦》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和确切的定位;二是划出了新旧时代的区别界线,三是发现和概括了对《红楼梦》评论研究“因人因时而异”的内伸外延现象。鲁迅算不上专门的红学家,但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及一些杂文里对《红楼梦》做过评说。黄伟宗直言不讳地说,在这么多《红楼梦》研究流派里,如要他选一个跟随的话,那就是跟鲁迅,恰如当年孔子说“吾从周”。而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则在评价其贡献的同时指出其不足。他对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不高提出了批评,俞平伯前期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高的”,应该列为“第二等”,新中国建立后虽改为“第一等”,但也在很多方面吹毛求疵。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何其芳在这个领域的建树最大,他的“异峰说”“民主思想说”和“共名说”都值得重视。对于1950-60年代的红学研究,他认为蒋和森的“全民共感说”和“通体说”受到何其芳影响而“青出于蓝”。他甚至提到周扬在1961年谈《红楼梦》的只言片语里有对人性的肯定,比如说林黛玉身上有真的“人性”,贾宝玉是自由思想的代表,他也是“人道主义者”等,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还是令人惊讶的,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在此隐现。而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红学,黄伟宗先生首先肯定俞平伯、李希凡呼唤“学术红学”的先声与实践(这是一对“老对手”,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认为曾扬华等人的研究是“正本清源”,他的《钗黛之辨》是对《红楼梦》下功夫做文本研究的范例,认为周汝昌的红学研究继承胡适的考据实证,有他的功劳,但是将小说本体研究开除在红学研究之外,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他还对刘心武、王蒙等的“作家红学”进行了研究。刘心武的红学被称为“秦学”,主要的进入点是研究秦可卿这个角色,考证出她的原型是谁,虽说有“索隐派”还魂的味道,但包含了大量的考证,黄伟宗肯定他能“自辟蹊径,自成体系,自圆其说”。他将王蒙称之为“现代感悟派”,其特点是感悟性、欣赏性、经验性、开放性、自我性。他认为作家论红学是现当代文学和红学研究中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这一点很有启发性。
总之,读黄伟宗“争味”一篇,可以感觉到三个特点:一是资料掌握较为齐备,评点范围比较广阔,对于重要的研究者几乎没有疏漏。二是评价精简到位。三是对有争议的、热点的问题不回避,有自己的观点,形成一家之言,敢于论断,善于论断。比如关于后四十回续书的问题,对它的好处与不足之处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点评,功在哪里,不足在哪里,一一道来。再如对近年出土的《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的辨析。他从情节的前后矛盾、人物形象的莫名变异、主题的改变、语言的粗俗等方面论证了这个版本是“完全背离历史真实和起码艺术真实的”明显造假之伪书。在另一篇分析“假味”的文章里,黄伟宗否定了《红楼梦》作者是冒辟疆的说法。
三、对话作为形式与方法
黄伟宗先生的《超脱寻味〈红楼梦〉——超脱境界对话录》,从其副标题可见,是一本对话体的研究著作。黄伟宗先生的对话体用得十分彻底,就连“题记”和“后记”都是用对话体的,也就是说自始至终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完成的。对话体在中西方古典时代并不罕见,众所周知,柏拉图的著作基本都是对话体,《论语》《孟子》也是用对话体的形式写成的。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在古代,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够发达,所以使用这种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文体。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柏拉图是有自觉的对话体的文体意识的,他认为表达真理有三种形式:口头谈话、书面写作和模仿口头谈话的对话写作。他认为口头谈话最富魅力,因为对话的双方开诚布公,直接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态度,但因为口头谈话受时空的限制,只能在极少的个体之间进行,要提高哲学的社会效应就只好使用书面文字。相对于那种僵死的、独断的书面文字,他倾向于使用一种模仿对话的文字,这就是对话体。柏拉图的对话体写作非常生动地呈现出对话的情境和说话者的形象,始终把真理的探讨置于问与答的交流中,并向读者发出召唤,因而具有经久的魅力。
黄伟宗先生也是有明确的文体选择意识的。他说之所以选择对话体,一是不喜欢论文体的形式。既然是退休后想做一点轻松的、享受的事了,就想享受任意而谈的乐趣。二是对话体这种形式,适宜于有层次地推进一个问题,直到把它剖析清楚。第三,对话体雅俗共赏。普通读者、《红楼梦》爱好者都可以阅读本书,而不只是在学术圈的狭小范围里被阅读。
本书的对话是虚拟师生对话,即学生提出问题,由老师来作答。问题的设置当然是服务于作者最终想要表达的观点的,某种程度上说,它起到一个托举、引导的作用,实际上是作者思路的一个反映。每一个学者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暗含着一个对话者的,比如你会问自己,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前人已有了怎样的研究? 你还能做的工作是什么? 你准备怎样来探究这个问题? 你所用的材料和所得出的观点与前人有什么不一样,形成怎样的对照? 等等,无时无刻不有一个内在的设问者,黄伟宗先生不过是把这个内在的设问者外化了,变成学生的身份。这个学生一会儿向老师提出问题,一会儿表达赞同或疑惑,推动着对话往前往深处走。因为是回答学生的提问,所以老师回答所用的论述语言就必然比较口语化,深入浅出,层层剥笋似的。而实际上学生的角色是有多重含义的:一方面代表读者可能发生的疑问;另一方面学生也是一个专业的合作者,他依然有一定的专业深度;另一方面,他也是作者的一体二身,是学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自我质询。
我们以“情味篇”看作者如何展开对话的过程。《红楼梦》是一本“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大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见不同的风景。所谓憧味、禅味、恩味、情味、食味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见的不同的风景,而从“情味”的角度看,《红楼梦》直接可以看成一部博大精深的“情书”。对话首先从学生问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一部“情书”谈起,老师的回答从“红豆词”说到《红楼梦》写的七种男女之情,说明它的确是一本“全味”情书。接着又从《红楼梦》的五个书名(除《红楼梦》之外,还有《金陵十二钗》《风月宝鉴》《情僧录》《石头记》)分析《红楼梦》的言情角度和境界,分析它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写情作品的不同以及独特价值。这也是一个很别致的角度,因为每一个名字都不是随意而起的。说到《情僧录》这个书名,黄伟宗先生分析贾宝玉这个沉醉情场的“情种”,的确与任何其他男女恋爱小说的主人公不同,他是只在“意淫”不在“体淫”的,的确是情场中的斋戒和尚。“意淫”即与肉欲无关的痴情,是贾宝玉区别于其他世俗浊男的基本特征:“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是《红楼梦》写情的别一境界。接下来的问答又从贾宝玉经历的“五方情缘”入手,分析他作为“缘主”与五位女子的不同情缘,包括黛玉、宝钗、湘云、晴雯、袭人,分析它们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其中作者把宝黛之情称之为“人性情”——是人的根基上原本有的性灵之情,而把与宝钗的感情称之为“社会情”,与袭人之情也是社会情的一种,因为宝钗和袭人都代表社会规训下的感情关系,但袭人情更为日常世俗。与湘云的“麒麟情”则可以称之为“命运情”,宝玉落难后在湘江偶遇史湘云,而据周汝昌、刘心武的考证,史湘云的原型是曹雪芹的表妹,晚年与曹雪芹一起生活,替雪芹编稿,甚至化身为脂砚斋、畸笏叟进行点评,这不是“命运情”是什么呢? 总之,通过对话层层追问的设计,黄伟宗先生把《红楼梦》写情的特征深入发掘出来,又指出《红楼梦》“起于言情,终于言情,但不止于言情”的超脱境界,完成了对红楼“情”的主题分析。
作为对话体,本书的语言特征是亲切、平易,娓娓道来,问题由浅入深地推进,兼顾普及性和前沿性,对观点的论证不繁琐,有时在对话中也大胆地提出“假说”。比如在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上,黄伟宗从现行版作者由“高鹗续”改成“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谈起,认为这样修改是出于对学术尊重和对读者负责。但他认为这也只是一家之言。他说在乾隆时代文字狱盛行的背景下,“我很怀疑现在张(庆善)先生所说曹雪芹已完成的后四十本是否真正在传抄时丢失? 现印行版本的后四十回是否真是程伟元搜集的无名氏原稿? 是否有可能是高鹗按当时的要求修改,或者重写曹雪芹失去的尚未像前八十回那样‘增删五次’的原稿呢?”意即原稿可能并未丢失,只是高鹗改写了曹雪芹原稿而已。黄伟宗教授并未去证明这一假说,但与众不同的是,他解释了后四十回为什么呈现如此面目。他认为高鹗是以儒家思想改造、中和了禅学思想,所以才呈现这等面貌。既要依原作之走势,不免又要掺入自己的私货,所以忍不住要写“宝玉中举”、再“沐皇恩”“延世泽”“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了,即使是出家做和尚,也是成为“大佛爷”。为什么呢? 后续作家,他们没有曹雪芹那种痛彻肺腑的体验,没有彻底的“空”“净”思想,不管是高鹗还是无名氏,所持的主要是儒家思想,但又限于前八十回作品中有明显的主导思想和故事框架,限制其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必须以折中手段进行,悲剧不能彻底,悲剧时时有想转换为“大团圆”喜剧的冲动。黄伟宗先生不是居高临下地批评,而是从续作者的理念和才华出发去解释后四十回何以呈此等面目,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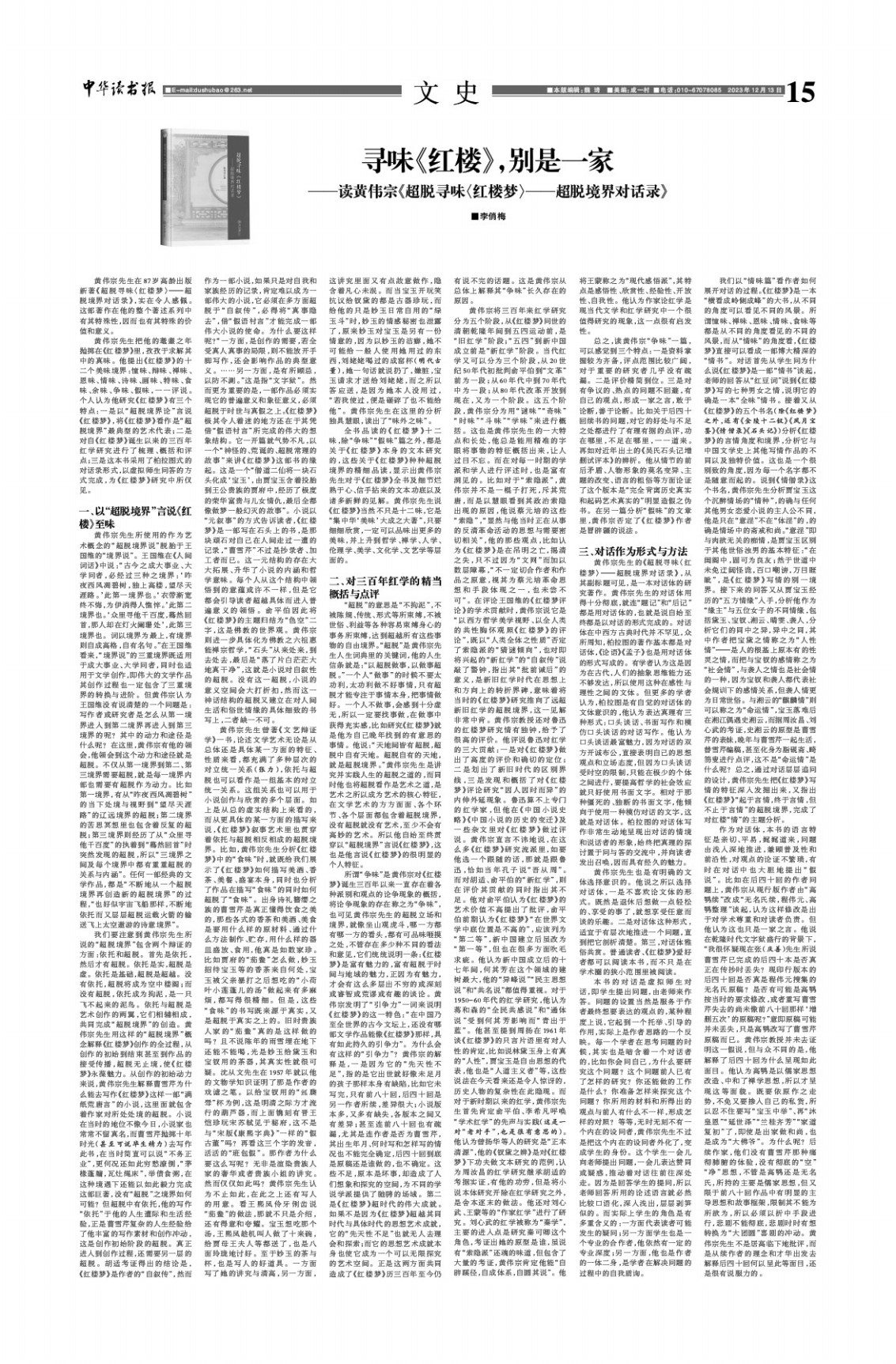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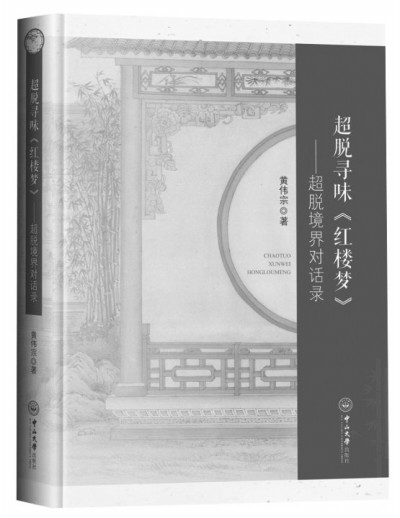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