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地写作可论之处甚多,地名是其中最基础的部分。就中国而论,地之有名始于何时无从考证。作为术语,“地名”最早见于《周礼·夏官·形方氏》:“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据著名人文地理学家陈桥驿考证,中国早期典籍中,“《禹贡》记载的地名约1300处;《山海经》约为《禹贡》的10倍;《汉书·地理志》涉及地名超过4500处;《后汉书·郡国志》超过4000处;《宋书·州郡志》超过2000处;《南齐书·州郡志》超过2000处;《魏书·地形志》超过6000处;《水经注》20000处左右”。古人为地命名,多依地物的一两个主要特征,或以山,或以水,或以植物,或以动物,或以姓氏,或以官职,或以气象,或以色泽等,不一而足。《水经注》总结地名的命名规律:“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
只是小说家写地,可以虚构,亦可据实,或虚实相间。统观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虚构地名者自是大有人在,但据实叙录者更不乏其人。特别是在创作上,存在着普遍的所谓“童年经验”或“乡村经验”。很多小说,篇名即含地名,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古华的《芙蓉镇》,王安忆的《小鲍庄》,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商州》《高老庄》,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等,都是以地名为小说的篇名。
以地名为小说篇名,本是中国小说命名法的一种。旧时的小说,以人为篇名的,有《穆天子传》《汉武故事》《燕丹子》等。以地为名的小说更多,如《海内十洲记》《西京杂记》《酉阳杂俎》《齐东野语》等,都是享有文学史盛名的笔记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本就有极饱满的地学元素。就小说本身而言,地名作为小说的名称,意味着小说某种空间上的限定性,意味着故事将在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空间中展开。小说家们在特定的空间和异空间,即小说地名所呈现出的相对固定的地域社会,与外部更大的时代、社会、历史空间的互动中展开叙事,这是《红楼梦》《水浒传》等的共同特点。
当代小说亦不乏其例,《芙蓉镇》《高老庄》《白鹿原》《天漏邑》《凤凰台》《圣天门口》《敦煌本纪》等都较为典型。如古华的《芙蓉镇》,作为一部反思小说,作品开篇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览风物”,写镇子旧时的繁华:
芙蓉镇街面虽小,居民不多,可是一到逢圩日子就是个万人集市。
三省十八县,汉家客商,瑶家猎户、药匠,壮家小贩,都在这里云集贸易。猪行牛市,蔬菜果品,香菇木耳,懒蛇活猴,海参洋布,日用百货,饮食小摊……满圩满街人成河,嗡嗡嘤嘤,万头攒动。
小说中的芙蓉镇以何镇为蓝本,究竟是作家古华故乡嘉禾县的唐村镇,还是湘西永顺县的王村(谢晋电影《芙蓉镇》拍摄地,现已改名为芙蓉镇)? 不得而知。但是古华以“芙蓉镇”名之,且写到芙蓉河、河岸的木芙蓉树、“芙蓉姐子”等,“芙蓉”显然是一种别有深意、别有意涵的预设。《本草纲目》有“木芙蓉”条目。“木芙蓉”释名“地芙蓉”,气味“微辛,平,无毒”,“清肺凉血,散热解毒,治一切大小痈疽肿毒恶疮”。小说中芙蓉镇之芙蓉,有没有特别的含义,此处不便作强解。
《芙蓉镇》是借名,借“芙蓉”之名,强化小说的批判功能。相比较而言,贾平凹的《高老庄》则是另一种借名。小说取境《西游记》中“高老庄”,借用猪八戒在高老庄娶亲,酒后现出猪妖原形的故事,“假道于山川,不化而应化”,以比附《高老庄》的主旨。《高老庄》写的同样是现形的故事,只不过现形的不再是猪八戒,而是大学教授高子路。原本子路应该像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样,勇武而刚直,辨别是非,行仁义,但《高老庄》中的子路,却一心要洗脱农家子弟的身份和趣味。为父亲去世做三周年祭,他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时,那些潜存在高老庄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如封闭、狭隘、自私、小气、粗鄙等一一再现。贾平凹借道于《西游记》中的“高老庄”,表达的其实是对乡土文明中人的精神退化的精深思考。
和《芙蓉镇》《高老庄》的借名相比,赵本夫的《天漏邑》更有哲学的、人类学的复杂气象。此作颇有《红楼梦》的味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小说中,两条线索交叉轮替,作家一边以田野调查的方式,以简笔写出天漏村的亘古、蛮荒、偏僻、神秘的历史,另以繁笔写出天漏村人的天性与人性。天漏村是个与世隔绝的所在。世间传说,天漏村是远古遗民的部落,古舒鸠国的都邑,历朝囚徒的流放之地,天象诡异,时有雷电伤人之事发生,人也诡异,沿袭着古老的法则。《天漏邑》的故事极为复杂、情节奇特,但究其宗旨,写的不外是人的罪性与恶性。天有“漏”,故有女娲补天之说,但天之“漏”又岂可尽补? 哪里会有无“漏”之天呢?“漏”,是事物的本质。于事和物而言,是亏欠、欠缺;于人而言,则是德性有亏。
对小说家来说,地和地名可以利用之处很多。地,不单提供小说故事情节展开和人物活动需要的物理空间,地名更是以其不可替代的地方性地理文化特质,构成小说家的标识。特别是在中国,内部为高山、江河所分割,形成很多大小不一的文明体,各地地形、地貌、植被、土壤、气候殊异,历史、语言、生活、礼俗、人情相远,地理特征和地名的命名机制相差很大,所以,区域性的地名系统,无论虚与实,多会构成各地独特的地名景观。如汪曾祺,居于高邮地区,地处江淮之间,中间有运河相连,湖泊星罗棋布,他的小说的地理景观,就难免会有“水”的韵味和智慧。如《大淖记事》: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
大淖、河源、沙洲等地名系统,和茅草、芦荻、蒌蒿等植被,呈现出鲜明的河湖湿地特色。生于斯,长于斯,汪曾祺即便写其他地方,也离不开诸如此类的地名系统,如《故里杂记》写“后街”:
侉奶奶住在一个巷子的外面。这巷口有一座门,大概就是所谓里门。出里门,有一条砖铺的街,伸向越塘,转过螺蛳坝,奔臭河边,是所谓后街。
街区的尽头,还是越塘、臭水河、螺蛳坝等。这类地名系统,是汪曾祺小说中颇具地方特色的地理景观,在《辜家豆腐店的女儿》《黄开榜的一家》《昙花、鹤、鬼火》《故里杂记》等小说中,这些地名反复出现。水系地名景观,给汪曾祺的小说带来盎然的生机和无尽的韵致。“自然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水无定法,亦无形法,故以万物为形法,所以,汪曾祺的小说,总是有任性、任情而不拘礼法和敢于突破世俗陈规的力量。最典型的就是《受戒》,菩提庵成了“荸荠庵”,荸荠庵便是菩提庵,“庵里没有清规,连这两个字都没有”,“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无分别,无善恶、无是非,世俗与佛法泯然为一,确乎是达到众生平等、万法为一的大境界。汪曾祺小说的地名景观,承载着高邮人的记忆,东大街、泰山桥、竺家巷等,无一不带着高邮的地方特色。
汪曾祺小说中的地名多有出处,大多能够在《高邮县志》和《江苏省高邮县地名录》等典籍中得到求证,相比较而言,贾平凹对地名的运用,则有更多的主观创造性。他的小说地名之多、类型之丰富、命名之讲究,实为当代作家中所罕见。如《秦腔》——街景有清风街、秦镜楼、魁星阁,乡镇有西山湾、天竺乡、竹林关镇,地名有三角地、七里沟,山景名有虎头崖、屹甲岭、伏牛梁等,涉及的地名有数十个。特别是近些年,贾平凹的兴趣转向了写秦岭的地方生活和其中的人事,写秦岭的山石、草木、鸟兽,连续创作出《山本》《老生》《秦岭记》三部长篇小说,其中涉及的地名更为丰富。比如《老生》,作品中的地名系统就几乎涉及秦岭山地环境中的所有地学类型。
自然地理形态上,小说写到的有河、川、山、崖、梁、坪、屿、砬、砭等;社会和人文地理形态上,小说写到了村、镇、街、观、寨、驿、寺等。这些地名,有的因为地的形状而得名;有的因为物产而得名;有的因为姓氏和人物得名;有的因史迹、神话传说得名;还有因为方位而得名。这些地名有实有虚,毫无疑问,写作这部小说,贾平凹肯定动用了大量地方志资源。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地名作为小说的叙事构成时,对《老生》这部小说的成形及其主旨的深化实有莫大的帮助。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地名,构造出一个具象的秦岭,特别是像梁、坪、屿、砬、砭、寨、驿之类,带有明显北方、山区和黄土高原特色的地名的反复出现,对秦岭的自然、人文、历史地理景观建构起到重要的支撑性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地名连缀起的移动空间,构成了《老生》的整个叙事空间。
这种微观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名所连缀的叙事空间,使得整部书情节紧凑,叙事富有跳跃性,没有丝毫的沉闷。小说因了秦岭的体势和形法,而有了某种跳跃的、晦暗不明但又纵横吞吐的气象。贾平凹因为擅用秦岭的地名和山川形势,因此让《老生》窥得天地之理,进而有了生生不息的气机。
(本文摘自《地方志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周保欣著,标题为编者所拟,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第一版,定价:88.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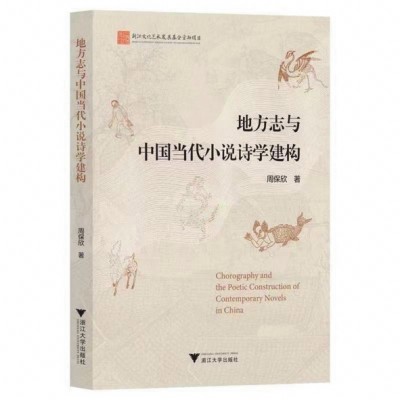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