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意大利导演罗伯托·贝尼尼执导的电影《美丽人生》——哪怕一个人失去了自由,也可以拥有做梦的权力——王延辉为他亲历的1970年代写出了一个梦幻般的彩色故事,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荒唐透顶的岁月,花儿还是要开放,小豹子还是要成长,芭蕾少年还是要把“阿拉塞贡”跳出“味儿”来。
即便作者声称《舞蹈的少年》“绝非自传性写作”,但是小说中“涉及本人职业经历,还有真名实地的具体描述”,至少可以说明这个故事来源于第一手的“生活素材”,作家之所以要“将以往的素材重新写一次”,无非是想通过五十年后的再回首重建少时记忆,给曾经被“写坏了”的青春争得一个洗尽铅华的机会。在小说中,作者让舞蹈复归于舞蹈,让少年复归于少年,回到常态常情中写中了一个属于那个“非常时空”的常人常事。
小说的故事空间主要集中于歌舞团。这样一个势单力薄的小单位虽然也会受到大环境、大趋势的冲击和影响,但是由于歌舞团的专业性很强、行政级别较高,反让它像远离尘嚣的伊甸园一般,成了一个封闭而又相对独立的小世界。发生在这个小世界的故事,当然也就具备了超出凡俗的独特性,这里的“常人常事”亦因他们所拥有的独特空间而“‘情况’真的‘特殊’”起来。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帮未成年人组成的芭蕾舞培训队。本来歌舞团就已经相当非主流了,老是和脚尖过不去的芭蕾舞更是一种至今也和大众生活极为隔膜的洋玩意儿,再加上它的二十来个队员又都是十四五岁的男孩女孩,他们在不知“巴黎”舞为何物的前提下凑到一起,至于会惹出什么乱子,闹出什么笑话,似乎都是发生伊甸园的天真游戏。这些孩子几乎无一例外都面临成长的烦恼以及来自成人世界的“规训与惩罚”,但是他们又像《美丽人生》中的小男孩一样,总是可以令“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他们因其骨弱筋柔、懵懂单纯而有惊无险,或者化险为夷。
作为小说核心人物的“小豹子”恰恰又是一个丧失“主角光环”的不完美主角。当他停止长个儿时,原本天生“最符合舞者标准”的幸运儿无疑成了命运的弃儿,好像忽然间就没了优势,没了“前途”,他也如同折翼天使,不得不告别伊甸园,告别自己的天真年代,走向封闭空间外的大世界,走向可以尽情奔跑的无边原野,找到让骨骼关节“咔咔作响”的新生之地。这个“不完美主角”最终渡过了由成“角”到成“人”的成长周期,完成了精神上的拔节。
此外还要注意到,“伊甸园”实际掌控者,并不是压倒一切的“上帝”,而是以向队长、闻老师、祖老师等舞蹈团公职人员为代表的成年人。这三人一个是跳秧歌出身的,一个是来自北京的专业芭蕾舞演员,一个则是相对刻板教条的文化课老师,他们作为培训队的权威主导者,对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专业修养和思想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并没有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刻意强化师生间的矛盾冲突,即使热衷于“政治挂帅”的“祖奶奶”,也没有黑化得一无是处。所以小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写活了一批向光而生的孩子,还体恤地写出成年人的烦恼、局限和温厚、豁达,舞蹈团有可能只是阴差阳错的放逐之地,但是他们依然兢兢业业地对待好每一天,把对芭蕾、对艺术的爱毫无保留地倾注给一群“舞蹈的少年”,为他们擦亮了头顶的四角天空。
难能可贵的是,故事的高潮在于,那段“艰难时世”仿佛到了尽头,孩子们最终冲破“伊甸园”,走出省城,来到了胶东乡下,见识了民间舞者的精彩表演。他们不仅发现原本与“芭蕾”格格不入的向队长竟是大显身手的“舞神”,更从那些“惊为天人”的民间艺人身上领略到了那种只有在那样的野地里才会有的“风刮不去、雪压不住、一敞开了咕嘟咕嘟往外冒的‘味儿’”。这是芭蕾与秧歌的相遇,也是“洋”与“土”的对话;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相互发现,也是“文”与“野”的深度交融。借着民间艺人激扬奔放的舞姿,走出“伊甸园”的孩子们来到了和大地相连的“场子”中间,与激发天性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在茫茫旷野中找到了个人的位置。大概,这也是作者所谓“花开在眼前”的美好寓意。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在长篇小说《权力与荣耀》中写过一段话:“生活中怪事很多,人们发现,不论日子多么不好过,总有某些瞬间你还是感到活得很开心,总可以同更倒霉的时刻做比较。即使在艰难险阻中,钟摆也依然来回摇摆。”——《舞蹈的少年》也让我们听到了钟摆的声音。的确,每一朵花都需要自在开放,每个少年都需要美丽人生,哪怕天灾人祸,无论世事多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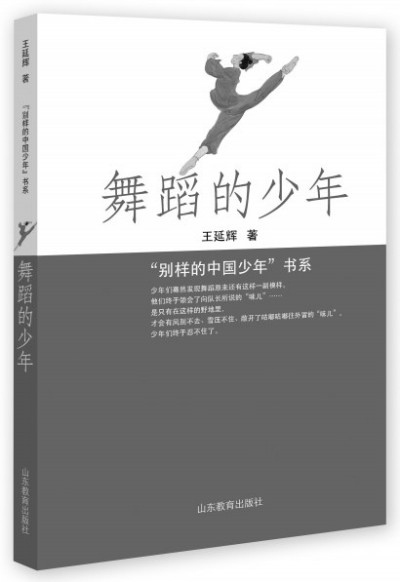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