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都在企盼遇见施家彰这样的诗人:他拥有中国唐代诗人那样的厚重,日本禅宗大师那样的潇洒,而发出的声音又是全然当代的。他擅长对自然世界的描述,包括他在其间生活多年的美国中西部景观。他的诗低调谦逊地涉及自己广泛的旅行以及从中吸取的不同文化经验,也包含美国本土经验,却恍若置身事外。”如果要用一段话来概括美籍华裔诗人施家彰(Arthur Sze)诗歌创作的特质,美国诗人、普利策诗歌奖得主卡罗琳·凯泽(Carolyn Kizer)的这段话应该是最恰当不过了。
1950年,施家彰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华裔家庭,20世纪70年代移居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圣塔菲,至今在那里生活、写作。原本是麻省理工理科生的他,因为在大学时代参加了美国诗人丹妮丝·勒沃托夫(Denise Levertov)的诗歌工作坊,遂决定弃理从文,赴加州伯克利修习诗学和中国古典文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他诗歌中呈现出的多元和丰富显示出了其背后深厚的中西文化传统之于其创作的深刻影响。2023年5月,精选其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施家彰的首本中译本诗集《玻璃星座》(The Glass Constellation:New and Collected Poems)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出版。在出版方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施家彰作为一个华裔诗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成为与会嘉宾的谈论焦点。
翻译家高兴说:“读他的诗我感觉到了一种丰富性、一种复杂性。另外,我又有一种十分的亲切感,因为施家彰先生诗集中处处可以看到中国的影子。”在评论家唐晓渡看来,施家彰诗中的身世感也许不那么强烈,但其开放的广阔性,他作为“文化中间人”所体现的对不同文化要素的持续综合,却不妨说在另一向度上体现了当代汉语诗歌所可能达到的标高。尽管视野的开阔,阅历的广阔,以及对具体的重视,在使施加彰的诗极富博物学特质的同时,也使其诗中的文化构成显得极为多元博杂,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中辨认出中国传统文化和诗歌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它的整个运思方式,说得大点,他的世界观。他的诗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血脉相通的。
“虽然他的诗歌从整体上还是一种欧美诗歌的传统,但是不可否认作为一个华裔诗人,在整体风貌的呈现上,他还是有那种东方诗学、东方诗歌对自然对生命的哲学性理解。”诗人吉狄马加如是评价。
听着来自中国这些同道和朋友们的评论和赞誉,端坐于其间的施家彰会偶尔从座椅上稍稍立直一些,以他几乎不动声色的点头和微笑谦逊地表示回应。而他清瘦的身形和面庞,一头梳向脑后的微卷的灰白头发,忧郁的眼神里有通向诗歌世界的深邃,那里广大又精微,抽象又具体,万物流转,道通为一。
近日,本报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了远在美国的施家彰先生。
“我迫切地想让全世界都能领略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
中华读书报:您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学的是理科,但后来被诗歌的魅力吸引,转而研习诗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做出这样的选择? 能否谈谈您早年的中文阅读?
施家彰:在麻省理工的第一学期,我坐在大讲堂里看着教授在白板上写微积分方程式。偶然间,我转向笔记本的背面,写下一些诗句。那时我并没有计划,但回想起来,可以说我当时产生了一种直觉:尽管我擅长数学和理科,但若继续走这条路,我可能会过上一种绝望的生活,就像美国自然作家(nature writer)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所写的那样:“多数人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Most men lead 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我摒弃了理科学习而开始写诗,这个彻底转变是出乎预料的——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燃烧。一旦发生,我的人生就永远地改变了。
后来,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诗歌学习。作为一个美籍华裔,我希望能更深入地挖掘中华传统。当我研究汉语言并开始逐字逐句读唐诗时,我逐渐爱上了它们;但当我阅读中文诗歌的英译本时,我发现它们令人失望,甚至令人心烦意乱。许多翻译的语调听起来很生硬,甚至有点过时;语言也显得僵硬而牵强。所以,我开始翻译,并怀揣着双重目标:作为一个年轻诗人,我希望能作出清新而精当的翻译,同时通过翻译来提升自己的诗歌创作技艺。
中华读书报:是的。您曾多次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并在自己的翻译诗集《丝龙》(The Silk Dragon: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Port Townsend,WA.Copper Canyon Press,2001)中收录了陶渊明、王
维、李白、杜甫等众多中国古典诗人的作品。诗歌评论家王家新认为您是“继庞德之后,再次将中国古典诗歌带到世界的人”,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施家彰:王家新过誉了,我愧不敢当。在将这些杰出的诗歌译为英文时,我竭尽所能。我知道翻译是一项不可能完美的工作,但尝试是有必要的! 中国古典诗歌为世界贡献了如此之多,它有卓越的洞察力、情感力量、富于想象的语言能力、对自然的敬畏。这许多的方面,都让我迫切地想让全世界都能领略这些诗歌的魅力。它们提供了一条体悟和敬畏对他者与众生的路径,我们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精神。每翻译一首诗,我都在努力为此作出贡献。
中华读书报:1915年,庞德(Ezra Pound)根据美国东方学专家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关于中国诗的笔记整理、编译而成的《华夏集》(Cathay)在伦敦出版。其中涉及战乱风云以及离愁哀怨等主题,与现代西方读者产生了心灵共鸣,因此深受欢迎且广为传播。请问您在翻译中国古诗时选取的标准是什么? 它们的接受情况如何? 在您看来,与上世纪初相比,今天的西方读者对中国古诗的阅读反映了哪些时代的变化,以及这些时代环境的不同又如何影响了读者的阅读选择和接受?
施家彰:作为一个译者,我的翻译进行得很缓慢。我的选取标准是只翻译我爱的诗歌。因为我的中文水平有限,所以每次只能读几个字,而且要借助字典、咨询那些中文流利的人。我读诗,与诗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所有的诗歌中,我逐渐对其中的一些失去了兴趣;那些浅薄的诗歌或许会有一瞬的闪光,但其影响力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减弱。然而,还有一些诗歌让我立刻意识到我并未完全理解它们,甚至为之感到困惑——我想到了李商隐那样的诗人——但它们让我体会到了深刻的惊奇、韵律与魔力,在我的大脑理解它们之前,它们便与我的身体相通——此类诗歌深得我心,它们就是我会最终选定的、我爱的诗歌。接着,我用自己笨拙的、生硬的字迹,一笔一画地把诗歌逐字誊写出来,由此,我不仅从外表上读诗,更从内部感悟其创作过程。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将诗歌个性化的体验,然后我就可以开始翻译它们了。
我的翻译在美国读者中反响极好,而且他们渴望读到更多。我正在准备推出我的中国诗歌翻译集的增订版——《丝龙II》(The Silk Dragon II),它预计于2024年5月由铜峡谷出版社(Copper Canyon Press)出版。虽然我已经独立写诗和定期英译中国诗歌长达50年之久,但我只有75首译作。在这部新的翻译集中,我又增添了一些古典绝句(classical quatrains),以及一些来自西川、翟永明、王小妮、王家新、严力、姜涛等人的现代诗歌,他们都是我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国际诗歌节上结识的诗人。然而,我还是想再次强调,在数十年的积累后,我仍只有75首译作。在美国,有编辑和出版商曾表示希望能大批量地发行我的作品,但我无法以那种方式工作。在同
一段时间内,别的译者或许可以出版一千页译作,而我只能译出75首来,但至少我忠于其中的每一篇。
西方读者现今对中国古代诗歌的阅读比早期更加宽泛和精深,但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庞德(Ezra Pound)在《华夏集》(Cathay)中英译了17首中国古诗,震惊了西方读者,让他们爱上了中国古诗。可以说,《华夏集》(Cathay)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文诗集,没有之一,而它竟然只包含了17首诗! 久而久之,通过众多的翻译,西方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但对于很多诗人的作品仍缺乏了解,他们对中国古诗的理解也亟待加深。我一有机会,就会极力推荐法国汉学家程抱一(François Cheng)的中国诗歌导论——《中国诗歌语言研究》(Chinese Poetic Writ⁃ing,其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译者涂卫群),这是其法文原版的英译本。在这部导论中,程抱一为西方读者解读了诗歌中的特定汉字,展示了其中无法被翻译出来的东西,并将中国诗歌与绘画、音乐、书法相联系。他对中国诗歌的解读深受符号学方法的影响,因而具有某种时代特征,呈现出当时的文学批评潮流,这一影响如今已被吞并和削弱了。
如今,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无疑影响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偏好与接受程度。在西方,许多读者怀着浓厚的兴趣探寻文学作品对当前气候危机的回应。这在美国诗歌领域迅速形成了一股蓬勃发展的潮流,叫“生态诗歌和生态诗学”(ecopoetry and ecopoetics),它与许多散文和自然作家(na⁃ture writers)甚至是科学家相关,他们共同呼吁关注我们时代的这一紧迫问题。
“以诗歌创作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复杂与挑战”
中华读书报: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国诗歌在哪些方面能为西方诗歌带来补益的资源?
施家彰:中国诗歌是一种无价的宝贵资源,能无穷无尽地丰富西方诗歌。如果西方读者有机会深入阅读和体验中国诗歌,那他们就可以开始理解中国诗歌的“现在时”(present tense)了。所谓“现在时”指的是即时性(immediacy)、敏锐的关切(keen attention)、想象和情感的力量(imag⁃inative and emotional power)、紧凑性(compression)、一语多关的层次感(layer⁃ing of simultaneous meanings)、并置式隐喻(metaphors accomplished through juxta⁃positions)、生成性沉默(generative silence)、抒情之美(lyrical grace)——这些都是中国诗歌的本质特征,它们被清晰地表达出来。
中华读书报:您的诗歌中,无论是构思、意象,还是哲思,无一不体现着中国古典诗歌对您的影响。但作为一位美籍华裔诗人,您在美国出生成长,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熏
陶,请问您在创作时如何平衡和处理中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您如何看待中国古典诗歌在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施家彰:作为一名美籍华裔诗人,我同时从中西方两种传统的文学、哲学和文化中汲取资源,并试着通过我个人的声音与视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诗歌,以应对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所面临的复杂与挑战。如果有中国读者读我的诗,他可能会很快发现我借鉴了《易经》《天问》《庄子》等许多古典文献资源并与它们对话。但作为一个用英文写作的诗人,我不会受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担所捆绑和困扰。这一点很关键,我自如地吸取、转化和创造。中国古典诗歌的长河宽广而深邃地奔涌在我的诗歌里,但它绝非唯一之源。在美国文学谱系中,我借鉴了惠特曼(Walt Whitman)、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和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这些美国作家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毕竟我是一个用英文写作的美国诗人。由于在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的圣菲生活了50年,我也受到了说西班牙语的美洲土著人社区的熏陶。我还吸取了聂鲁达(Pablo Neruda)、霍皮语语言学(Hopi lin⁃guistics)、普韦布洛礼仪(Pueblo ceremo⁃nies),以及叶芝(Yeats)、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资源来丰富我的诗歌。
在我的创作努力中,中国古典诗歌的意义与作用一直在变化。起初,我研读唐诗,但后来觉得也有必要去研究其他时代的诗人。唐诗的古典美(classical beauty)有一种束缚感,而就我自己作为诗人的成长历程而言,我希望能在我的诗歌中融入越来越多当代世界的元素。我需要颠覆传统、挣脱束缚,并能在诗歌中表达至暗之暗与至明之明,要能驾驭“电子”(electron)、“钚”(plutonium)和土著美洲人的编织技艺构造(the structures of Native American weaving)等当代元素。中国古典诗歌是我永远的灵感之源,但我不能被其束缚。就像庞德(Ezra Pound)所说的“常新”(Make it new)那样,每一代诗人都需要创新。
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中对不同文化资源的汲取,以及您对美国社会生活的观察,各种建筑、风物、山川、河流乃至动植物都成为您诗歌中的主角。您从这些细微的事物上升到宏阔的抽象思考,呈现出现实经验的复杂性和独特的风格魅力。这种风格的形成,除了多种语言、文化的影响之外,应该还蕴含着您个人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能否就这个问题展开谈谈?
施家彰:感谢您对我诗歌的反馈。我需要说明,作为诗人,我走过的道路漫长而艰辛,我诗歌中的复杂性在逐渐演化发展,这得益于我的个人经历。我住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菲,这是一个独特的城市,因其高海拔沙漠景观及其对艺术的推崇而闻名。尽管这里的人口只有十万人左右,但很多创作者选择居住在这里。20世纪80年代初,我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盖尔曼(Murray Gell-Mann)成为朋友,我们的交谈涉及粒子物理学、空间、时间、物质和弦理论,这些讨论对我来说很重要,并成了我的灵感之源。后来,我跟随自然主义者艾萨克(Bill Isaacs)学习,他教授一门蘑菇鉴别的课程。一连五个夏天的周末,我都在山里采蘑菇,学会了如何甄别可食用蘑菇和毒蘑菇。我在美国印第安艺术学院(Institute of Amer⁃ican Indian Arts)任教的22年里,曾与来自美国各地两百多个部落的大学生合作,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土著语言和文化。在进入这所大学之前,我曾受到一个国家项目的邀请,以诗人身份在新墨西哥州和阿拉斯加州的一些初高中工作了十年。在印第安居留地和说西班牙语的初高中,我应付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状况。在阿拉斯加,我乘坐水上飞机来到一个偏远的岛屿,在那里,捕三文鱼的渔夫住在随潮汐而起落的浮屋上。我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星期,以诗人的身份激发青年学生写诗的灵感。还有一次,我在安克雷奇的公立学校工作,那里的气温从未高于零下29摄氏度。然而,到了晚上,在绿色和紫色的夜幕中,极光闪耀在整个北极圈的天空。我诗歌中的许多意象都来自生活经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诗歌中,都要永葆好奇、持续成长、甘于冒险。
“中国当代诗人的国际视野和对多种传统
诗歌的敏锐理解令人
印象深刻”
中华读书报:前不久,您在中国出版了诗集《玻璃星座》。在成都和北京的几场新书研讨会上,您谈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读者一种看待世界的全新眼光。具体来说,您希望中国读者能从中获得哪些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施家彰:我知道我的诗不易读懂:它们需要被从头到尾地反复阅读、品味和深
思。然而,我希望我的诗歌能一次又一次地吸引读者,因为其中会不断浮现出令人惊奇和心动的东西。尽管诗歌中所描述和表现的事件极其阴暗——但我相信,真正的诗歌永远不会过于阴暗——我还是希望读者能够意识到,阅读我的诗歌是充满惊奇与愉悦的体验,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丰沛的活力回归生活。
中华读书报:这些年来,您来中国参加过多次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之类的活动,另外,在国外的类似诗歌活动中,您和国内新诗领域的评论家及诗人们也有很多交流。请问您对当代中国新诗有何印象和感受? 中西方诗歌发展现状有哪些异同? 它们背后的深层文化差异是什么?
施家彰:中国当代新诗有其多样性和生命力,许多杰出的诗人持续发展和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作为局外人,我对中国诗人当前展现出的国际视野和对多种传统诗歌的敏锐理解印象深刻。我相信,俄文诗和德文诗——我想到了阿赫玛托娃(Akhmatova)、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茨维塔耶娃(Tsvetaeva)、策兰(Cel⁃an),他们的一些作品被王家新翻译成了中文——对中国当代新诗演进的影响比它们对美国诗歌发展的影响更大。有趣的是,法文诗——我想到了树才对法文诗的中译本——对中国和美国诗歌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还认为,中国现代诗人最初转向西方寻找灵感,而在摆脱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束缚而独立出来之后,他们现在已经能够从这些古典源泉中汲取养分并不为之所累。当然,每一代诗人都需要创造出一种诗歌来有力地与时代对话。正如西川所论证的那样,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鸿沟,同中文与外文之间的鸿沟一样宽广。
在美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中,我想到的是,在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等地开展的实验和不同艺术学科间的合作,对许多美国诗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不知道在中国当代诗歌与诗学的演进中是否有类似的情况。此外,稍晚一些,斯奈德(Gary Snyder)摘选了寒山的诗歌并英译,但他将寒山塑造为反美国物质主义(Ameri⁃can materialism)的、反正统文化(coun⁃ter-culture)的人物,我不确定在中国当代诗歌的演进中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另外,美国诗人受到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发展出所谓的“深度意象”(deep image)诗歌,这与中国诗歌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美国当代诗人赖特(James Wright)受白居易的启发写下一首美丽的诗歌,而许久之后,默温(W.S. Merwin)又以书信形式写下了一首给苏东坡的诗歌。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整个美国诗歌领域。
然而,这些诗歌运动和流派的标签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尽管有时划分诗歌运动和流派可以展现主流趋势,但诗人毕竟不是为了成为某个诗派的一员而写作的。那么,把中国诗人分为第一代、朦胧诗、后朦胧诗这几类,这样做好不好呢? 作为一个中国诗歌的译者,我并不关心某个诗人究竟归属于哪个诗歌运动或流派;我只寻找那些具有惊人独创性的诗歌,诗人在其中全身心地投入了激情与活力。正如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曾说的,我无法定义诗歌,但如果它让我感到“我的天灵盖好像被揭开了”(takes the top of my head off),那我便能知道它是诗歌。
从广义上讲,我认为中国诗歌和美国诗歌的演进问题是比较研究的一个范例。二者相互启发,而且我希望它们能继续彼此激发灵感。尽管中西方有着深刻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但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可以通过密切的对话,继续相互启发和挑战、促进彼此的成长。在我看来,这种互动不是在大规模的公开活动和平台上发生的,而是沿着空白的边缘地带逐渐进行的,就像我逐首逐首地翻译那样,诗人与诗人也应该一对一地直接相互交流。
(本采访稿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简佳星翻译,特此致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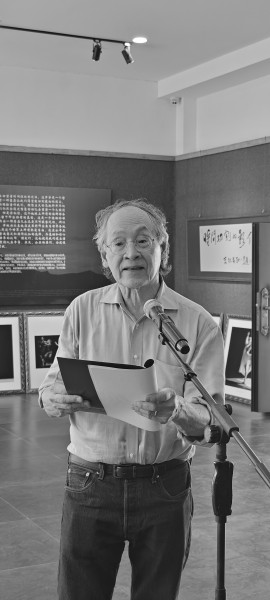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