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秋,上海博古斋拍卖公司恢复线下拍卖,在新文学版本的“万象专场”上,爆出了冷门,一册民国版诗集,非郭沫若、徐志摩等名家签名本,从一千元起拍,一路上扬,后以五千元的加价幅度递增,拍出了六位数的高价,最后定格在十六万元,加上百分之十五的佣金,总计十八万四千元。这让在场的众多买家眼睛一亮,大大超出了拍前预期,创出了新文学诗歌版本的拍卖记录。
这是邵洵美的精装本《花一般的罪恶》。拍卖前的预展上,我小心地翻阅过此书,触手如新,可谓十品。我当日写下小文《新文学收藏正当其时》,文中说:“我在研究新诗史料中,知道邵有此诗集,但这是第一次见到版本真容,很有点震撼的感觉。不禁感叹:太珍贵了! 不说书的内容,就是封面装帧,就够精致的。布面精装,书名和作者,压型烫金,下面配一朵大大的金色之花。这是金屋书店一九二八年的出版物,这家书店是邵自己开的,他在自家书店印诗集,如同今天的自印本,可能只做几百本,送送小圈子内的爱诗朋友而已(此书还有平装本,那是售卖给普通读者的普及本)。邵是唯美主义诗人,他的诗集,就体现出唯美的理念。这样的装帧,过了近百年,不但不落伍,反而更亮眼更珍稀”。由于时间的消蚀,原本黄色的烫金封面已然暗淡,显出了些许旧气,色泽沉郁,略呈银白色。
第一次知道邵洵美的名字,还是听忘年交章克标老先生说起的。章老晚年定居上海,我常拜访他,听他聊天。内容天南海北,却都是文坛轶事。谈起邵洵美,他淡淡地说:“很早就一起做同事了。”
章克标早年留学日本时,就与滕固、方光焘、张水淇几人商量过成立文学社之事。一九二四年他们先后回国,章克标就跟着滕固编《狮吼》半月刊。不料这本唯美派的同人杂志,竟有不错的销路,还远销海外至新加坡等。正巧邵洵美从法国巴黎回国,途经新加坡,在码头一侧看到书报摊上的《狮吼》杂志,买了一份带到船上竟看得如痴如醉。船到上海,他就迫不及待地按刊物上的地址,找到了滕固、章克标等人,大家一见如故,尤其是邵洵美与滕固,都出身书香门第,在文学趣味上又有许多共同语言,成为知己之交。邵洵美很快融入到“狮吼社”这样一个文学社团中。这批文学青年在上海聚集,是因为他们不满社会的虚伪、强权的环境,要发泄内心的郁闷情绪,要发出醒世的“狮吼”之声。他们的作品,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是对传统封建道德的反叛,对才子佳人般鸳蝴派的挑战。由于邵洵美的加盟,后期狮吼社有了一段辉煌的鼎盛期。《狮吼》得以恢复出刊,并出版狮吼社丛书,以及滕固、章克标等人的文集。
一九二九年狮吼社活动渐少,邵洵美另办了金屋书店,并让章克标与他一起主编《金屋》月刊。地址先在南京路、福建路一带,后搬入离邵家较近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青海路)同和里。但这个地方不太适合开书店,邵洵美就把书店迁往四马路(今福州路)望平街。据章克标回忆,金屋书店虽只有一开间门面,邵洵美却把它设计装修得十分考究,沿马路一边是大大玻璃橱窗,可对外陈列各色精美图书。店牌是黑底金字,看上去既金碧辉煌,又高雅大气,充分体现了邵洵美的审美情趣。
这就说到了诗集《花一般的罪恶》。既然邵洵美的书店、刊物及店招都用了金字,说明他喜欢金色。这本只有五十五页的诗集,就是金屋书店的出版物,在墨绿色的封底上,书名、作者名及用以装饰的一朵大金花(六瓣大叶加三瓣小叶),都用了烫金压模,呈凹凸型,有很舒适的手感及视觉感。这样的装帧设计,已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唯美主义风格。接着,邵洵美把版权页上应有的出版机构(金屋书店)、出版时间(十七年),移到扉页的书名下,而后面的版权页上,只写“五月五日初版”、定价及“版权所有”四字。
邵洵美祖籍浙江余姚,但祖上几代已定居上海,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外公是赫赫有名的盛宣怀。邵洵美就读的“南洋路矿学校”(交通大学前身)就是盛宣怀创办的。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不但结识了徐志摩、张道藩、刘海粟等文艺同好,还喜欢上了外国诗歌,如希腊女诗人莎茀,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魏尔兰等,曾到巴黎法国画院学习绘画。赵景深曾形容邵洵美“面白鼻高,希腊典型的美男子”,诗评家周良沛说,“他的唯美,似乎是荣华富贵之享乐的存在所决定的”。从物质到精神,都与邵洵美唯美主义的艺术情趣契合。从他自己金屋书店印制的《花一般的罪恶》就可以看出,他的出版社出书,不但内容要好,还要以别致的装帧、精美的设计、豪华的印制,成为“唯美”艺术品。
这本薄薄的诗集,共刊诗三十一首。因为在此之前一年,邵洵美出版过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列“狮吼社丛书”之一,分两编共三十三首诗。在编《花一般的罪恶》时,他把那本诗集中较满意的十几首诗,如《恋歌》《来吧》《情诗》《五月》《爱的叮嘱》等,直接移了过来,有的改一下诗题,也一起编入《花一般的罪恶》。书名取自诗集的最后一首诗,但读者一看就明白,这是从波特莱尔的《不吉祥的花》(即《恶之花》)移植过来的。所以说,《花一般的罪恶》中有近半作品不是新作而是重编。看《来吧》中的诗句:“啊你我的永久的爱/像是云浪暂时寄居在天海/啊来吧你来吧来吧/快像眼泪般的雨向我飞来”。再看《上海的灵魂》:“上面是不可攀登的天庭/下面是汽车,电线,跑马厅/啊,这些便是都会的精神/啊,这些便是上海的灵魂”。这些语句,这些意象,是邵洵美特有的。
此书出版后,引发文坛不小的反响,邵洵美在《狮吼》上写了《关于〈花一般的罪恶〉的批评》,开头他就说“真是毁誉备至了”,针对有人在《苦茶》杂志上的批评文章,如关于诗的道德礼义,关于诗的看不懂,以及诗的用词等,邵洵美一一予以反驳并加以说明,称批评方是“不负责任的批评”。
八年后的一九三六年,邵洵美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诗集《诗二十五首》。从金屋书店开始,邵洵美对出版的兴趣与日俱增。之后因徐志摩的邀请,他入股新月书店,委以经理一职,并主编了后面四期《新月》杂志。因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新月书店被商务接纳。邵洵美另办了时代图书公司,附设可印大型彩色画报的时代印刷厂,引进一台德国最先进的影写版印刷机,设照相、修片、制版、印刷等车间,印制张光宇、张正宇等主编的《时代画报》《时代漫画》等,此机解放后转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承印新创刊的《人民画报》。邵洵美另对四马路金屋书店的原房进行改造,作为时代书店的门面,出刊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以及《十日谈》《人言》等。可以说,在邵洵美的诗人桂冠旁,还应给他一个出版家的头衔。
《诗二十五首》是邵洵美主编的“新诗库”第一集第五种,由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这是他的一部重要诗集,精选了八年中的二十五首诗,虽也是薄薄的一册,却有他的不少代表作,表明了他在诗艺上的不断成熟,如《洵美的梦》《天和地》《风吹来的声音》《蛇》等。在这部诗集中,邵洵美破天荒地写了近万字的《自序》,第一次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他的诗歌观。他说:“我写新诗已有十五年以上的历史,自信是十二分的认真。原因是我和新诗关系的密切是任何人所不知道的,我写新诗从没有受谁的启示。我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种的熏陶与影响,外国诗的踪迹在我的字句里是随处可以寻得的。这是必然的现象,一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当然会沾染到他们的一些气息。但是我的态度不是迂腐的,我决不想介绍一个新桎梏,我是要发现一种新秩序”。同时,他对同时代诗人作了中肯评说:“孙大雨是从外国带了另一种新技巧来的人,他透澈、明显,所以效力大,《自己的写照》在《诗刊》登载出来以后,一时便来了许多青年诗人的仿制,不久戴望舒又有他的巧妙的表现,立刻成了一种风气。当然,光有新技巧也不够,我们知道孙大雨在技巧以外还有他雄朴的气质,戴望舒在技巧以外还有他深致的情绪,摹仿他们的人于是始终望尘莫及。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有了新技巧还要有新意”。这篇《自序》,可以看作是邵洵美关于新诗的宣言。陈梦家在编《新月诗选》时,选了邵洵美的五首诗,其中四首来自《诗二十五首》。陈梦家说:“邵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那绻绵是十分可爱的”。一九八八年八月,上海图书公司所属上海书店出版社原版影印《诗二十五首》,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这是邵洵美的诗在新中国诞生后首次介绍给读者。到九十年代初,周良沛编选《中国新诗库·邵洵美卷》,共二十八首诗,三首选自《花一般的罪恶》,其余均选自《诗二十五首》,并撰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作为《卷首》,第一次对邵洵美及他的诗作出全面评说。
当然,不能否认,《花一般的罪恶》是邵洵美喜爱的一部诗集。朱自清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选的三首诗《昨日的园子》《来吧》《我是只小羊》,均来自这册诗集。不仅内容,更因为它装帧的精美别致,以至直到今天,这册诗集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此书收藏流转有序,是沪上老诗人任钧生前的旧藏。作为抗战时期以时代为号角的左翼诗人,会喜欢并几十年来保存一册“唯美派”诗集,可见诗人艺术取向的多面性。
说点《花一般的罪恶》一书拍卖期间的花絮。征得原物主的同意,拍卖公司将《花一般的罪恶》做了少量的复刻本,还原了旧版初时的烫金字样,封面上的金色花卉也压制成凹凸型,这精装书封的复制,比一般的平装本影印有更大的难度,所以称复刻本,如此化一为百,让更多无缘见识原版本的读者,尤其是邵洵美诗歌的爱好者,在这“下真迹一等”中,略感原著风貎。当然,也给邵洵美及新诗研究者提供更多版本考证的便利。正如五十年代丁景唐先生决定影印五四以来优秀文艺期刊时所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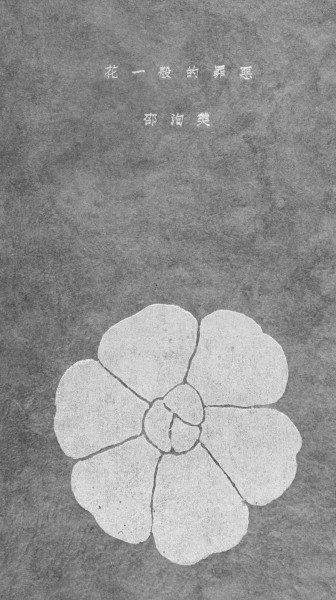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