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浴洋
年届期颐的王鼎钧先生(1925—)是当代文坛重镇。在过去数十年间,他的作品风行海内外。与他同龄的聂华苓先生曾经概括自己“一生三世”——“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三生影像》)。倘若把“爱荷华”换作“纽约”,此说对于王鼎钧先生也适用。其与时代同行的百岁人生,是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重要见证,更不用说他还自觉存史与作文。
文学史上的王鼎钧主要以历史书写与散文创作名世。他的四卷本回忆录(《昨日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堪为巨制,而其散文中的“人生四书”与“作文六书”诸系列也都深受读者欢迎。既能写大气磅礴的别样史著,也能以轻松亲和的口吻分享自己的艺文心得,王鼎钧兼具两副笔墨。金针度人,致力提升中文读者的文艺欣赏素养是贯穿其整个写作生涯的一条主线。他在这一方面用心最力,用功最勤,用情也最深,背后寄托了以文艺欣赏作为理想的国民素养的期待。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王鼎钧作品系列”便汇集了他的这类结晶。《文艺欣赏七论》(2023年版,以下简称《七论》)是其中最新一部。
《七论》顾名思义,书分七辑,依次围绕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绘画、书法与篆刻等七种文艺类型应当如何“欣赏”展开。每辑收文一组,通常以题为“漫谈XX欣赏”的总论起首,然后辅以若干具体案例的专论。这也正是《七论》的最大特点——既提供欣赏某一文艺门类的理念、知识与方法,更结合作品演示方法、态度与经验的使用,尤其是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最后一点才是王鼎钧的文艺观与欣赏术的核心,即《七论》从表面上看是在传授关于文艺欣赏的专业知识,但宗旨其实强调了文艺与日常生活的内在关系,特别是怎样将文艺欣赏内化为现实人生的组成部分。
现实中人为什么需要文艺?在王鼎钧看来,“现实世界产生欲望,艺术世界产生美感,欲望使人烦恼,美感使人的心灵净化”。所谓“美感”,并不只是“美丽漂亮”,“而是凭自己的直觉进入一个圆满的状态,没有利害,没有恩怨,没有逻辑,没有‘小九九’”。(《漫谈诗欣赏》)所以,欣赏文艺可以说是“人之为人”的本能需要,是人性完满的重要途径。因此王鼎钧认为,人在内心深处与文艺皆有因缘,“有人只是因缘未到,我们在中间帮他跟诗结缘”。(《今诗话》)“在中间帮他跟诗结缘”可谓《七论》的主旨。将有缘人摆渡至文艺的彼岸,在艺术世界中自我发现与自我完成,实现人性与人生的上升与提炼,是文艺欣赏的旨归所在。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懂得“欣赏美感”,能够“净化心灵”,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由人组成的现实世界也就自会不同。
当然,文艺欣赏有其门槛,这是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别所致。《七论》首先要引领读者跨越的便是这道门槛。门槛的关键是形式。于是在《七论》中我们可以读到什么是诗的语言,什么是诗的节奏;什么是小说的“事件”,什么是小说的“结构”,小说中情节与人物的关系是什么,小说家如何“表述”又怎样“隐藏”;对于一部戏剧,可以“看故事”,可以“看演员”,还可以“看导演”……所有这些,王鼎钧都加以图示般的详细示例,令人一目了然,别有会心。譬如他解读杜甫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极精到:“落木萧萧,老成凋谢,是静态的,线条是直的;长江滚滚,新生代汹涌而来,是动态的,是横线,是曲线。一边让我们看见公墓,非常安静,好像凝固了,一边让我们看见运动场,众声喧哗,每一秒钟都有变化。生死两个场面中间只隔一条线,杜甫把它戏剧化了。”(《漫谈诗欣赏》)同样是感慨“一代新人换旧人”,这便是“诗的语言”。
王鼎钧的语言也十分精到。虽然讲的是专业知识,但全无理论腔与说教气,读来熨帖、舒服,同时又敏锐、准确。如果说在“诗的语言”之外何谓“散文的语言”,尤其是“说理的散文”的语言,《七论》就是范本。而在文学史上,王鼎钧的写作其实渊源有自。读《七论》让人不难想到朱自清1946年出版的文集——《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在这两本书中,朱自清以“明白清楚”的白话文讨论文艺的“标准”与“尺度”,致力将好的文艺作品引渡给更多读者,使之“雅俗共赏”。不但在语言形式上,乃至在思想追求上,王鼎钧都在朱自清奠立的这一传统的延长线上。而这本身就是现代散文的一翼,也是知识人介入现代生活,贡献于现代精神与现代社会的一种方式。
朱自清的文论兼及“旧的标准”与“新的尺度”(《〈标准与尺度〉自序》),但其秉持的是“现代的立场”(《〈论雅俗共赏〉序》)。王鼎钧也如是。《七论》纵横古今,视野开阔,但他并不厚古薄今。相反,其观念是开放的,亦是现代的,他主张“以今化古”。以文学领域“古今之争”分歧最大的新诗与旧诗的关系为例,王鼎钧认为“时至今日,我们恐怕不能再说‘所有的好诗到唐朝已经作完’”,因为“唐人知道箫声吹出怀乡病,不知道号兵吹出来的是血丝,唢呐吹出来的是火焰”,“唐人知道‘玉树凋伤风树林’,不知道‘叶子慢慢片片剥落,像凌迟’(张错)”……对于古典文学熟稔于胸的他而言,正典的传统没有造成画地为牢的局限,反而让他更加洞察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后出转精”“兼收并蓄”与“标新立异”。王鼎钧发现,“每一次变革都使文化遗产更丰富”。他以历史的也是未来的眼光看待新诗的命运:“当年他们有志气,从封建大家庭毅然出走,不带走一片浮云。现在他们回来支撑门户,当然要盘点老家有多少家底。”在他看来,新诗与旧诗早已不再对立,新诗正在接续旧诗,也将在不断开拓“诗的疆域”的过程中承担更多的“期待”。(《今诗话》)王鼎钧形象地说道:“《诗经》是中国文学之父,《楚辞》是中国文学之母,唐诗是长女,明清小说是长子。五四运动,中国文学有了外遇,生下一个混血儿,就是新诗。这个混血儿受家族歧视,在外面创业,有很大的成就,又认祖归宗,为这个大家庭增光。”(《法拉盛诗歌节》)
王鼎钧的如此观念与立场不仅表现为他对于文体演变的通达态度,更从他对于现代价值理念的坚守与高张上体现出来。“新文化”的内核是“新价值”。这构成了王鼎钧的文艺论述的支柱。他指出,文学的意义在于“特性”,“有特性才有自己的价值,才可以独立存在,不被并吞,不能代替”。(《漫谈诗欣赏》)而“艺术的表现者毕竟是人”。(《张火丁的两出戏》)所以,对于具体的“艺术的表现者”及其“特性”的理解与尊重也就是“文艺欣赏”的不二法门。而这份理解与尊重指向的则是对于人的“独立存在”的肯定。王鼎钧特别强调从人的本性的层面上区分“艺术”与“宣传”:“艺术作品都应该多义,多义打破空间的限制,天下的人都能接受,也超越时间的限制,后世的人也能接受。这是艺术品和宣传品最大的区别,宣传品只能针对特定的对象,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有唯一的含义。”(《今诗话》)“作家多半不能超越个人立场表现人生,读者多半不能超越生活经验和现实利害欣赏作品”。(《移民文学》)批评家也只是“强调那些作品反映了什么、代表了什么”,“越说越抽象,简直拿小说当论文了”,带来“许多不正确的暗示”。(《漫谈小说欣赏》)在这样的潮流中,文艺的“多义性”被简化,“特性”被抹杀,“宣传”而非“艺术”充溢于世界。
不过,即便在再艰难的困境中,犹有艺术家不向现实低头。“社会极其单一化的时候,犹能容得下梅兰芳,犹能产生张君秋,岩石的裂缝里有土壤,就能展开一丛兰花,或者立起一棵苍松。”(《张火丁的两出戏》)这是因为真正的艺术充盈着人性的力量,真正的艺术家能够将苦难转化成为精神资源,并且从中锻造恰当的形式。此时,以思想、阅历和情感为之赋形的艺术也就不仅是技巧,而是一种精神的形状甚至人性的形式了。王鼎钧非常欣赏画家李山。“我问他在‘那个十年’如何继续作画”,李山回答:“只要上头有天,下面有地,我就能画。”王鼎钧为之震撼。由此再看李山笔下的骆驼。“那些年,李山贬新疆,‘天苍苍,野茫茫’而众神默默,他与许多‘沙漠之舟’朝夕相看,有一天,忽然像庄子那样,不知骆驼是‘我’抑或‘我’是骆驼,或者忽然像佛家所说的那样,缘起不灭,与骆驼互为今生来世。”(《以画会友》)王鼎钧有感于此,想到帕斯卡尔的名句——“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进而言之,艺术家便是为人性赋形的人。在这种意义上,“文艺欣赏”是将“人”从一切“非人”的因素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是人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完成。
艺术家具有这样的力量,但真正的艺术却不总是被理解与尊重。在王鼎钧看来,“振兴文运固然要鼓励创作,恐怕也得帮助读者提高欣赏力”(《诗手迹》)。唯有“欣赏”的土壤更加肥沃,艺术的参天大树才有望长成,人性的上升与提炼才可以实现。
所谓“欣赏”,既是一门知识、一项技能,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人不但需要学会欣赏艺术,还应当学会欣赏不同流派的艺术。同是现代文章大家,“鲁迅如凿井,胡适如开河,胡适如讲学,鲁迅如用兵”,“读鲁迅如临火山口,读胡适如出三峡”。(《散文七宗》)各人不妨有所好,但也必须领会鲁迅与胡适各有所好。“写小说如潜水,写游记如划船;写小说如登山,写游记如散步;写小说如高歌,写游记如低吟;写小说如驯虎,写游记如养猫;写小说如爆炒,写游记如蒸煮。”(《旅游文学》)不同文类各有各的精妙,欣赏者何妨既“各美其美”也“美人之美”? 这就不仅是欣赏之道,也是为人之道与处世之道了。所以,“欣赏”不单是对于读者与艺术家而言的,也可以发生在读者与读者之间,以及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群与群之间也都需要更多互相欣赏与彼此成全。
从“人各有己”通向“群之大觉”(鲁迅《破恶声论》),这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理想。文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被鲁迅看到,也被王鼎钧看见。《七论》不作黄钟大吕之音,但却在静水流深中延续了这一最可宝贵的人文传统与现代精神。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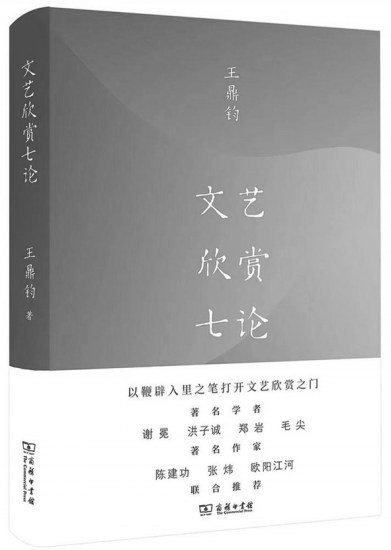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