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枷锁》是毛姆无比真诚地探索个体的终极价值和精神的终极出路的第一次尝试,这个问题之后便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个母题。
■冯涛
查了一下微信记录,我的朋友姚燚二〇二〇年六月问我愿不愿为译林出版社翻译《人性的枷锁》。在接受邀约前我确实有过一些顾虑,主要原因一是篇幅太大,五十多万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并不太喜欢这本书。但反复考虑以后我还是答应了,因为此前已经翻译了毛姆的长篇小说《刀锋》《月亮和六便士》,回忆录《总结》和不少短篇小说,如果再完成这部篇幅最长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的翻译,在翻译毛姆这件事上也算“功德圆满”了。再者,我“并不喜欢”这本书的印象源于年轻时的第一次阅读体验,我也很想看看在自己早已过了“人生的中途”以后对它的认识是否会有所改变。
我在为前一部译作《耻》写译后记的时候正值二〇二〇年一二月份,隆冬严寒,又是新冠肺炎疫情初起,形势最可怕的时候。等到正式开始《人性的枷锁》翻译的时候,惊魂稍定,基本上已经做好跟疫情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了。本来预计一年半左右完成,大约二〇二二年初交稿的,结果又拖了半年,前后算是两年的时间吧。这样算起来,疫情三年,我有两年的时间都在翻译这本书,而且它的初稿事实上是在上海二〇二二年四五月的封控期间完成的。在最后的那两个月期间,尤其是在最后的关头,它的翻译——一定要完成它的翻译简直成了我用以抵抗绝望的主要凭借。在我二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这成了我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
《人性的枷锁》当然不是毛姆小说的处女作,处女作兼成名作是《兰贝斯的丽莎》——他根据自己学医的实习经验创作的一部自然主义小说,作为他文学生涯的啼声初试赢得了不少关注和赞誉,但本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他在几次艰辛的尝试以后,结果却发现此路不通了。毛姆后来被迫转行写起了剧本,意外地大获成功,成为英国剧坛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剧作家之一。极盛时期伦敦西区一晚上同时上演他的四部剧作,当时的《笨拙》周刊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莎士比亚本尊站在他那几出同时上演的剧作海报前咬他的手指头。
就在毛姆本可以作为最成功的剧作家继续成功下去,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名望的时候——他原本也是这样打算的,他却开始深受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如今的记忆的折磨,变得寝食难安起来。为了祛除这一心魔,他在舞台事业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时刻毅然决然地重拾小说创作,几乎是一口气写出了这本他的作品中篇幅最大的自传体小说,也由此奠定了他此后一生小说创作的基调和主题。
幼失怙恃的菲利普·毛姆该如何在这个广漠的世界上安身立命,人生在世,到底该怎么活下去?这是《人性的枷锁》的核心问题。
宇宙恢宏而又冷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众生皆苦,万相本无”。世界的荒谬、人生的痛苦和无意义是每一个敏于感受和思考的个体必将发现的真相和终极事实,所以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所以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也就是说,那便是如何才能说服自己不要自杀。
年幼且有残疾的菲利普独自一人慢慢摸索着成长起来,慢慢地去认识这个世界,慢慢地从一层层束缚着他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他首先挣脱的是宗教的枷锁,宗教诚然是种枷锁,但宗教可能也是个体用以逃避人生痛苦和无意义这个根本问题最方便且最强大的凭仗,扔掉了这个凭仗以后就必须去寻找别的凭仗:挣脱枷锁容易,找到凭仗难。他一度认定艺术可以成为安生立命的根本,但又发现自己在这方面仅有中人之才,这才选定行医作为终身的职业,然后便开始经受情欲的折磨,在精神上脱了几层皮,物质上经受过一番穷困潦倒的考验之后,这才终于认清了自己人生的道路,觅得了足以安生立命的那个职业,找到了可以相伴一生的那个人。至此,菲利普终于挣脱了束缚着他肉体和精神的层层枷锁,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洗心革面,修成正果。
若是跳出小说设置的情境,追问一句:菲利普·毛姆果真找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了吗? 那回答必然是:当然没有,也不会有。如果有的话,毛姆本尊也不会在七十岁上还要在《刀锋》里最后一次让拉里再苦心孤诣地重新寻觅一遍了。《人性的枷锁》是毛姆无比真诚地探索个体的终极价值和精神的终极出路的第一次尝试,这个问题之后便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个母题。其实又何止是毛姆,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位真诚的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都须面对的母题,也是我们每一个敏于感受和思考的个体终须要面对的终极问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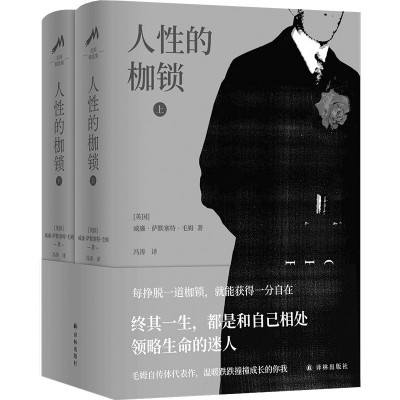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