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向荣
本文副标题之溥仪署名文章,指《我的前半生(全本)》附录三《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以下简称“署名文章”)。它发表于《人民日报》1961年9月17日第五版。笔者作为《我的前半生(全本)》的责任编辑,把它作为附录三,非常偶然。2006年5月,我根据《我的前半生》图书档案提供的线索,想在《人民日报》找寻《我的前半生(全本)》序言《中国人的骄傲》,但在该报电脑上遍查,只有一篇文章题目为《中国人的骄傲》,即庆贺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奥运会上取得首枚金牌的文章,却无意中发现了溥仪的这篇署名文章。该文有明确的批判台独内容,这在溥仪著作中当属仅见,故在编辑过程中把它纳入书中。
本文正标题所谓近因,指“九·一八”事变形成的原因,当然限制在溥仪本人在《我的前半生》三个版本(指李文达“另起炉灶”的《我的前半生(批校本)》《我的前半生(全本)》和《我的前半生》)以及“署名文章”中所述;本文正标题所谓远果,《我的前半生》的三个版本均未述及,而在“署名文章”中才有一定的表述。考察文献之间的关系,既是《我的前半生》成书史的组成部分,又能认识溥仪思想在他特赦后的新发展。
笔者在群众出版社2021年版拙著《〈我的前半生〉成书史论》第三章《开端——〈我的前半生〉(批校本)》(以下简称“批校本”)中,经过详细地考论,说李文达“另起炉灶”的《我的前半生》“执笔时间在1961年6月中旬之后”。并云“到1961年8月15日,已经完成了‘另起炉灶’一稿的第一、二、三章和第九、十、十一章”。即第一章《我的家世》(1859-1908),第二章《我的童年》(1908-1917),第三章“小朝廷”(1917-1924),第九章《在苏联的五年》(1945-1950),第十章《由抗拒到认罪》(1950-1954),第十一章《认罪以后》(1955-1956)。可见李文达并不是按这部回忆录的时序操作撰写,而是先记叙末代皇帝的早年生活,再记叙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前期。那么,从1961年8月15日,到1961年9月中旬,溥仪和李文达又写出了该书稿的什么内容呢? 众所周知,“批校本”是1962年2月定稿的,从前1年的8月到次年的2月,大约有半年时间。假定“署名文章”也由李文达执笔,那么,作为心中早有酝酿准备的文章快手李文达是否已经写出“批校本”第五章《公开叛国》第一节《不静的“静园”》,为“署名文章”准备了素材呢? 这当然属于假定式的判断,也可以做翻转过来的认识,但都不能抹杀“署名文章”和“批校本”的内在联系。先看看“署名文章”的表述:
记得是在一九三一年夏季,当时我住在天津。我的弟弟溥杰正在日本东京读书。因为暑假就回国了。他告诉我,在他回国之前,曾经在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任职的吉冈安直中佐邀他到鹿儿岛去玩。临别时并且神秘地对他说:“你回到天津之后,请对令兄说,现在张学良搞得实在太不像话了,也许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未可知。请令兄多加保重罢! 他不是没有前途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快真相大白了。就在一两个月以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军国主义出兵东北。而在这不久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板垣征四郎的亲信上角利一给我带来了当时已经投降日寇的大汉奸熙洽的一封信,劝我“速赴东北主持大计”。接着,臭名四溢的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又以让我主持一个“新国家”等等甜言蜜语为诱饵,把我骗到了东北。难道“九·一八”事变像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偶然事件”吗? 不,决不!从以上一系列事实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制造事变作为借口而出兵占领我国东北,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处心积虑地经过周密布置然后采取的行动。
再看“批校本”第五章《公开叛国》第一节《不静的“静园”》的表述。
……我怀着喜事的预感到了日本兵营,香椎浩平在他的官舍门口正等候着我,他勿忙地告诉我,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派了人来,来的人希望在这里和我见面。说着,他领我走进他的客厅。在这里我看见有两个人恭恭敬敬站着,一个长袍马褂,是久别的罗振玉。另一个穿西服,脸孔陌生,从他的鞠躬姿势看出他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了这个人叫上角利一,是板垣大佐手下的人,然后就退出客厅,屋里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罗振玉给我请过安,拿出一封信给我。信是熙洽写来的,熙洽是一个远支宗室,当时是吉林省长官张作相的参谋长。信里说他等了二十年,终于把复辟的时机等到了,希望我即刻到祖宗发祥地,“面南复位,救民于水火”,在“友邦”的帮助下,先据有东北,然后再图关内“一匡天下”。看完了信之后,罗振玉除了把信中意思重复一遍之外,又大讲关东军的仗义协助,东北全境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都等着我去,只要我同意,日本军舰就来接我动身。他说完,上角利一向我转达板垣的表示说,关东军对东北毫无领土野心,愿意全力帮助我建立一个新国家,因此派他来接我到旅顺,然后就到沈阳即位,希望我立时动身。
我期待了二十年的事情,终于来临,这个好消息使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从这年的夏天,我就有了一种“喜事临门”的预感。这预感不但是从报上和郑孝胥的口头上可以听到,而且更有溥杰从日本给我带来的机密的暗示。他这次暑假回国之前,曾应前天津驻屯军参谋吉冈之请,到吉冈驻防的鹿儿岛去盘桓了几天,吉冈对他说:“请告诉你的令兄——宣统帝,张学良在满洲国闹得很不像话,也许最近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宣统帝多保重吧,他不是没有希望的。”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署名文章”和“批校本”叙述的顺序不一样:前者先说吉冈安直的话,又叙上角利一捎信之事,再述土肥原贤二主持一个“新国家”的甜言蜜语;后者则把上角利一捎信之事放在最前面,复叙板垣征四郎“建立一个新国家”的说法,末了言吉冈安直的话。在“批校本”同一章第二节《土肥原和他的“道具”》中,又补上土肥原所说同样的言论。看来这两个日寇都有骗人的鬼话——建立一个“新国家”,揭示了“九·一八”事变直接的原因。诚然,由于文章体例不同,“署名文章”是论说文,“批校本”是自传文,使得前者叙述史实宜简宜粗且少跌宕,后者叙述史实详尽擅腾挪且多人物活动的细节。两个史料在语言表达上反映出三个容易忽略的问题:第一,“批校本”因是稿本,“你的令兄”的说法存在语病而不顾,“署名文章”则在《人民日报》发表,更正为干净的书面语言“令兄”;第二,“批校本”使用“盘桓”一词表示逗留之意,如此古雅的语汇,经常出现在溥仪口述溥杰执笔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中,相信或是李文达或是《人民日报》的编辑,从文字通俗的角度考虑,更正为“去玩”(“批校本”以后的两个版本则将“盘桓”改为“做客”);第三,“批校本”直言溥仪曾经的身份“宣统帝”,从具体的时空环境来看,并无错误,但《人民日报》删削了这一说法,则是新的时空环境的产物,愈发显得正规和严谨。事实上,“批校本”之后的两个版本也是遵循《人民日报》的表述的。
倘“署名文章”从“批校本”脱胎而来,当然具有删繁就简的过程。“批校本”披露田中奏折的内容说:“吾人如欲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当吾人得以支配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又披露其内容说:“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现皆实现,唯第三步的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署名文章”仅用较短的语言提及“田中奏折”:一九二七年的所谓“田中奏折”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这个奏折明目张胆地写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而欲征服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困惑:同是省略式征引,“署名文章”出现的“田中奏折”里“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而欲征服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语,在“另起炉灶”的所有三个版本中都没有。“批校本”与从它发展出来的后两个版本的表述一致,为同一语境。那么,“署名文章”的话是从哪里来的呢? 难道可以反过来说,是“批校本”由“署名文章”脱胎而来,进行了由简入繁的修润? 另一种可能还是“批校本”的表达在前,溥仪或李文达根据“田中奏折”确有的内容择要言之(笔者按:溥仪的疏忽是未用省略号)。须知身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的末代皇帝,在所在单位并无帮助他的写手,他自己凭一人之力,囿于水平限制,也难于完成在党报上发表文章的任务。只有公安部的李文达最熟悉他在“署名文章”中想要写的内容,他俩就是这样提炼“田中奏折”内容的,毕竟论说文和自传文对征引的要求有所不同。“署名文章”中这句话在“批校本”中可以不说。日寇即便特狂妄,后来又与德意结成轴心国,也奈何不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何言“征服世界”呢?
“署名文章”也有稍稍加强“批校本”的地方。它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时举了一个例子:“日本的一个‘华族’(‘明治维新’后的贵族)水野子爵当时就曾送我一把扇子,上面别有用心地题上‘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这样两句诗,暗示我要‘卧薪尝胆’待机东山再起。”这个例子产生得较早。据《溥仪文存》(爱新觉罗·溥仪著,王庆祥注释整理)记载,中央档案馆存档溥仪1955年前后所写的认罪材料(详见该书第118页-119页)曾引录之。“批校本”上则无此内容。但从它发展出来的后两个版本都添加了上述内容,而且愈表达愈完善:
……七月二十九日,日本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我接见了他。在这次平常的礼貌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原来溥杰回国之前,水野子爵亲自找过他,接洽送扇子的事,因此,溥杰明白了这两句诗的来历,并且立即写信报告了我。这是发生在日本南北朝内乱中的故事。受控制于镰仓幕府的后醍醐天皇,发动倒幕失败,被幕府捕获,流放隐岐。流放中,一个武士把这两句诗刻在樱树干上,暗示给他。后来这位日本“勾践”果然在一群“范蠡”的辅佐下,推翻了幕府,回到了京都。以后即开始了“建武中兴”。水野说的故事到此为止,至于后醍醐回京都不过三年,又被新的武士首领足利尊氏赶了出来,他就没再说。当然,那时我也不会有心思研究日本历史。重要的是,这是来自日本人的暗示。那时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东北局势日益紧张,我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已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来说,事实上都是起着行动信号的作用。(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前文已说“批校本”完成于1962年2月。从1961年8月15日以后,溥仪和李文达一直在打磨“批校本”。以李文达之快手,几千字的《不静的“静园”》两三天就写出来了。然而还有一种可能:在写《不静的“静园”》之前,即在撰著“另起炉灶”的第一、二、三章和第九、十、十一章的同时,就已经撰写了“署名文章”,提前做好准备,供《人民日报》之用。但并不像是这样。因为,倘《不静的“静园”》一节产生于“署名文章”之后,为什么会把这样生动的例子漏掉呢? 拙著《〈我的前半生〉成书史论》曾引录“李文达1962年5月28日致溥仪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溥仪和李文达两人对《郑孝胥日记》研究之深。纵观《我的前半生》全书,多次引用《郑孝胥日记》来记录、阐释当时的史实,便可进一步证明该日记对《我的前半生》的重要性。笔者曾在上述拙著中说:“这封信反映出创作主体之间的切磋、沟通情况。这种主动方与被动方(主动方指李文达,被动方指溥仪——引者注)的‘交往’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很像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破案的过程中深入开掘证人、充分发挥证人的作用。”对“证人”的解释,拙著脚注云:“所谓证人指‘帝师’之一,后来担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的郑孝胥。李文达梳理《郑孝胥日记》的相关内容,将某些史实逐一地传递给溥仪,力求在逻辑层面上搞清他面对这些史实的想法。”而李文达致溥仪之信,写于“批校本”完成后的三个月,信中有“这年这月(1931年7月29日——引者注),日本水野子爵来访,题诗‘天莫空勾践’……”语。(李文达注云“郑孝胥日记,六月十五日见水野,郑在场”)可以做这样的推测:撰写“批校本”时,溥仪对水野这首诗的典故叙事尚不熟悉,故于“批校本”中舍之,只在“署名文章”中蜻蜓点水地提及,留待从“批校本”中发展出来的后两个版本逐渐加以更加完善的解释。从中可以看出《我的前半生》成书过程不乏温火慢功的细腻,也就是说,“署名文章”是急就章,撰写它并未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大约是完成了《不静的“静园”》后,为了给《人民日报》供稿而写出来的。
“署名文章”在披露“九·一八”事变的近因之后,讲述“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十四年来东北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中”时,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伪宫内府警卫处长佟济熙悄悄地告诉我说:他亲戚伪警卫官金贤有一个熟人,被日本军队抓去修筑军事要塞;完工以后,日本军队为了保守这个工事的秘密,把所有工人全都杀了,只有他亲戚的那个熟人在九死一生中逃了出来。”无独有偶,“批校本”也举了同一个例子,其描述的详细程度胜过“署名文章”。似乎又像是“批校本”的某些内容脱胎于“署名文章”。其实它们都在相近的时间节点产生,所用素材,包括《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时期积累的东西,全在溥仪和李文达瓮中,只要认识不同作品之间的密切关系,不把“署名文章”作为孤立的存在,而必须把它当做包括“批校本”在内的《我的前半生》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做新闻和出版的一次联合作战,并为后来轰动全球的名著奇书鸣锣开道即可。
在溥仪研究文献上有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即李淑贤提供、王庆祥整理注释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基本没有1961年的日记(仅存1月14日一篇)。以溥仪勤写日记的习惯,倘存留这一年的情况,必当记录“署名文章”和“批校本”的撰写。可惜该年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付之一炬。
最后谈谈“署名文章”最显要的价值,即该文结尾的几个段落论述了《我的前半生》系列没有说的内容:20世纪60年代“展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在今天是多么的必要”。即“九一八”事变的远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覆灭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看,不少过去曾经欠下中国人民血债的罪犯,不是又在嚣张一时了吗? 吉田茂,当年我进天津日本租界时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在田中内阁时曾经以外务次官的职衔行使外务大臣的权力,是推行“田中奏折”中规定的侵略方针的一员急先锋。岸信介,过去被称为“满洲五巨头”之一,曾经在伪满任“产业部次长”和“伪总务厅次长”,大量掠夺中国东北的物资。这两个战犯,战后都先后当了日本首相,竭力推行复活军国主义政策,下台后仍然在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而奔走呼号。至于过去是关东军中的要员,而今天又成为日本重新武装的骨干,更是不乏其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在今天又开始暴露了。池田政府不是在叫嚷什么“台湾归属未定”吗? 外相小坂不是公开表示要“支持自由台湾”吗? 卖国贼廖文毅不是被豢养在日本准备作为建立所谓“台湾独立国”时所用的傀儡吗? 这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主张“满洲独立”和把我豢养起来作为建立“伪满洲国”时所用的傀儡,手法如出一辙。
这是迄今为止笔者看到的唯一的末代皇帝公开发表的反对台独的言论,并且把台湾独立和伪满洲国做“手法如出一辙”之比。它是20世纪60年代溥仪特赦后,历史性的、政治性的、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充分体现了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敏锐把握和清醒觉悟。同时,报刊政论文“大批判”的鲜明色彩,以一种文风特质,亦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署名文章”可补“批校本”之欠缺,也可补完成形态的《我的前半生》的欠缺。它对于台独思潮的批判,紧密联系对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批判。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反动势力从来都是台独势力的政治支撑。溥仪及其时代研究是当代性的研究,而任何一门学科的当代性研究都是本身十分丰富,并且不断地在充实、延展着。说到底,一个甲子之前的文章,在今天乃至将来均将不失镜鉴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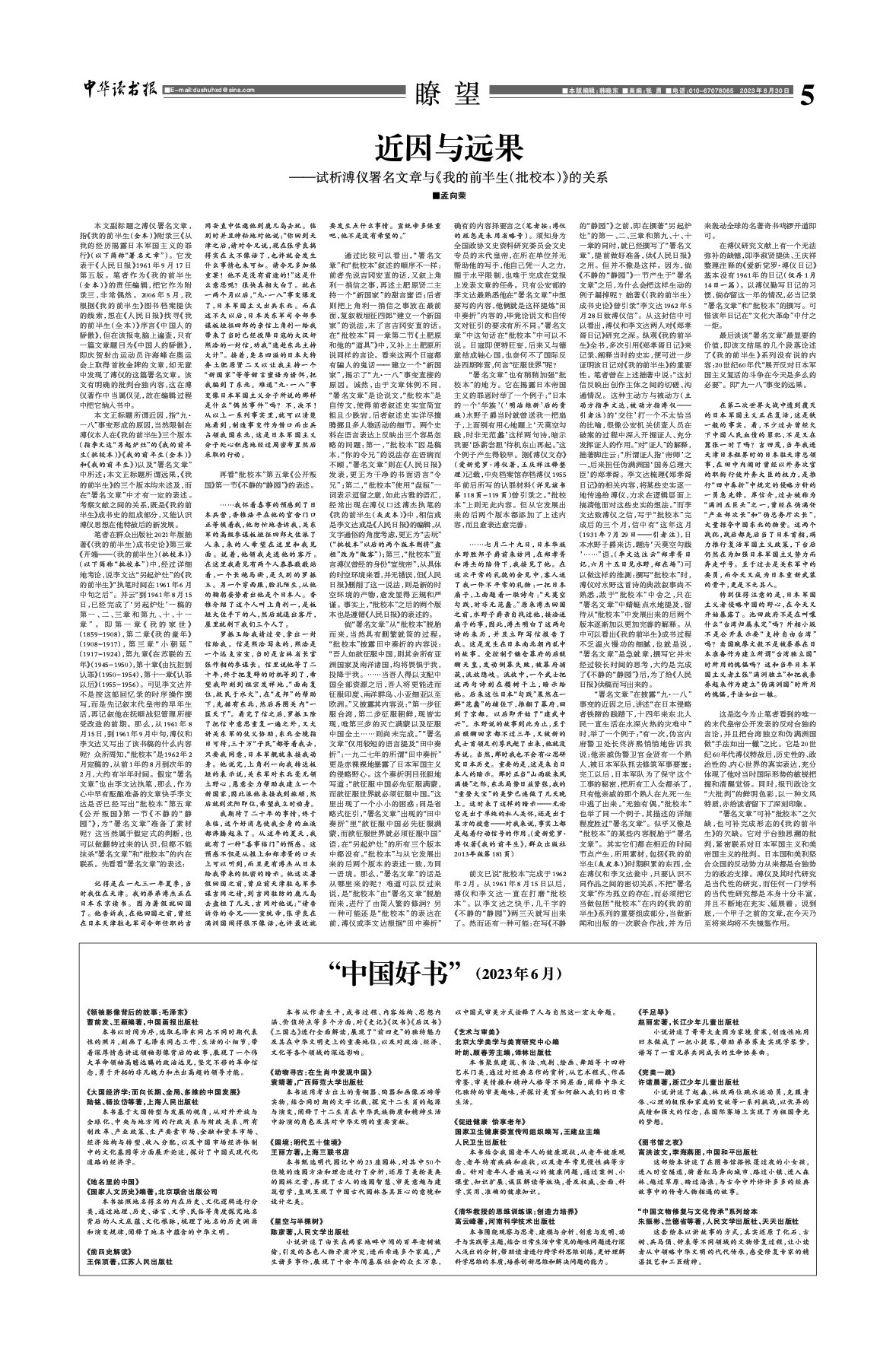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