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技术正在一条宽广的高速公路上前行,人们享受着技术带来的成果,也憧憬着道路尽头的彩虹。然而,借用电影《黑客帝国》的隐喻,高速公路又是一个机械化世界中充满危险的地方,道路负荷越来越重,车辆速度越来越快,危机与风险暗流涌动。更为复杂的是,几乎每个人都参与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与运行,却没人能准确预知这只庞然大物延伸向何方。
西方工业革命孕育了当代世界技术文明,技术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然而,技术网络遍布的时代,人是自由的吗? 人类未来的社会形态,只能由技术来决定吗? 远离高速公路的丛林间,还有其他道路供人们选择吗? 关于以上问题的反思,随着各种技术的快速变迁,又衍生出了许多新版本。
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哲学教授杜谢克(Val Dusek)的《技术哲学导论》从多个方面讨论了技术及其伴生的哲学、文化、社会等问题。全书主题包括: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定义、技治主义、技术理性、技术决定论、技术自主论、技术时代人的本质、女性主义与技术、非西方技术与地方性知识、反技术运动、技术的社会建构等。作者没有追求时髦酷炫的理论引介,而是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定义等基本概念谈起,循序渐进地进行理论阐释,较好地完成了一部导论性作品应当完成的工作。
是技术改变了社会
归纳主义、技治主义、技术理性、技术决定论、技术自主论等群体无疑承担了技术高速公路“筑路人”的角色。
科学是否构成了技术公路的“路基”,这是当代技术面临的基本问题。部分学者将技术理解为“应用科学”,这种不考虑情境的“移植”无疑是片面的。人类曾经拥有漫长的技术历史,技术史与科学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都处于各自独立的状态。即使是当代,许多技术发明仍然是偶然或者反复实验的产物,而不是直接运用某项科学理论来实现预期的科学目标。为了避免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江晓原提出“科学画图景,技术见真章”的形象描述,以此厘清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科学与技术有着各自的运行方式,讨论二者的关系,既不能“乱点鸳鸯”,亦不能“一分了之”。
科学与技术的各种关联当中,科学仪器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联接方式。纯粹的大脑思考和肉眼观测在现代科学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作为一种技术产品的科学仪器成为科学研究的核心。当代科学十分依赖复杂精密的科学仪器,成为高度“技术负载”的工作,仪器准许我们看到哪里,我们就看向哪里,科学仪器先于科学研究。仪器的应用,使许多仅仅存在于理论上的“东西”成为了可以操作的对象,能否通过仪器操作成为判别那件“东西”是否存在的重要标准。
技治主义是技术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技术专家成为当代社会显性或隐性的“操盘手”。“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办”,这一观念深深根植于多数人心中。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讨论了“哲人王”的培养,将数学作为重要的训练手段。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构想了一个由所罗门宫从事自然研究、带领人们走向繁荣的技治主义乌托邦社会。圣西门建议直接由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统治社会。孔德的技治主义版本中,科学家取代了教士,成为真正知识的来源。时至今日,技治主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传统的政治家和商业领袖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与决策者,科学家、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学者、传播学者等群体组成了新的技术专家阶层,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前进方向。
按照“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技术发展决定了社会与文化形态,通俗讲就是“有什么样的技术,便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现实中关于技术决定论的例子比比皆是,汽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计算机技术重构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性质,核子技术塑造了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马克思指出,技术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上层建筑,“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技术不仅决定了当下的社会形态,也预设了未来的社会形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正在步入一个重新定义自我与工具的时代,人类社会似乎面临着一次不可避免的重新塑造。
针对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技治主义者和技术决定论者并非盲目乐观,他们运用严格的评估手段来控制风险。核电站的熔毁风险、环境开发的生态风险、工业产品的安全风险等各类风险均可以建立对应的评估机制与评估模型。当然,目前绝大多数风险分析仍然由技术专家来完成,按照流行的社会观念,公众似乎“不太理性”,由公众进行风险评估,不如“严谨的”专家“靠谱”。无论如何,风险评估机制为技术公路安装了护栏,技术可以更加“安全”的加速前行,“筑路人”对于技术之“成”充满自信。
反技术思潮种种
社会建构论、女性主义、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深生态学等群体对于当代技术及其伴生的各类问题进行了反思。其中,有些学者寻求技术时代的“桃花源”,有些学者力争“筑路权”与“方向盘”,有些学者主张另筑一条“人本主义”技术道路,这些思想体现了技术时代的困境与危机。
社会建构在当代技术系统中无处不在,手机、电脑、汽车、飞机等技术设备及其技术理论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因素建构而成的。对于许多技术哲学“小白”而言,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不难理解,至少比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建构论关于科学事实与科学对象“颠覆常识”的知识论阐述令人轻松愉快。按照“技术系统”的定义,技术不仅包括物理制品,还涉及各种社会利益与社会关系,“硬”与“软”两个方面共同塑造了当代技术形态。电影《黑水》与纪录片《我们所知的魔鬼》中,杜邦公司刻意隐瞒全氟辛酸(PFOA)的致癌风险,制订自来水含PFOA的安全浓度标准,反映了资本利益集团对于技术系统的介入与影响,暴露了专家风险评估机制的缺陷。2023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消息,宣称“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这一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政治博弈同样值得深思。
当代技术解放了女性吗? 还是压抑了女性? 这个问题涉及全球近一半人口。按照社会常识,汽车、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等技术解放了女性,女性可以减少家务时长,获得更多的生活余暇和自由空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现代技术的高效便捷,人们购物次数越来越多、房子越住越大、更换衣服越来越频繁,女性被更多地“锁定”在生活琐事当中。不仅如此,当代技术对于女性职场也并不友好,女性被天然地与文书、秘书、打字员、速记员等职业相联系,远离工程师等“男性”职业。更有甚者,现代生殖技术剥夺了女性对身体的控制权,将女性身体视为实验器皿,女性被进一步“物化”。
当代反技术大军中,浪漫主义和生态主义是两股中坚力量。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迅速扩张,工业化城市的污染、贫困、丑陋使卢梭等浪漫主义学者对理性崇拜心生厌恶,他们拒斥工业文明带来的伪饰与扭曲,力求感知自然之美,将野性自然作为智慧与灵感的源泉。当代“回归自然”运动可以视为浪漫主义等思潮的复兴,展现了人们对于冰冷虚伪的技术世界的蔑视与抗争。较为激进的深生态学认为,传统生态主义把自然视为实现人类福祉的工具,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是一个整体,“肢解自然就是谋杀自然”。人类对于生态系统的过度介入与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不同文化思潮为解构与反思当代技术提供了大量见解,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需要面对“破”与“立”这一基本问题。除了汉娜·阿伦特等少数学者对技术表现出完全负面与悲观的看法之外,多数学者都憧憬了技术的理想形态及其社会图景。芒德福构想了一种新石器时代与生命更加接近的技术形态,用去中心化的民主技术取代今天的官僚技术,这一技术非常类似于电影《鲸骑士》中毛利人的技术活动与生活方式。女性主义者希望建立一种更加亲近自然的、饱含情感的、人道主义的技术形态。尽管许多乌托邦式的技术构想在今天看来过于理想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揭示了当代技术的顽疾,在日益支配人类的技术公路之外,开辟了多条富含人文关怀的“丛林小径”。
技术可以被理解吗?
曼哈顿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阿波罗登月工程等大型复杂技术工程具有丰富的技术哲学研究价值,可以从多个哲学视角进行分析,同一工程甚至可以容纳社会建构论和技术自主论等相互抵触的学术观点。以阿波罗登月工程为例,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看,登月工程与美苏冷战争霸、意识形态对抗、民族主义倾向等政治与社会因素存在密切关联。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太空项目的财政资助逐渐减少,太空探索也受到波及。政府支持、社会需求、公众认可等因素成为当代大型技术工程的“动力之源”。
然而,从技术自主论的角度来看,如果将阿波罗登月工程理解为一个超级复杂的技术系统,工程师、政客、公众、宇航员、制造商等群体都只能按照特定规则完成系统的一小部分工作,对于其他工作都“极其无知”,那么任何个体责任都会淹没在这个庞大的技术系统当中。正如纳粹官员艾希曼声称的,自己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每个人都只是在做自己的一小部分工作罢了。技术自主论关于复杂系统与个体责任的观点,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流行数十年的阿波罗登月“骗局说”:由于公众无法了解复杂工程的全貌,于是创造出各种关于登月骗局的“娱乐”版本。其实,何止是公众无法了解工程全貌,即使是大型技术工程的当事人,也难以完全掌握复杂系统的每个环节。
《技术哲学导论》讨论非西方技术与地方性知识时,提到了“技术与魔法”这个有趣的话题。任何技术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常常孕育于某种深刻的文化根源。如果将技术与文化强行剥离,留下纯粹的技术过程,无疑会破坏技术的完整性。世界许多民族的造船、捕鱼、种植、收获、冶炼等活动都会佐以祈祷、唱诵、庆典等文化活动,这些“魔法”文化与技术过程形成了有机整体。如果可以接受较为宽泛的技术定义,那么这些文化动员、文化心理、文化传承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传统技术的一部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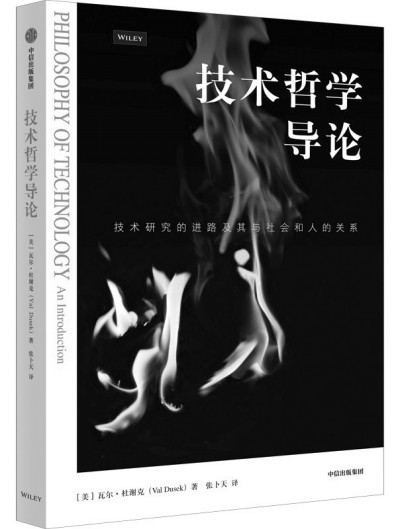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