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蒯家姐弟来说,家虽然小,但这是他们出生与成长的地方,这里有他们的过去,有爸爸,有爸爸栽下的梨树。
《梨花里》是荆歌“少年的美丽乡愁”系列中的一部,作品以抒情笔调描写了一个叫梨花里的江南小镇,叙述了一群少年在不长时间里的生活片段。读完作品,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与意绪弥散开来,有那么一点伤感,有那么一点惆怅,有那么一点欢乐……
儿童文学总是与成长相关。不过,这成长一般是在成人注视下的,儿童虽然是成长的主角,但是在作品中,他们是被看的对象。《梨花里》不同,孩子们依然在成长,但是他们不仅仅是被成人关注,同时,他们又在看着成人,试图理解成人的世界,走进成人的内心。正是这看与被看组成了作品的双重视角与双重叙事。
对于蒯琴和蒯强姐弟来说,作为香山帮匠人的爸爸的去世无疑是家里天崩地裂的悲剧。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的意外离世一下使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顿。有时,一桩突发的事件可以让人一夜长大,蒯琴就是这样,这个小学生对弟弟说:“要勇敢地活着! 强大的人,是不会被任何力量打败的! 你要像个男子汉,不要动不动就哭鼻子,丢人的!”然而,对蒯家来说,灾难接踵而来。爸爸刚刚去世,要债的人就上了门。五十万,如同天文数字一样的债务和凶神恶煞般的讨债人使蒯家坠落到深渊。面对这样的巨额债务,蒯家姐弟曾经不约而同地想到逃走,但蒯琴没把这个念头说出口就否定了,她紧接着想到的是去劳动,去挣钱还债。他们计划每天放学后到河边去抓鱼,卖给镇上烀鱼干的陈师傅。蒯琴真的这么做了。她找到同学——渔民的孩子林小红弄来丝网,第一次下网就捕到了鱼,卖了二十块钱。然而,卖了二十元后蒯琴沮丧地计算出,凑够五十万需要近七十年。况且不是每天都能捉到鱼,蒯强甚至为了捉鱼掉到河里差点淹死。
如果说爸爸的意外去世让蒯家姐弟看到了生命的无常与生活的艰辛和残酷,那么接下来妈妈与其旧时同学丁叔叔的交往则让他们陷入了迷茫、孤独与忧虑。他们看得出,与丁叔叔的交往让妈妈从悲伤与焦虑中走了出来,变得快乐而美丽。关键的是丁叔叔答应借钱给他们家还债。在成人看来,这是丧偶后女人的再婚,而且,这再婚的对象又是过去的同学,因而,这故事还可以前推演绎。但是,《梨花里》没有把故事复杂化,它的叙述是克制的、有限的,它限定在蒯家姐弟的儿童认知里。弟弟蒯强显然理解得简单,有人愿意借钱给他们还债,这就好。而姐姐蒯琴比弟弟要清醒一点,想得更多更远一点,感受也更复杂一些。姐姐认为这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钱还是要还的,只不过换了债主而已。更复杂的是她觉得丁叔叔是陌生的,她本能地排斥他。她朦胧地觉得妈妈与丁叔叔的关系不是这么简单,接着会有事情发生。妈妈会嫁给丁叔叔吗? 丁叔叔和爸爸哪个好? 丁叔叔在浙江安吉,他们的家在苏州梨花里,要是变成一家,那家又在哪里? 他们会离开他们的家吗……这些在成人眼里显然很幼稚的问题却给这个小女孩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与惶恐。作品不落俗套的地方是始终没有转换视角去写丁叔叔和妈妈如何看这姐弟俩,如何在意他们的言行,如何消除蒯琴的不安,而是始终将视角放在孩子们身上,让他们去观察,去感受,去思考。作品中最让人心疼的就是这童稚的目光与纯洁的心灵,孩子们是用了浑身的气力去面对、去感受、去理解成人的世界。荆歌没有强人所难,更没有说教与煽情,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一切都交给孩子,水到渠成,春来冰消。这是荆歌的儿童观,也是荆歌的成长观,更是荆歌的儿童文学观。成长是孩子们自己的事,儿童文学也应该更多地给孩子们独立的空间,更多地将视角留给孩子们。事实上,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成人与孩子共同的世界,我们在看他们,他们也在看我们。
《梨花里》不但有人,还有地方,这就是梨花里。读完作品,我想到了非洲的一句谚语:“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这句谚语道出的是人与地方的秘密。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养成的标准就是他知道了自己是哪里人。换句话说,一个人的长成就是他获得了“地方感”。因此,也可以说,《梨花里》写的就是梨花里,是梨花里的孩子们,是孩子们童年里的家与家乡。在孩子们的眼中,这是多么好的地方啊,这是江南,是江南的水乡,是江南的古镇,孩子们因家里突遭变故而萌生逃跑念头后,继之而来的却是离开家乡的恐惧。逃到哪里去?“那会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那儿有家吗? 有亲切的小镇吗? 有美丽的道南桥、青龙桥吗? 有细细长长、清清冽冽的黎川吗? 有好吃的多肉馄饨和油墩子吗?”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家乡,每个孩子都可能面临离家的恐慌。我们知道,围绕个体的一切存在都是自我意识的内容,其中包括个体对自身所处地方的定位,它意味着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只有知晓了“我在哪里”,个体的生命感才是具体的,自己的存在才会得到确认。荆歌以往的作品就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他营造的文学世界一直让我们感受到他强烈的地方感。现在,他将这种地方感植入、皴染到他的儿童文学中,让他笔下的孩子与地方建立起了亲密的情感关系。
荆歌是耐心的,他让孩子们去感受。他知道,地方感的养成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开端无疑是家庭,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个体地方感的形成总是从自己的家庭开始的。所以,《梨花里》是从蒯家开始写起的,它是作品的叙述线索,也是蒯家姐弟在命运跌宕中不断依恋家庭、不断理解家庭的过程。对蒯家姐弟来说,家虽然小,但这是他们出生与成长的地方,这里有他们的过去,有爸爸,有爸爸栽下的梨树。所以,丁叔叔的到来对他们,尤其对年龄稍大而敏感的蒯琴而言,实在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可能带来家的变化。有没有家,是否回得了家,是否还能拥有家,对个体而言至关重要。家的记忆是一个人地方感中最为深刻的内涵。以家为圆心,人们随着自己生活半径的扩大而形成关于地方的同心圆。以家为原点,再到邻里,再到家乡,然后才是更远的地方。《梨花里》象征性地叙述道,孩子们从家乡出发,乘船经黎川到太浦河,面对开阔的太浦河,仿佛看到了长江……
小说对孩子们生活与成长的梨花里的书写称得上工笔白描。除了蒯强依恋的那些,这里还有更为美丽的风貌,“老街上的白墙黑瓦、小桥流水、郁郁葱葱的树木、闪着时间之光的青石板路”。它为什么叫梨花里? 正是因为春天如雪的梨花!这里有绵长的历史传承,汝老师和她工作的柳亚子纪念馆就是小镇人文历史的写照。小镇的风土人情太丰富了,就说它的饮食,可不只是蒯强说的馄饨和油墩子,还有陈师傅的烀鱼干、黎里辣脚、生煎、烧卖、套肠、绿豆糕、云片糕、定胜糕、虾仁面、鳝糊面、白斩鸡……正是这些抓住了孩子们的心,其实,这就是孩子们地方感的雏形。由此,他们获得了对一个地方生活的身心体验、真挚情感和最初的价值认同。有一天他们会知道,正是从喜欢黎里开始,他们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家乡,然后是国家,最后是世界,在不断扩大的范围中建立了自我的定位,并形成他们对地方的认知、情感、理想、道德担当与行为自觉。为了渲染这种地方感,荆歌特地设计了汝长风和汝高云这对孪生兄弟的人物形象。他们是黎里人,却出生和成长在青海的格尔木。假期中他们回到了他们的故乡黎里,并且爱上了它。兄弟俩纠结了,黎里好,格尔木也好,它们都是他们的故乡。这种选择性的困难正是地方感形成的深刻之处。
这也许是荆歌的“美丽乡愁”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乡愁是一个文化母题,在已经被反复书写的今天如何写出新意? 特别是对孩子来说,对依然在乡的孩子来说,乡愁是什么? 该如何表达? 它对孩子们成长的意义又在哪里? 我以为《梨花里》提供了一个范本。小说的结尾,丁叔叔落户黎里了,汝家兄弟回了格尔木。人事虽然多变,但蒯家姐弟还在梨花里。家在,爸爸亲手栽的梨树已经开花。在梨花的海洋里,蒯琴的内心忽然涌起一阵小小的伤感,这小小的伤感是小姑娘成长的标志。她自觉地意识到她在梨花里,并且因此为不在的人和远去的人而感到忧伤。
孩子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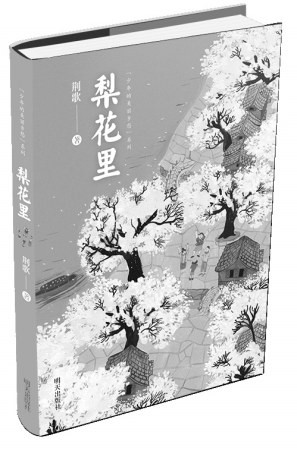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