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庄子,几乎必提“心斋”“坐忘”两个概念。但是,“心斋”“坐忘”究竟指什么,至今也是一桩无厘头公案。本文还是从行气导引的角度再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1
首先还是看庄子如何说。
关于“心斋”,庄子是通过孔子与其得意弟子颜回之间的对话说出来的,是他们讨论的关键词: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 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暤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若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人间世)
“进”意即进展。“方”即方法。“斋”即斋戒。“易”意即容易。“其易”犹“岂易”。“暤天”意指自然。颜回觉得自己老是没有进步,就请教老师用什么方法来改进。孔子说,要斋戒,但不是祭祀那种斋戒,而是“心斋”,就是“心的斋戒”。于是,对话进入核心问题。
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一志”应为“一汝志”,意即纯一你的心识。孔子对于“心斋”所作的具体解释,就是“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这两句是大白话,其实就是练气。后面所谓“心止于符”,意思是心意起缘于思虑,必与出现的境遇符合。而“气”就是“虚而待物者”。成玄英疏:“如气柔弱虚空,其心寂泊忘怀,方能应物。”其实就是虚空之谓。“唯道集虚”意思是:只有真道才能集合空虚之心。最后一句话很重要:“虚者,心斋也。”也就是说,“心斋”即“虚”。我们由此可以稍作推演:“虚”=“气”;因此,“心斋”=“虚”=“气”。
颜回按照孔子说的做了,很有效果:
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 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戏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人间世)
颜回在没有进入“心斋”的时候(未始得使),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实自回)。进入“心斋”之后(得使之),颜回感觉没有自己了(未有回),已经达到“忘我”的境界了。他问孔子,这样是否就是“心斋”所达到的效果。孔子回答,已经达到了,你已经尽得“心斋”之妙了(尽)。接下来的文字是对“心斋”的境界描述:看那个空虚之境(瞻彼阕者),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虚室生白),吉祥所集者为至虚至静(吉祥止止),形体虽坐在那里而精神飞驰(坐驰)。这样就使得耳目内在通达(徇耳目 内通),而超脱、阻断心智的日常使用(外于心知)。如果你通过“心斋”而“坐驰”,鬼神都会冥来附体(舍)。不仅如此,孔子还认为,“心斋”能够化成万物,是禹舜成为圣人的关节处(纽),是伏羲(伏戏)和三皇以前君主(几蘧)所奉行终身的。故由此可见“心斋”对于我们普通人(散焉者)是何等重要。这里的关键词还是“虚”(虚室生白)。由上文可知,“虚”即“气”。一句话,颜回通过修炼气的功法,终于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是这种气的功法效果的校验。
经过上述分析,基本结论是:“心斋”就是练气,或者说就是行气导引之术。
关于“坐忘”,庄子也是通过孔子与颜回之间的对话说出来的,也是他们讨论的关键词: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它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它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枝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 丘也请从而后也。”(大宗师)
“益”意为进步、长进。在这里,孔子认为,彻底忘掉仁义、礼乐这些世俗的道德价值、儒家礼仪,比起一般人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没有得道。当颜回说自己达到一种境界,就是四肢被“毁灭”了(堕枝体),感觉器官的基本功能也没有了(黜聪明),离开自己的肉体(离形),丢弃了大脑的思考、判断功能(去知),同于大道(大通)时,孔子就极为震撼。颜回说,这就是“坐忘”。这里颜回说得很清楚,所谓“坐忘”,就是一个人达到四肢和感官功能没有了,大脑的思考功能也没有了,因此与“大道”为一体。对于这个“坐忘”的本义,学界一般无可争辩。至于“坐忘”的更高意旨,就众说纷纭了。我们暂时搁置,后面综合来说。
很显然,庄子通过孔子与颜回说出“心斋”“坐忘”两个概念,其效果是一石三鸟:第一张扬了自己的主张;第二同时否定了儒家价值观;第三,庄子通过孔子之口,教诲孔门大弟子颜回修炼“心斋”,而且,还反过来让颜回教诲孔子修炼“坐忘”,可谓对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反讽的极致。
庄子在这里所说的“坐忘”,虽然也达到“离形去知”的境界,但没有提到“气”和“虚”。因此,本文对于“坐忘”的论证需要有个间接的推论。
2
虽然庄子关于“坐忘”没有提到“气”和“虚”,但“坐忘”的特点是“离形去知”和“忘我”。这个特点是庄子描述很多得道者所独有的状况:
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 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齐物论)
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颜成子入见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徐无鬼)
南郭子綦为得道者。他凭借几案(隐几)而坐,仰天吐气(嘘),失魄之状(嗒)如同没有肉体(耦)。颜成子游是子綦弟子,名偃。他发现,今天的南郭子綦与以前的南郭子綦不一样。于是惊诧并发问是怎么回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是著名成语,出处即在此。而南郭子綦的回答是:今天“吾丧我”,意即我遗忘、失去了自我,与上文“丧其耦”义同。(韩林合认为:“吾丧我”之“吾”指本体自我,“我”指经验自我。《虚己以游世》127页)。这里南郭子綦“仰天而嘘”,就是庄子说过导引之士练功时的“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即修习吐纳或行气导引之术。他在行气导引中达到“吾丧我”的境界,也就是“坐忘”的境界。
相似文字还有: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 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天运)
“何规”意为如何正修(自己)。孔子描述他所见的老聃像是“合而成体,散而成章”的龙。“章”意即文采焕烂。老聃“乘乎云气而养(翔)乎阴阳”的状况,就是处于行气导引的境界之中。孔子惊讶得张口不能闭合(嗋)。子贡(赐)所谓“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成玄英疏:“圣人寂同死尸寂泊,动类飞龙在天。”这里的“尸居”与以上“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应该义同。“发动”意为奋发机动。所以,处于行气导引之术中的老聃,其表象也是“吾丧我”“忘我”的状况。下面的描述则更加直接: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沬,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 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谓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田子方)
孔子去见老聃,老聃刚沐浴(沬),披着头发(被发),安静不动(慹)不像是个人(非人),这也是上文所谓“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之状。孔子便隐身在屏风后面等待。一会儿出来见老聃(少焉见),孔子忽然头晕目眩,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老聃形体特别(掘)如槁木,遗弃万物不像人形(离人),冥于独化之状。便向老聃请问为何如此。老聃说,他正游心于无物之际(物之初)。孔子问是何意。老聃说心被干预因此不能感知,口开不能合(辟)因此不能说话。所谓“游于物之初”,实际就是在做行气导引。(参见拙文《庄子究竟怎样“游”?》)
可见,《庄子》中的得道者,在做行气导引之术时,其外在呈现的表象都具有“离形去知”“吾丧我”“忘我”的状况。
庄子认为,“离形去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婴儿状况:
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庚桑楚)
这是《庄子》中的老子与南荣趎(寓言人物)说的话。婴儿动的时候不知所为,行走不知所去之处,身体如同槁木之枝而心如死灰。如这样,祸亦不至,福亦不来。这里关于婴儿之论,与《老子》有关论述内容高度一致。《老子》云:“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五十五章)《老子》所述非常明确,“专气致柔”达到婴儿的状态,就是修炼气的极致境界。可见,通过调息吐纳、修炼气的功法,来体悟甚或得道,是《老子》和《庄子》的一个共同思想。
更多的“离形去知”之状,是人在这种状况之下近似乎动物。《庄子》中关于得道者行气导引的这种状况有很多具体描述。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岀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应帝王)
许由的老师是啮缺,啮缺的老师是王倪,王倪的老师是蒲衣。他们皆为得道高人。“四问”事见《齐物论》篇,一问物是否所同,二问有何不知,三问物是否无知,四问至人是否不知利害。蒲衣子说,舜(有虞氏)不如伏羲(泰氏)。舜藏匿仁义试图获取百姓之心(要人)。虽然他得到了人心(得人),但是他还没有达到与物混同为一(未始出于非人)。伏羲安然卧睡(徐徐),无知自得(于于)。忘物我是非,或马或牛(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随人呼召,与牛马混同为一。但是,他也没有完全等同于物(未始入于非人)。庄子的玄妙之意在于:人既要与物混同,但也不能完全变成动物。可见这些得道高人在行气状况之中,几乎是非人亦非物。他们的故事还有:
啮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啮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知北游)
“被衣”即是“蒲衣”。被衣说啮缺:端正你的形貌,纯一你的视觉,自然之和(天和)就会到来;收摄你的智慧,纯一你的外形(度),精神就会自来身上。美德将会装饰你,你会居于道,你就像初生之犊(瞳),天性纯一,常保自然之性(无求其故)。他的话还没说完,啮缺已经熟睡了(睡寐)。被衣大喜,唱着歌走了,说:啮缺“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本真自然,不以巧故自持(真其实知),浑浑沌沌(媒媒晦晦),不用任何心思与人交往。在这里,啮缺既有“新生之犊”之状,也有“形若槁骸,心若死灰”之状,也就是“离形去知”之状。
这种状况同样发生在老子身上:
士成绮明日复见,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郄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圣之人,吾自以为脱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茍有其实,人与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天道)
士成绮(寓言人物)说,他昨天讥刺(刺)了老子,今天感到心里在矫正嫌隙(正郄),不知何故。老子说,我自以为早已超脱了(脱)所谓聪明神圣之人这些外在名誉称谓之心(含义是你居然还这样称呼我,也是我的道行不够)。你称呼我牛马我就是牛马。如果真以为自己有圣人之遗迹,别人给以美誉而不接受,那就要有灾祸(殃)降临。我安心而行,而不勉强行之(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这里老子说“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与“离形去知”在本质上也属于一类。
通过上述反复论证,可以断定“坐忘”就是行气导引之术。“心斋”与“坐忘”一样,其外在表象和特征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离形去知”“非人”“吾丧我”,其最高境界是“婴儿”和“初生之犊”。
3
“心斋”“坐忘”是一种行气导引之术,上述论证应该是坚实的。
冯友兰先生认为:“所谓‘心斋’、‘坐忘’,皆主除去思虑知识,使心虚而‘同于大通’,在此情形中所有之经验,即纯粹经验也。”(《中国哲学史》301页)后期他又说:“‘坐忘’的方法是靠否定知识中的一切分别,把它们都‘忘’了,以达到心理上的混沌状态。”(新编第二卷122页)这个界定否定了前期的说法,比较接近庄子的思想。但总而言之,“心斋”“坐忘”是用日常经验无法解释的。冯先生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庄子所谓的“斋”与“心斋”、“忘”与“坐忘”之间,具有本质的界限。“忘”是一般人所具有的正常心智功能。在斋戒中人们也宁静心神,暂时超脱世俗事务,可以达到一般的“忘”的境界。但是,“心斋”“坐忘”则只能是行气导引之术,是人们日常经验无法达到的境界。当然,在庄子那里,二者之间也有集合部。这个看法我们可以从《庄子》中得到佐证。
庄子也说到“忘”的功能。他说起过很多高明的能工巧匠,都具有“忘”的特点:
工陲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甞不适者,忘适之适也。(达生)
“工倕”为传说尧时巧匠。工倕以手指旋转,随便画圈(旋),就能合乎规矩(盖规矩),不需要用心算(稽)。这表明他心灵(灵台)专一没有桎梏。同样道理,鞋子适合就忘记了脚;裤带适合就忘记了腰(要);心灵舒适就忘记是非;心里没有事(不内变),不操心外在世界(不外从),处理世间事务(事会)就顺心如意。而本性对于事务自然适应,那就是更高的境界“忘适之适”。
另外,《庄子》中一些身怀绝技之人,也具有“忘”的本领:
颜渊问仲尼曰:“吾甞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甞见舟而便操之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甞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 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达生)
颜渊渡(济)河(觞深之渊),很惊讶摆渡船工(津人)的高超技术。于是问是否能向他学习操船技艺。摆渡工说,会游泳者就能够快速学会(数能)。假若是能潜水的人(没人),虽然从来未见过船,但上船便能操造。颜渊再问为何,摆渡工不说。于是,颜渊便问孔子。孔子说,会游泳的人就忘记水了。会潜水的人视深渊如同山陵,视水中翻船如同地上行车倒了一般,是平常事,不会淹死人。如此这样,心中没有惧怕的念头,所以心安神定。就像赌博的时候,用不值钱的东西(瓦器)下注,心里无所谓输赢,故而能巧中。如果以银铜打造的钩带做赌注时,则心中就惧怕了。而以黄金做赌注时,心生怖惧,反而心智昏乱而不中。因此,看重外物,内心就笨拙了。这里的“忘”是指忘掉利害得失。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忘”就是得“道”。当然,这是“庖丁解牛”中庖丁所谓“进乎技”的“道”:
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马曰:“子巧与? 有道与?”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者乎!”(知北游)
大司马家锻打腰带钩的工匠,八十岁了,所锻造的腰带钩没有一丝一毫(豪芒)的差错。他自称有道(守),即“于物无视,非钩无察”。之所以至老而仍然得其捶钩之法,全靠对于其他事物不用心视察(忘)之故。这里的“无不用者”意指道。
《庄子》描述的这些专业高人在工作时的共同特点,就是专心专一,忘掉利害得失,甚至“忘我”。当然,这几个高人所达到的“忘”的境界,还是属于一般的日常经验层面。有些工艺大师的“忘”则与行气相关,他们的境界应该是在“忘”与“坐忘”的集合部。例如: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 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甞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驱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达生)
“鐻”是一种乐器。陆德明《释文》引司马彪注,认为类似夹钟。“齐”繁体字“齊”,同“斋”,即斋戒。梓庆制作乐器之技的根本,是“未尝敢以耗气”。而“齐(斋戒)以静心”就是养气,最后也是达到“忘吾有四枝形体”的境界。这实际上已经接近“心斋”“坐忘”了。但是,梓庆还没有与牛马混同,成为“非人”。因此,他所达到的这个境界,是一般日常经验的“斋”“忘”与真正行气导引之术“心斋”“坐忘”之间的集合部。
可见在《庄子》中,不仅一些寓技于道之士,他们的技艺与凝神静气的“忘”有关,还有一些顶级的工艺大师们,能够行气导引,进入到接近“心斋”“坐忘”的状况之中。由此可见,“心斋”“坐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某种技艺的极致状态。由此,我们不禁看到庄子关于“心斋”“坐忘”概念的巨大思想张力。
从庄子气论角度说,行气导引之术所有人得道的必经之路。按照行气修炼的不同“果位”,得道者最高的一类是《庄子》中的至人、真人、神人、圣人,例如邈姑射山上的仙子、西王母等。在《庄子》三十三篇之中,几乎每一篇都有对于这些人的描述,常常浓墨重彩。他们是庄子的最高理想人格,几乎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凡夫俗子望尘莫及。其次一类是由“心斋”“坐忘”方法得道者,例如南伯子綦、啮缺、蒲衣、王倪等人。他们虽然是脱俗超凡奇特之人,但也是生活在世俗凡尘之中,为常人所闻所见所触,甚至能和他们一起所处。这种现实世界的楷模对于人们的榜样力量是巨大的。第三类是庄子描述的身怀绝技的巨匠大师们,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行气导引之术,接近“心斋”“坐忘”的境界,例如梓庆等。他们得道的境界不在神仙世界,而就在人间现实社会,是一种高妙的内心体验和人生境界,可以达到“至乐”。
另一方面,从现实的角度说,庄子认为,人们要在乱世全生,关键在于淡漠无为,心灵安宁。实现心灵的安宁,最关键的就是彻底忘记世俗的价值和事务,甚至关闭所有感官的功能。而能够实现这一目的,则只有通过行气修炼的功法才能达到。因此,“心斋”“坐忘”也是现实世界人们自我救赎的有效手段。而且,在庄子描述的三类得道者之间也有过渡者,例如“御风而行”的列子是处于第一类仙人和第二类得道高人之间;梓庆则是处于第二类与第三类能工巧匠之间;而“捶钩者”“工锤”“津人”等,则是处于第三类与普通人之间。可见,庄子倡导的行气导引之术的得道受益者,形成了一个从神仙到人间的阶梯。神和人通过这个阶梯在逻辑上被打通了关隘,勾连起来。这个阶梯也展示出每个个体在乱世生存的可行途径和思考逻辑。可见庄子的“心斋”“坐忘”思想也具有现实意义,与庄子的社会关切具有内在联系。从对于庄子“心斋”“坐忘”内在思路和深层思想的上述推论,让我们不能不感叹,庄子的思想不仅深邃,其内在逻辑和结构也十分美妙,令人叫绝!
庄子的“游”是行气导引之术,“坐忘”“心斋”也是行气导引之术。虽然气论是庄子的重要思想之一,也与道论相关,但如果全部《庄子》只讨论气的问题,庄子最多就是气功大师,或气论思想家。其实,庄子还有很多关于世界、社会、伦理、知识的深刻思考,涉及哲学形上学、存在论、伦理学、知识论等。而且,他的这些思考和论述,完全可以与柏拉图媲美,不仅是先秦中国哲学的高峰,即使在当代,也是哲学界很少人能够企及的制高点。
(本文所有《庄子》引文出自章启群《庄子新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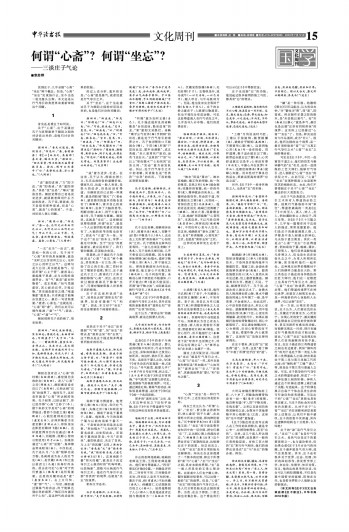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