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日前当选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是迄今中国学界唯一入选该院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本报特邀朱雁飞博士对李雪涛院士进行了专访。
1
朱雁飞:李教授,首先祝贺您当选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德国国家科学院是一个怎样的机构? 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达到何等的成就才能成为其院士?
李雪涛:德国国家科学院的德文名称为National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Leopoldina,源于1652年始创的利奥波德科学院,是世界上延续至今的最古老的科学院,也是德国最古老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的联合会。它最初是以后来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利奥波德一世(1640-1705)命名的,这位皇帝在位时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在东部成功地抵挡住了奥斯曼帝国的进攻,同时在西部抵抗住了法王路易十四的霸权。
德国国家科学院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其创始原则,根据不同的研究领域,共设立了四个学部28个学科组,总共拥有1500多位院士,分别来自自然科学、医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其中约有四分之三的院士来自德国本土和其他德语国家(奥地利、瑞士),另外约四分之一来自世界其他国家。
德国国家科学院具有独立性和学术性两大特点,其院士的选举过程基于严格的卓越学术标准。首先从提名候选人开始。提名有两种方式:由该院学科组或主席团任命的成员遴选委员会进行提名,经学科组、学部以及主席团三轮选举后产生,最终结果由科学院主席直接写信告知新当选的院士。候选人须以书面形式同意接受院士资格并承诺为科学和学术事业尽职尽责,选举程序至此告一段落。我此次当选,被归在第四学部的第23学科组,即“科学史和医学史”学科组。
截至2022年年底,德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中有187位获得过诺贝尔奖,拥有过歌德(1749-1832,植物学学部)、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自然研究者学部)、达尔文(1809-1882,自然研究者学部)、玛丽·居里(1867-1934,物理学学部)、西门子(1816-1892,物理学学部)、玻尔(1885-1962,物理学学部)、海森堡(1901-1976,物理学学部)、爱因斯坦(1879-1955,物理学学部,但在纳粹时期院士资格被取消)、普朗克(1858-1947,物理学学部)等巨擘。能够忝列这些享誉全球的科学和人文巨匠中间,我倍感荣幸。
其实早在2011年3月,我就曾到过访位于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勒河畔哈雷的德国国家科学院,并在那里用德文做过一场题为“轴心时代与中国的互动”(Die Achsenzeit und China: wechselseitige Wirkun⁃gen)的公开演讲——至今我办公室里还挂着这次演讲的海报呢。自此以后每一年我都参加在那里举办的有关知识迁移史研究的会议。2014年10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成立前夕,我们同德国国家科学院在哈雷共同举办了题为“欧洲、日本与中国的知识迁移与现代化进程”(Wissensau⁃stausch und Modernisierungsprozesse zwischen Europa, Japan und China)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从这一点来看,我所在的研究院早在十多年前,就与德国国家科学院有着密切的学术往来了。
朱雁飞:再次祝贺您! 您在全球史、德国汉学史、德国现代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学术史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和论文。在这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究中,您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什么?
李雪涛: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和关系。为什么一种文明能够融入到另一种文明形态,以及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我时常思考的问题。我主要通过以下四个维度来予以探讨:一、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的实存哲学和历史哲学为中心的德国现代哲学研究;二、以佛典汉译为中心的佛教史研究;三、以德语世界汉学史为中心的中国学术史研究;四、以知识迁移史为中心的近代中外互动研究。这些研究领域涉及文明的碰撞和互动,是解读中华文化的重要路径。
对于中外文明之间的融合和关系,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如何以非中国的方式连接其他文明与华夏文明。以佛教为例,中国的佛学绝非印度佛学的单纯的移植,而是“嫁接”,是印度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个“嫁接”的过程中,我们如何以非中国的方式将印度哲学中的超越观念与儒家学说中的内在线索连接在一起,从而摆脱中国历史思维的定式,进入跨文化的全球场域?
2
朱雁飞:佛教起源于印度,经过了一千多年的适应化过程,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如何理解您所说的中国佛教的“嫁接”?
李雪涛:是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将佛陀与黄帝、老子一并祭祀,并且将佛教的咒术看成是神仙道的神秘力量。到了公元4世纪,人们开始用以老庄之“无”的思想解释佛教之“空”的“格义”的方式来理解印度的学说。直到5世纪,从龟兹到长安的鸠摩罗什(344-413)创立了中国佛教的术语体系,才奠定了中国佛教的基础。之后的中国佛教学者们开始关注义理本身。在发现了从印度和中亚传来的佛教各经论的内容相互矛盾之后,中国佛教僧侣们开始运用自己的智慧来重新评估各种佛教的学说,这便是所谓的“教相判释”。由此便进入了形成中国佛教宗派的新的文化创造阶段。而佛教和中国传统思想、历史社会不断地对立、抗争、调和、融合之后,也逐渐产生了儒释道三教合一说。
中国是以自身的语文将发生于印度的佛教传译和接纳过来的。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来自印度和西域的高僧,以及汉人中的佛教学者共同努力、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出生于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各宗的弟子们,均将这些汉译的佛典奉为佛陀的教说,以此组织成独特的教义,终于完成了以汉传佛教为基础的大乘佛教。我的德文专书《宋僧赞宁(919-1001)对佛典汉译理论与实践的洞见》(DieÜbertragung buddhistischer Sutren ins Chinesische: Theorie und Praxis.Am Beispiel von Zanning[919-1001])2019年由德国的东亚出版社与我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在这本专书中,我研究了中国历史上佛典汉译的具体实例,并从中得出结论:佛教进入中国及其与中国文化间的碰撞、融合,是解读中国性的重要路径,同时这也构成了两种文明共同问题的关键媒介,能够使两种文化的历史资源进入互为批判的动态关系之中。中国佛教在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跨文化宗教的潜力。
朱雁飞:您于2021年出版了中文版的专书《雅斯贝尔斯与中国》。不论是雅斯贝尔斯与中国的事实影响,还是他通过中国而获得跨文化视野,进而构建出自己的学说,您都进行了精彩的解读。在此之前,您还翻译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您能解释一下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概念吗?
李雪涛: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轴心时代(Achsenzeit)是一个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至今依旧信仰的世界宗教的时代”。这位哲学家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开头便使用了这个由他自创的概念,来展示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雄心。他借此描述的并不是某一历史事件,而是人类历史上的精神“突破”(Durchbruch):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在相互之间没有影响的情况下,非凡的事件似乎都集中发生在世界上的几大地区:在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全部流派都相继产生;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佛陀也生活在这一时代;在伊朗,查拉图斯特拉认为宇宙的过程就是善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众多的先知;在希腊则生活着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的诗人、哲学家和学者。正是在这个时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意识到其自身的种种限制,他们体验到了世界的恐怖以及自身的无能为力。在面向深渊之时,他们极力寻求着解脱与救赎,并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在意识到自我的种种限制时,他们为自己设置了最高的目标。在自我的深处以及超验的明晰中,人们第一次体验到了绝对。超验性的思维在不同的轴心文明地区塑造了不同的观念:在中国出现了“道”,在印度开始讨论“梵天”(Brahman),而古希腊的哲人不断在探讨“逻各斯”(Logos)的内涵。
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文明之梳理,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印度和希腊三种文明是以何种方式达到“统摄”(das Umgreifende)的。而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在达至终极真理的方式方面给予了雅斯贝尔斯极大的启发。如果没有中国思想的参与,“轴心时代”这一概念是否会出现,是值得商榷的。反过来,正是借助于作为存在哲学大师的雅斯贝尔斯的复述,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才变得鲜活起来,从而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实际上,中国是雅斯贝尔斯寻求世界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通过对世界不同文明发展进程的探寻来思考和揭示人性存在的现状,进一步发现共同的起源和未来,从而为他的世界哲学理念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基础。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世界历史在不同的轴心文明地区实现突破,这一点有力反证了西方历史学家特别明显的“声称唯有我掌握真理”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可以借助于轴心时代而在他者之中认识自身,从而意识到相互理解的可能性,以及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多样性乃至今天所谓的跨文化对于雅斯贝尔斯的意义。轴心时代学说的意义重大,在于它重新确定了西方学术研究的方向,换句话说,为战后西方学术研究的重新定位奠定了基础。由于雅斯贝尔斯在纳粹德国的特殊经历,这一理论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罪行为背景,包含着强烈的规范性要求。因此,雅斯贝尔斯在运用这一概念的时候不仅要解释历史的发展,而且还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坚信,其中的一个教训就是要采取一种新的路径来理解历史。“普遍历史的语言”必须避免“排他主义”这一人类曾经遭受过的“西方灾难”。
3
朱雁飞:您曾经在德国留学并获得了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请问留德经历对于您的学术研究有哪些影响?
李雪涛:198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德语,那时我认为,所有的德国人要么是哲学家,要么是诗人。你可以想象得到,到了德国之后,当我看到大多数德国人跟我们一样时,有多么失望!
我曾经在三所德国大学——马堡大学、杜塞尔多夫大学和波恩大学——工作和学习。说实在的,在德国的学习和工作塑造了今天的我。当时,任何一位想在德国大学读学位(那时并没有Bachlor,只有Magister或Diplom)的学生,都需要选择一门主专业(Hauptfach)和两门副专业(Nebenfächer)。这对于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来讲是极具挑战性的。我当时选了汉学作为主专业,日本学和比较宗教学作为副专业,但后来因为日本学需要提供在中国大学的日语成绩单,所以我又换成了日耳曼学(Germanistk)。即便是在汉学系里面,有一些课程对我来讲也是完全陌生的,例如葛莲(Dorothee Kehren)博士开设的东亚艺术史课程,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开设的中医古汉语课程等,这些课程对我整体理解中国文化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前些年我做过有关中国艺术教育家滕固(1901-1941)在柏林大学的留学研究,也做过有关宋元时代的禅宗画家牧溪(13世纪)的《六柿图》研究,这些其实都是受到了东亚艺术史课程的影响。此外,在方法论上,我学会了陈寅恪所谓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和“精确性”(Genauigkeit),这要归功于德国大学研讨班(Seminar)的作业(Referat)要求。我回国后参加学生的论文答辩,发现很多学生只是在做一个历史题目,而缺乏问题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不懂得什么是Fragestellung(提出问题),至于如何将研究目标与当前的学术研究状况、所选择的方法和当前的范式联系起来,对当时大多数学生来讲,更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朱雁飞:德语世界汉学史是您的深耕领域之一。作为德国汉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在这个领域所从事的工作和研究成果?
李雪涛:汉学史是我2004年从波恩回到北京后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尽管德语世界汉学家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但他们的学术传统、立场和方法与中国学者完全不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德语世界汉学家们以其独特的语文学传统,对中国哲学、文学、历史、艺术史等学科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2008年,我的专书《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这是基于一手的德文文献和档案所做的系统研究,而不是转述或综述。六年后,即2014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在这本著作中,我提出了“汉学学术史”的观点,并为汉学研究提供了诠释学的哲学基础。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何乏笔(Fa⁃bian Heubel)研究员也同意我借由汉学史来反省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处境的观点,并且指出:“汉语学界应当接续民国以来所累积的文化资源,从而与当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发展趋势产生创造性的互动。”
2018年,我编了一个读本《东亚研究与全球史建构:德语东亚文化史的几个研究路径》,主要收录了有我翻译的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余凯思(Klaus Mühlhahn)、戴默尔(Walter Demel)、吕森(Jörn Rüsen)等德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的重要相关文章,从中可以看到,由中国乃至东亚史建构起来的世界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西方学者反思自我、反思历史的一种重要视角。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进程中,作为殖民主义产物的民族志学、人类学,在经历解构之后,文化上的他者、异族不再是被征服的对象,或是与动物并列的研究客体了,而是获得了重要的建构意义。实际上,东亚地区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贡献极大。这些研究的成果对于构建欧洲的“世界史”都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在德语世界汉学研究方面,一个具体的实例是顾彬教授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第八卷《中国文学德译书目》(Bibliographie zu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in deutscher Sprache,2021)。在这一卷中,我依据目录学的方法,辑录了663页的书目,系统收录了从1980年至2020年四十年间德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书目,具体分类为:中国古代文学作者目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目录、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目录以及中国文学作品选集和研究。
4
朱雁飞:您在2021年还出版了两卷本的《德国汉学研究史稿》专书,对德国汉学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您能否概括介绍一下这部专书的内容和特点?
李雪涛:这部专书分为“分期与书目”“语言、文学与翻译”“范式与机构”“互动与批判”和“专史与回顾”五个部分。其特点大致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跨文化的比较视野:因为德国汉学的研究主体是德国学者,而他们研究的对象又是中国乃至东亚,因此德国汉学家们已经具备了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他们的知识构成也很难归于某一种文化,因此不论德国汉学家的“汉学研究”还是这些“汉学史再研究”,都力图打破国家的界限,实现跨民族、跨文化等的比较历史研究观照;二、整体观:将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历史置于更加广阔的相互关系的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避免由于关注细枝末节而错失对历史的整体观察;三、互动观:将德国汉学研究史置于中-德乃至亚-欧的动态交往的网络体系中加以理解;四、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论:正是在对中国历史的构建中,德国历史学家渐渐开始从思想观念、研究视角、历史叙述等层面反思进而解构西方中心论。面对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包括莱布尼茨(1646-1716)在内的德国哲学家都不断地思考如何摆脱狭隘的地方主义,并由此出发超越各种地方中心论的思想;五、跨学科的方法的运用:德国汉学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今天对它的历史梳理,也必然是在历史学、语文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参与下进行的,这同时也体现了德国汉学史研究的活力和多样性。
朱雁飞:从2008年的《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到最近出版的《德国汉学研究史稿》,可以看出您从最初的“内部论”(internalist)或“谱系式”(genealogical)的历史思考方式,转变为将德国汉学研究的现象、事件与进程置于“全球脉络”中予以分析,从而形成了一种真正的跨文化全球史研究。这些著作为德国汉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那么您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李雪涛:其实,一直以来我所做的研究都可以归在“跨文化研究”的范畴。现在依然活跃在学术界的德国当代哲学家威尔士(Wolfgang Welsch,1946-)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跨文化性”(Transkulturalität)的概念,相对于前现代社会的同质性和单一性,他将现代社会理解为结构上的异质性和混合性。他认为,文化并不是作为可以相互划分的单位而存在的,而是将外来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相互交错和融合而形成的动态实体,由于历史或文化间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根据这样的“跨文化性”,我们时代的文化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联系的。当代人的身份特征是他们结合了不同文化渊源元素的集合体。因此,今天的个人本身就是跨文化的。这不仅适用于移民,而且越来越适用于每一个个体。跨文化身份的优点是比老式的、单一的身份更容易沟通和连接,因为它们之间通常有重叠,能够实现最初的相互理解,并在随后的沟通中不断扩展。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1881-1969)在1940年创造了一个术语“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用来描述文化的融合和交汇现象。“文化互化”跟其他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融合了以往的概念,特别强调随之而来的创造新的文化现象(新文化)的想法,其中“互化”被理解为产生全新的东西。
最近我读到日本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一段话:“今后的日本文化不是与其他民族根本对立意义上的独自的文化,不是像过去那样从异民族取来文物并使之日本化所形成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在日本的独自的显现。……认为日本文化完成于过去,并力求保持下去的心理……是以朝气蓬勃创造日本未来文化的现代日本人必须首先排斥的。”尽管津田的这句话写于20世纪30年代,但今天看来依然没有过时。我认为中国文化也不能预设一个早已完成了的主体性。它是在与外来文化或者他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显现出来。主体性是生成性的、动态的,是今天依然需要我们进行创造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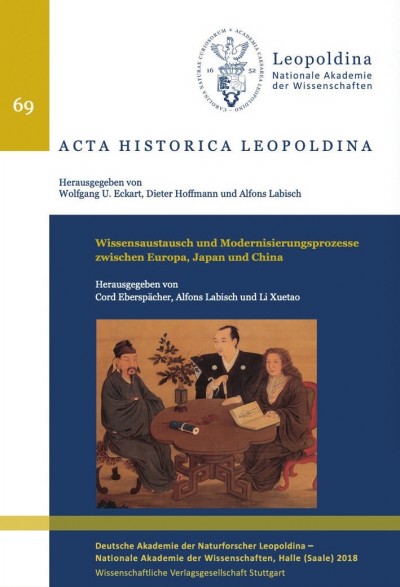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