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精品文学品牌“故乡·童年 原创儿童文学书系”再添新作——《钟鼓楼下》。这是一部充满人情味、烟火气、趣味性的京味小说,作者金少凡是北京老舍文学院作家、老舍研究学者。他以原汁原味、醇厚地道的京腔京韵,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末期胡同里的生活图景和民俗风情,还原了作者记忆深处那些温暖人心、趣味盎然的童年故事。
作品主要围绕老北京钟鼓楼下的张旺儿胡同展开。张旺儿胡同里杂居着的六七户操各式行当的普通人家:房东耿三儿以收房租为生,为人本分、仁义;东屋的谭先生是小学老师,知书达理,虽然柔弱谦和,但在危急时刻毅然挺身而出;孙师傅是钟鼓楼这一片乃至北京四九城里最好的锔锅匠,凡是摔碎打碎了的东西,在他手上都能完美复原;南屋无儿无女的沈师傅擅长捏泥人,在钟鼓楼下摆摊子,辛苦度日;阔家少爷三当家的整天提笼架鸟,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北屋刘宝泰家的四个儿子调皮捣蛋,惹出不少麻烦事儿……
“我”、小山子、小芬和四个水子等孩子的童年生活也别有一番风趣:斗蛐蛐、看戏、学艺、摔跤、抓虾喂鱼、玩油葫芦……虽然处在一个物资生活贫瘠、国家动荡的年代,但大家苦中作乐、互帮互助,将饥寒交迫、战乱频仍的岁月过成了一首诗。这些琐碎庸常的生活经过一个孩子好奇的目光打量之后,呈现出了一种平淡、从容、厚道、豁达的气象。
作品还系统地梳理了北京的人文历史,介绍了建筑、民俗、曲艺、美食、童谣等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传统文化,再现了评书、葡萄工艺品、逛笼等非遗项目的历史风貌,也重现了窝脖儿、捏泥匠、锔锅匠、剃头匠等老北京民间艺人的生活情态,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吃喝玩乐到营生忙活,作品中凝聚着大量丰富生动的细节描摹,就像一张老北京文化地图,在泛出北京人特有的生活质感的同时,也折射出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
作为在钟鼓楼下长大,已将那座美丽都城的每一缕炊烟、每一声叫卖、每一种味道都镶嵌进记忆里的老北京人来说,像叙述自己的母亲一样去写作老北京的故事,似乎是一件再符合逻辑不过的事情了。可以说,这部关于老北京的儿童小说,已经将历史文化的元素蕴藏于字里行间,在小人物们的喜怒哀乐之中,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老北京民风民俗的瑰丽画卷。展卷阅读,仿佛有一位“老北京人”在耳畔亲切地絮叨,让我们身临其境般在小胡同里行走,感受孩童成长中的喜怒哀乐,了解北京的风土人情与历史文化,在轻松调侃、幽默风趣的语言表达中,往日里的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那些感动与温暖,便随着胡同儿里的光影淌入每一位读者的心中。
窝脖儿
我正要跟小山子出去找谭先生请教事情,忽然听见院儿门外响起了咕咚咕咚的脚步声。
定睛一瞅,先瞅见了一溜儿移动着的家具,由胡同里,逐渐地移动到了院儿内。有柜子,有箱子,有桌子板凳,还有一对儿老高的大瓶胆,之后才发现了家具下面的人。
“窝脖儿!”小山子喊了一声,就跑了出去。
我也跟着他跑出去瞧热闹。
“窝脖儿”是老北京的“搬家公司”。之所以被称作“窝脖儿”,是因为他们在搬东西时,无论大件小件,无论是轻是重,无论木质、石质乃至瓷器,一律是扛在脖颈子上,这样一来走路时就须得哈着腰窝着脖子,久而久之,脖子上就磨出了茧子。茧子越增越厚,越长越高,于是脖颈子上头,就留存下一个厚厚的肉球。
是新房客搬过来了。
那天耿三儿收取房租时就是带着他来看的房子。
新房客姓孙,赁了一间东屋,和谭先生做街壁儿。
家具都移动到了院子里。“窝脖儿”们用一根木棒在身后把家具支住了,从腰间抽出灰不溜秋的手巾来擦汗,大口地喘气。
“您哪位是孙师傅?”领头儿的“窝脖儿”斜侧着,抬起头来朝东屋喊问。
新房客赶紧迎上去,说:“我我,敝人贱姓孙。师傅您受累了,请您把东西往屋里头放吧。”说着就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
领头儿的“窝脖儿”便走到东屋的房门口。
我们要瞅的就是他。
他的身后头,背着一个特殊的物件。那物件正吱吱作响,还呼噜呼噜地冒着蒸汽!
领头儿的“窝脖儿”来到东屋的门
口后,便绷着浑身的肌肉,把身子直着慢慢地下蹲,再下蹲,直至自己的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后背上背着的那样特殊的物件,在吱吱的响声中,被很轻巧很稳当地平撂在了地面上。
那是一只着着火的煤火炉子,上面还坐着一把开水壶!
这是“窝脖儿”行的规矩。领头儿的为了展示搬家的背负功夫,要把主家着着火的炉子背起来,上头再坐上一壶水,一路上,要行得平,走得稳。到地界了,炉子不仅不能灭,水壶当中的水不能洒,而且水还要一路开着吱吱地冒着蒸汽。同时这也是主家在讨吉利,火不灭,水不洒,开水冒蒸汽,预示着新家新生活美满幸福。
我跟小山子忙凑近了那炉子。
新房客孙师傅站在了我俩旁边,他先给“窝脖儿”作了个揖,之后瞅瞅炉子,提拉提拉水壶,见火旺旺儿的,
水一滴没洒,蒸汽弥漫,相当满意,就又拱手称谢。
“窝脖儿”头儿就伸手在自己个儿脖颈子上厚厚大肉包的茧子上抹了一把,然后接过孙师傅的酬劳。
孙掌柜的您搬家街坊邻居盼您发孙掌柜的您发财金银财宝往里抬孙掌柜的喜满堂金银财宝往里装大盆儿装了小盆儿装大碗儿装了小碗儿装盆儿盆儿碗儿碗儿装不完我们等着孙掌柜您的赏钱
忽然间,一帮孩子拿着合扇,唱着数来宝跑进了院儿。
新房客孙师傅喜笑颜开忙着支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零钱,朝着孩子们扔了过去。
唱喜歌的孩子们你争我抢。当然,我跟小山子也参与其中。为此,我俩的脑袋还碰撞到了一起,这让我的眼前冒起了一片金星。
院儿里一片热闹。
热闹了阵子,“窝脖儿”们走了,唱喜歌的孩子们也散了。我跟小山子正要回屋,这时候新房客孙师傅从东屋走了出来,身后头跟着一个小女孩儿。看身量儿,小女孩跟我们的年龄相仿。
新房客孙师傅在前,女孩在后。女孩手里头端着茶盘子。
“你叫和平?”“你叫小山子?”他笑吟吟地问我和小山子。
我俩赶紧点头。
“有劳你们,”新房客孙师傅说,“引见我们去各家各户拜访一下子,好不好?”
在我和小山子的带领下,孙师傅先敲开街壁儿谭先生的门,拱手,行礼,指引着女孩叫先生,之后又挨家挨户地走过去。
新房客孙师傅每到一家门口,都高拱手深作揖地说道:“叨扰您啦,新来乍到俩眼一抹黑,还请您往后多照应着。”之后便给女孩指认长辈,并按照大人们的年龄,刘叔儿、刘婶儿、沈大伯、沈大妈地称呼完毕。
女孩端着的茶盘子里放着芝麻糖。那天,我们全院儿的人,每人嘴里都充满了香喷喷、甜滋滋的芝麻糖味儿。
到了晚半晌儿,全院儿每一户人又都来到了新房客孙师傅家。自然,还是由我跟小山子支应在前,大家先在东屋门口高声喊一句:“孙师傅,给您道喜了!”之后,便端着一碗酱、一碗面、一瓢黄豆走进孙师傅家。
新房客孙师傅再次高拱手深作揖。
我妈也把墙柜打开,从一个小包袱里头掏出几大把花生来。花生是我姥姥头年从乡下带来的,特意嘱咐是给我当零嘴儿吃的。可是我妈一直把它台在墙柜里,不许我动。
我妈把花生放进一只大海碗里叫我端着。她见我不动,就剥开一个,把花生豆儿放进我嘴里,之后对我说:“走,咱们给新房客孙师傅家温锅去!”
(本文摘自《钟鼓楼下》,金少凡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3年4月第一版,定价:30.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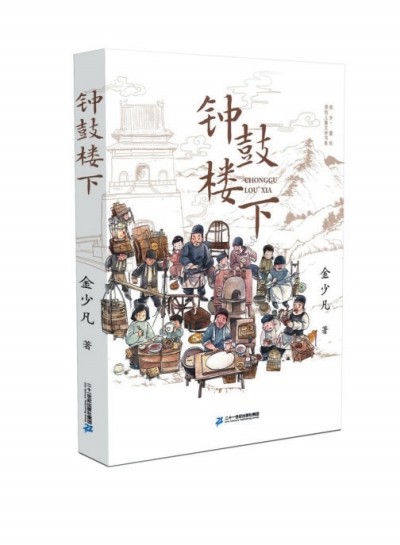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