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有个颇为壮观的图书资料室,里面排列整套整套开明书店印行的图书。李师东时常会去翻翻开明书店1926年到1953年的图书出版目录,揣摩开明人的初衷和用心,获得教益和启示。胡愈之、章锡琛、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唐锡光、傅彬然、钱君匋、王伯祥、宋云彬……这是在开明书店史册上光辉灿烂的名字,开明的传统是他们开创和存续的。
“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这是在开明书店工作了近20年的叶圣陶老先生谈到开明书店时的话。
多年后,他们的文化努力,依然是我们从事出版工作应该具备的底气和自信。
从1984年大学毕业至今,李师东在中青总社的院子里工作了40个年头。这与当时学校的分配有关,与他本人受益于中青总社出版的图书有关,更与他在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这个院子里受到的熏染有关。
在中青总社的东侧办公楼前有一棵玉兰树,每年开春,繁花似锦。后面是一排红豆杉,东南角是一座茶楼和一丛翠竹。这是25年前胡守文任中青总社社长时精心布置的。在院子东头北墙外,有一棵大树,每到深秋,树叶随风飘散,天地一片金亮。在这样的场景里做编辑出版工作,自然会觉出内心的丰饶和充盈。
院子里的人一茬接着一茬,但那些树、那些书,一直都在那里。这里的人和书和树,是文化出版的难得一景。后来者唯有勤谨不怠,尽其所能。
李师东说,小时候在农村,特别羡慕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当时觉得特别好奇,又特别神奇。人一辈子要做的事很多,几十年后回过头来看,把一件事做得问心无愧,已经很不容易。做编辑工作也一样,让好的东西更好,让更多人分享它的好,这就是一种高尚。
路遥在中青社的平房招待所住了一个来月,本来给《青年文学》写的《人生》,初稿14万字,《青年文学》容纳不了,只能转投《收获》
中华读书报: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就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您在什么机缘下去的《青年文学》?
李师东:1984年7月,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做编辑。文学编辑室在社里排序第二,俗称“二编室”,编辑出版当代文学读物、外国文学读物、文学知识读物。《青年文学》1982年创刊时,就是在文学编辑室。
历史上,“二编室”在中青社举足轻重:文学知识方面,《历代文选》《历代诗歌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等,影响很大;当代文学方面,“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等,至今大家耳熟能详;外国文学方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牛虻》等,更是影响了很多人。我在“二编室”编的就是文学知识方面的古典文学读物。
当时新时期文学浪潮翻滚,我一边编古典文学读物,一边在关注热火朝天的文学创作。1985年初夏的一天中午,在食堂排队买饭,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与中青社还未分家)儿童文学编辑室的编辑杨群(后来担任过国安足球队领队)问我:最近看没看到好的作品。他说的好作品自然是指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的。一个编古典文学的和一个编儿童文学的,都在关心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可见当时的文学氛围。我说:刚看了一篇,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写得非常好。还顺便做了一番评价。杨群说,你的看法很有特点,写成一篇文章给我。我就写了4000多字的评论《现实的无可选择与个人的表现情状》。文章很快就在《作品与争鸣》发表了。
那个时候,《青年文学》刚从文学编辑室分出来不久,得知“二编室”有一位青年编辑对当代文学很热心,担任小说组长的黄宾堂就找我,让我给陈染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写同期的“作品小析”。还没等“小析”发出来,10月下旬,兼任《青年文学》主编的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维玲在走廊里碰见我:小李呀,你这么喜欢当代文学,那你就去《青年文学》吧!
就这样,我别过我的师傅、当年的老“开明”李裕康主任,揣上几样办公用品,就去了《青年文学》编辑部。
中华读书报:您能描述一下到了《青年文学》以后的工作情形吗?
李师东:到了《青年文学》,发现这里的人比“二编室”的人还要年轻。陈浩增、赵日升也就40出头,詹少娟、马未都、李鸿飞30来岁,黄宾堂、李景章不到30岁,程丽梅和我同年,22岁,耿仁秋还小一岁,两位编务也和我们年龄相当。一个很年轻的集体,非常有朝气。
在编辑部里,大家遇到有争议的作品,会各抒己见,既专业又民主,意见一致了,就雷厉风行去做。看到好作品,大家相互传阅。1986年,我在《啄木鸟》第2期上读到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题材、人物、表述,让人耳目一新,连忙向编辑部推荐。大家读了都说好。马未都和王朔熟,有点委屈:好什么好! 我拿过来的几篇都被你们毙掉了。我在一旁敲边鼓:你就再拿一篇呗。不久,马未都真拿来了王朔的新中篇《橡皮人》。但篇幅很长,差不多要占一期的版面。
这一次的《青年文学》,就破例了,在1986年的第11、12期上分两期刊发了《橡皮人》。
年底正值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召开。按惯例全国青创会由中国作协和团中央共同举办,我们作为团中央的直属单位,自然也是参与者,与会人员人手两册《青年文学》,王朔受到的关注可想而知。1987年1月,我们还和《小说选刊》联合召开了王朔作品研讨会,我协助马未都请过一些评论家。
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新兵连》也类似。
路遥的《人生》,本来是给《青年文学》写的,他在中青社社内的平房招待所住了一个来月,结果把初稿写成了14万字。《青年文学》才5个印张,肯定发不了,后改由《收获》发表,中青社出单行本。
当时《青年文学》的专业氛围非常浓,大家一心想的是推出好作家、发表好作品,非常纯粹、投入。领导开明,编辑敬业,这是我当时感受到的《青年文学》的氛围。
1994年第3期开始,《青年文学》开辟了“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4年46期,推出了余华、苏童、迟子建、格非等55位60后作家82篇中短篇小说
中华读书报:1992年您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1994年《青年文学》推出“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您怎么想到这样一个说法?
李师东:我开始在《青年文学》做编辑,接触的都是60年代之前出生、比我年长的作者。我和他们打交道,自然留心我的同龄人有谁在写东西。那个时候,迟子建、程青、姚霏、陈染、孙惠芬等开始写的大多是校园生活和成长中的感受,俞杉、刘西鸿的短篇小说还获了全国奖。
80年代的编辑部里,总是人来人往,在京的、来京的文学朋友都喜欢上编辑部聊天。在全国人大研究室工作的评论家张兴劲有空也来。他是张炯的研究生。张先生当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兴劲协助研究会在编一份叫《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的内刊。一次我和他聊到:现在有一批很年轻的作者创作势头很好,他们都是60年代出生的,但还没有人去关注他们。张兴劲一听就有兴趣,让我写一篇关于这些青年作者的创作综述。这样,1987年第10期的该刊头题就是我写的《属于自己年纪的文学梦想一一1960年代出生作者小说创作述评》。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到了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程青的《那竹篱围隔的小院》、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孙惠芬的《变调》、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作品,并对他们的创作作了初步的归纳和分析。
进入90年代,60后作家已经形成规模和阵势。以余华、苏童、格非、北村、吕新为代表的先锋写作更是独树一帜,广受关注。我琢磨着,就60后作家这个话题好好写篇文章。
1992年春节前,学兄潘凯雄嘱我给广东作协主办的《当代文坛报》写稿,我结合在《青年文学》与青年作者打交道的切身感受和相应的思考,写了《第四茬作家群》一文,发在该刊1992年第1期上。我在这篇长文里,正式提出了“60年代出生作家群”这样一个说法,并从生活阅历、文学目的、创作心态、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青年文学》一直在关注青年作者的创作,在全力推出文学新人。60年代出生的作者,正是当时《青年文学》所要关注的创作群体。新任主编的黄宾堂非常支持新任副主编的我,所以从1994年第3期开始,我们就开辟了“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这一主打栏目,一直做到1997年年底,长达4年46期,一共推出了55位60后作家的82篇中短篇小说。不少作家成了当期的封面人物,如余华、苏童、迟子建、格非、徐坤、毕飞宇、邱华栋、范稳、关仁山、朱辉、麦家等,后来许春樵、叶弥、程青、何向阳、张执浩、红柯、祝勇、孙惠芬、洪治纲、凡一平等,也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重要作品,相继成为刊物的封面人物。60后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就这样走上了文学的前台。后来,大家对70后、80后作家就有了接续的关注。
中华读书报:回过头来看,您觉得60后与50后、70后乃至80后以后作家的代际差异,主要在哪里?30年过去了,60后作家是不是大多数都在坚持?
李师东:60后作家所以能成为一个特定创作群体,与50后、70后等形成代际差异,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解读,但都绕不开一个客观的社会现实依据:60后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走出校园、走进社会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始,正是60后走进社会之时。他们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同路人和参与者。正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塑造了60后的集体性格:他们对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进步尤为上心,也特别在意时代和社会对他们的内心触动。
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塑造了每一茬人走进社会后的生活内容和人生轨迹。
50后作家走进社会时,面对的是当时的社会动荡和青春蹉跎,所以在他们的创作中总会有一个人格化的“泛英雄”的形象存在,或隐或显,或深或浅,在努力证明自己。直到《人世间》里出现了主人公周秉昆,这位当年“上山下乡”中留在城里的小弟弟。他维系家庭的正常运转,正直善良,大情大义,被人们视为平民英雄。
70后走进社会,正赶上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认知失衡,让70后在创作的出口和归属上陷入迷茫和困顿。饶有意味的是,70年代初出生的魏微、丁天等紧随60后而文心早慧、崭露头角的作家,从此长时间失语。直到70年代末期出生的徐则臣、石一枫在新的时间节点上逐步找到内在的价值支撑。多年之后,70后的领军人物魏微终于写出了长篇小说《烟霞里》。这部小说,从1970年12月27日主人公田庄的出生之日写起,强烈的年代感,极具说服力。经过漫长的跋涉,70后正在用人生找回自己,证实自身的文学价值。
60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而成长成熟,他们中的写作者一旦确立了用写作与时代和社会相向同行后,就很少有人半途而废,文学创作从此如影随形。他们中的优秀者,已经成为中国文坛的中坚和实力人物。他们坚信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坚信自己做出的文学和人生的努力,这是这一茬人拥有的情怀和自信。
现在大家习惯说60后、70后、80后、等等后,其实,以出生年代划分作家群体,本来是文学的应急之词,冷不丁变成为社会习惯用语,这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代际划分从来不是严格的标准,而是现实的产物。直到目前,它仍不失为我们观察当下文学的一个角度,也是观察社会现实的一个角度。
一部作品生在作者,养在编辑,这是作者和编者之间的正常逻辑联系。对一部作品而言,作者和编者的关系就是“生”和“养”的关系
中华读书报:在长达近40年的编辑生涯中,您和作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你如何看待编辑在作家创作过程中的作用?
李师东:做编辑工作自然要和作者打交道,这是一门学问,要靠时间和经历。和知名的作者打交道,要有对话的能力和水平,你的意见和建议对他有帮助;对不知名的作者,则要有发现才华的眼光,要有成就才华的专业本事。作者都是从不知名到知名的,这里面有个人的修炼,也要有编辑的帮助。
做编辑工作,实际上是把作者的个人写作素材转化为共享的社会文化资源。编辑工作的要义在于转化,把作者的文稿形态转化为文化的传播形态。在这样的一个转化当中,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对文本的判断、对文稿的处理,组织策划,整体设计,宣传推广,乃至确定书名篇名、宣传导语,这都是编辑要做的事。一个称职的编辑,从职业化的专业角度,有条件更理性更全面地鉴定、评判一部作品的好坏优劣,能敏锐发现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缺陷或不足,会对作品的价值做出连作者也意想不到的淬炼和提升。能写出这样作品的作者,从来是把作品的编辑引为同道的。
表面上看,作者是把作品交给了杂志社、出版社,其实他是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出版机构里的他所信任的那一个人。
作者和编者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他对作品的发表或出版肯定是有期待的。作者对编辑工作的理解会因人而异。等到作品有影响了,大家看到的一定是作者的成功。版权发生变更了,编辑的原初贡献往往会被社会和行业所忽视。以至于人们会说,做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做编辑的人也会生出自我矮化的小编意识。
其实作者和编者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文化做事。
一部作品横空出世,是社会的合力使然,体现的是在一个特定情势之下包括编辑在内的有形或无形的智慧力量的汇集和凝聚、贡献和付出,如此这般,方才“万般宠爱于一身”。作家的传世作品,从来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作为,它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境况和这个时代人们的共同努力,因才情高迈而彰显其名,成为一个特定时段的文化表征。古来圣贤之书,它们的诞生和流传、误读和重读,正是因为历世历代作出的不断文化加持。
至于作者和编者到底是什么关系,这要从具体的作品说起。一部作品就是一株小树苗,它“生”在作者的苗圃里,必须要移植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去长大成材。移苗、培土、浇灌、整枝、杀菌,让它长成期望中的那么一棵树。这是编辑所要做的事。做这样一项工作,首先要喜欢去做,要有情怀和格局,会爱才识货,得有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喜欢它,悉心呵护它,让它长成大家心目中的一棵树,这就是“养”。一部作品生在作者,养在编辑,这是作者和编者之间的正常逻辑联系。对一部作品而言,作者和编者的关系就是“生”和“养”的关系。这样去理解编辑工作,才有可能把握文化出版的价值和要义。
中华读书报:您培养、发现了不少作者,有的还成了知名作家,您编的《人世间》大家都在读。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编辑心得?
李师东:作者和编者同在一个战壕,是相互成全、相互激励的,他们一起携手同力,在为文化做事。
人都是需要肯定和鼓励的。编辑也是人,同样需要鼓励和肯定。一个编辑的选题,今天被毙掉了,明天被毙掉了,时间一长,很可能他就找不到北了。相反,发现了编辑的某一特长、某个优势,进行耐心细致的引导,他很有可能会逐步形成自己的工作思路,会越做越有信心。这是我在工作中的实际感触。
对写作者来说,尤其是对正在爬坡过坎的写作者来说,来自编辑的支持和肯定,无疑是对作者写作自信的激发、唤醒和调动。
麦家在90年代初写过不错的短篇小说,后来几年里在公开出版物上没了踪影,1997年的五一,我们在成都见着了,几个月后他寄来了中篇小说《陈华南笔记本》,三两年后,他写成了长篇小说《解密》。前阵子麦家说,如果不是当时在成都见过一面,很可能就不写小说了。我说这只是一次缘分。如果没有那次见面,也会有其他的机缘等着他重新提笔。他注定是要写小说的。我起初说的是:1991年你在《青年文学》发的短篇小说,写得多好啊!好好写,写好了,我们安排上封面人物。
作者和编者的面对面接触,尤其重要。现在联系很便捷,但作者与编者还是需要更多的交流。面对面,人与人之间就会有一个气场,应答之中,能见出彼此的状态和心境、想法和看法,便于深入的了解和沟通。古人讲知人论世、将心比心,少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和设身处地。古人还说: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都是见了面才会有的效果。
我想到了1991年初春读刘醒龙中篇小说《威风凛凛》的情形。当时刘醒龙把这篇七万来字的小说写得密不透风,恨不得让自己的感受倾囊而出。我想找刘醒龙当面谈谈。当时我们并不认识。小说中哪些要省略,哪些要点到为止,哪些要有所加强,只有当面交换意见才会有效果。为一部中篇小说的修改,领导批准我专程去了一趟湖北黄冈。和刘醒龙见了面,沟通非常顺畅。作者显然意识到了编辑部和责任编辑对这部作品的重视。见了面,在沟通交流中就多了一份真切、一份信任,也多了一份情谊。《威风凛凛》刚发表,刘醒龙就寄来了另一部中篇小说《村支书》。在编发《村支书》时,刘醒龙寄来了另一部更上一个档次、后来成为刘醒龙成名作和代表作的《凤凰琴》。如果当初没有去一趟湖北黄冈,只是写一封信,提提修改意见,改好了发出来了,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了。刘醒龙会不会把后面的两个中篇接连寄来,不知道。他会不会去写《凤凰琴》不好说,但这部作品寄不寄给《青年文学》,那就难说了。
有彼此的熟悉和了解,有投缘和契合,有欣赏和信任,作者和编者就不是简单的工作关系了。如果作者和编者既是工作关系,又是朋友关系,那么作者的得意之作肯定会首先想到他的这位编辑朋友。我编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新中国极简史》、麦家的《解密》、胡松涛的《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梁晓声的《人世间》,都有同样的感触。
说到《人世间》,我写过好几篇文章,有一篇近万字的评论,还被《新华文摘》转载过。不能不写,因为由衷地喜欢,要让更多人知道。我和另一位责任编辑李钊平付出了我们应尽的努力,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更有赖于作者梁晓声的充分信任、总社皮钧社长的鼎力支持和全社的精诚协作。做成事,要靠天时、地利、人和。
中华读书报:您在出版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临近退休时在忙些什么?
李师东:作家徐坤说:搞文学的、做出版的,退不了休。我是临到退休更忙了。
2022年1月底,电视剧《人世间》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安排我全面负责《人世间》的生产印制和营销推广工作。春节前我们赶印了5万套,备好了10万套的用纸。电视剧一开播,线上线下一片添货声,最火爆的时候,京东、当当一天就能各自销出四五千套。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印务、营销的同事碰头,及时掌握和处理遇到的各种情况,保证生产和供应。赶上了疫情封控,在河北三河的库房进出不了货,在廊坊的纸盒厂做的封套也出不来,好在印厂是在北京市内。纸盒厂的同志真了不起,他们想方设法,倒了四趟车,终于把封套送到了印厂。入不了库怎么办,营销部门就直接安排在印厂打包发货,急中生智。我们还开展了“百城千店共读《人世间》”的线下销售和阅读征文,组织防盗打假,最多的时候,一天打掉了800多个盗版销售点。总社多次及时召开专题会,研究《人世间》的生产和营销,有力保障了《人世间》图书的效益最大化。去年一年,《人世间》一书的发货码洋就超过了1.2亿元。我们克服困难,做到了图书生产和销售没有一天断档,全社一起打了一场扎扎实实的硬仗。
最近一两年,我考虑更多的是中青图书的基础建设,组织了两套“文库”的出版工作。
一套是“新时代青少年成长文库”。这套文库收的是中小学生必读的经典图书,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向全国青少年推荐。我们的出版意图是向青少年提供放心可靠的版本和文本,现已出版图书50多种。
另一套是“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这是我们中青总社和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共同策划组织的一项工程。该文库已列入国家“十四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寻在新时代如何对广大部队官兵和全国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路径,我们明确了“用革命文物讲好英烈故事”的出版定位:重温民族复兴英雄史,打造新时代“红旗飘飘”。目前该文库已出版第一辑。
中华读书报:您退休以后,准备做些什么?
李师东:种完树,种菜去。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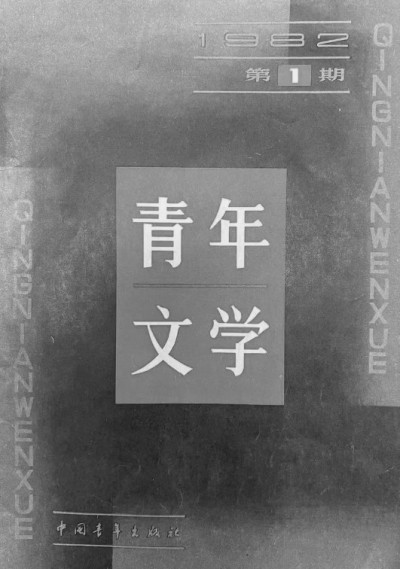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