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当出版社的编辑告知我决定要再版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一书,作为忝列末座的作者,除了心存感佩,不免有一种担心,我担心的是读者。三十多年过去了,孔子以三十年为一世,走过了一代人;除了代际更迭,社会环境也有所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虽然社会上开始关注传统文化,但热度不是太高;如今,传统文化热已经遍及华夏大地。这种情况下,像《中国儒学思想史》这类书,是否还会引起读者关注、在推动传统文化研究深入的过程中添砖加瓦?
当把全书再浏览一遍,上面的那些顾虑竟涣然冰释。这是因为,书中对儒学思想发展的主体看法,基本上经受住了历史检验。这些主体看法主要指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其哲学理念是孔子所建立的;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后来的儒家容纳儒学思想发展可以超出古人的畛域;对于儒家以外的学说,主张包容并蓄;甚至对外来文化,也主张兼容吸纳。这就可以解释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科学思想也能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例如“格物致知”的学说,在古代主要是从伦理角度和个人修养立论的,而至宋代,二程朱子将其纳入知识论范畴,到了近代,“格致学”成了“科学”的代名词,“格致家”成了科学家的代名词。而晚明西方科学随着耶稣会士来华,受到了有着进取精神的中国儒生的欢迎,兼官员与儒 生 于 一 身 的徐 光 启(1562-1633)与利玛窦(1552—1610)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同时代的李之藻(1565-1630),不仅译刻了带有中文注解的大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高1.74米,宽4米),还编辑整理了《天学初函》,收入西方有关天主教理和学术方面的著作10种(理编)、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10种(器编)。正是儒家思想理念所具有的张力,使得在大航海之后的中国产生了一批主张兼容吸纳外来文化的儒生。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以学术史的眼光写《明儒学案》的时候就说过:“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这是对儒学理论的重要概括。
写至此,我也回想起30多年前张先生对我们说过的一些想法,后来也体现在这部《中国儒学思想史》的写作之中。
其一,思想是文化的核心。张先生经常说,从思想史角度探讨传统文化,比较容易收到应有的效果。对于儒学思想,他也十分注意挖掘其核心理念,加以升华。上面提到的“和而不同“就是一例。据我的观察,在1980年代中期的孔子研究中,张先生是最早从哲学理念高度阐发“和而不同“的概念,而不是从具体语境出发、就事论事地讨论。1986年他发表在《孔子研究》第三期上的论文《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引起学界的注意。特别是他把“和而不同”与“百家争鸣”“独立思考”联系起来,将“和而不同”上升到人类思想发展的规律来看,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来理解这一概念,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范例。
其二,独立思考。记得我们当年讨论书稿的时候,张先生非常强调研究、改造、继承、创新八个字,这八个字的基础,是独立思考。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书,在先秦,焦点集中在对“人学”的讨论;从汉代以后,在每一个朝代都将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纳入视野加以讨论,用这两个线索贯穿全书,这也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果,与其他同类的著作有所不同。在今天看来,书中具体结论固然可以讨论和深化,但其思想闪光仍存则是无疑的。
其三,区分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是非常复杂的事,不能简单从事。张先生常常告诫我们注意思想史研究的多面性。这里稍加引申加以说明。例如在明末清初,儒生面对当时西方传入、称为“天学”的西学,有的儒生为探其天算之学,皈依天主之学;也有的独喜天算,不喜天主;还有的视西学一概为“邪”,辟之破之唯恐不及。儒学面对西学的这些复杂情况,是对研究者判断能力的一种检验,简单从事就容易产生错误结论。
如何对待外域文化,早期儒学并不具备直接经验,但如果将“和而不同”上升到哲学理念的高度,就会认识到由“不同”产生的“和”,高于简单的同一。所以汉唐时代儒学没有排斥佛教进入中国,对于明代来自远西的思想文化,儒学也作如是观。对中国历史作了“功课”的利玛窦等人,当时不明其理,一开始把自己装扮成“和尚”,教堂取名“鲜花寺”,反倒效果不佳,改用“西儒”自称,得以立足。从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来看,儒学对远西文化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其理论思维指导的结果。这使西方的天文、历算、几何、地理、哲学、语言等知识,从16世纪中期起以汉语的形式纷纷进入中国,同时中国文化经典也翻译成拉丁文进入欧洲,确立了中国在全球史发展中的地位。儒学的理论思维,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毕竟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们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旧作,但儒学的理念是温故可以知新。我们寄希望于此。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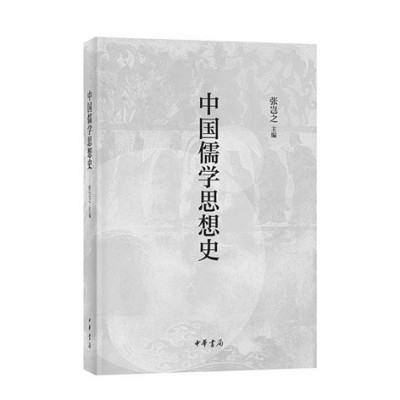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