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羽黑
一
常言道:“文无定法。”那么诗是否也是如此呢?“七律”这种诗体以“律”为名,说明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平仄、押韵),但我们所说的“作法”,主要并非规则,而是通过怎样的方法成就一首好诗。自唐以来,很多文学派别提出过种种主张,探寻诗法,但终究都是一家之言。因为他们以好诗作为范本,然而“酸咸不能调于众口”,什么是好诗便有争论;“梅止于酸,盐止于咸”,是好诗,但是否只有这样写才算好诗,这是第二层争论;最后,“味在酸咸之外”,好诗是否能用主张的方法写出,是最重要的争论。所以,方法很多,争论也从未停息。江西派提出“活法”,要“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这是神妙的境界,而非切实的方法,“活法”等于无法,可见越是要提出普适的理论,越有流于空泛的危险。但从另一面说,历来文学派别立足于好诗以说明方法,也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法门:作法和欣赏应该结合。欣赏之道和创作之法,两者可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为好诗的权衡操于读者,即便有人认为诗应该是“为己之诗”,只写给自己看,像陆放翁所说“诗到无人爱处工”,但自己也是读者,以读诗之我评判作诗之我,与评判作诗之他人,原理无异。事实上,每一首诗的第一位读者正是作者本人,诗的质量不仅在于作者的创造才力,也反映了作者的欣赏水平,就像好的厨师不会把烧坏的菜端出去,好的诗人也不允许不惬己意的作品流传。江西派还有一种说法,叫“悟入”,因为他们认为诗的精妙“言语道断”、只可意会,所以要从作品本身入手领会。故以下选取历来七律大家的作品,通过欣赏说明作法。
在进入正题前,我想就七律的规则说一点看法。有一些规则是灵活的,严格来说只是风格,但有一些忌讳虽然还没变成规则,我们却应该避免。比如,我们可以把诗写得流利,也可以写得拗口,事实上一直存在这两种风格,前者批评后者“诘屈聱牙”,后者批评前者“烂熟软媚”,但都不失为一种美学类型,关键看作者的才力高下。但有些情况不同。比如,七律韵脚外的句尾字,最好不要是一个音调,因为韵脚已经押韵,其他句尾字应该错落有致,否则会很单调。“单调”没有美感,正如噪音不是音乐,应当避免。
二
七律是所有诗体中最晚成立的,也是最晚成熟的。我以为唐代能够自立风格的七律大家只有两位:杜甫和李商隐。
杜甫《咏怀古迹》
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
环佩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
分明怨恨曲中论。
这是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的一首。有人认为“明妃”和“分明”的“明”字重复,所以“明妃”当作“昭君”,这样改确实好。七律只有五十六个字,重字应当避免,除非是刻意的重字,例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前者表现一种大气包举的粗犷风格,后者是顶针格,音调流美。此诗的两“明”字则是瑕疵。
诗题是“咏怀古迹”,首联点题。第一个字便有讲究,袁枚说“群”不能作“千”,否则就“不入调”。他是从音调上说。从文字来说,作“千”就和第七句的“千载”重了。我以为还可以从第三个方面说。“千山万壑”这样的四字成语一般应该避免,因为七律字数有限,四字成语浪费了作者的独创空间。古诗则不必如此,杜甫有一首古诗,“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千秋万古”就是成语。改“千”为“群”,显作者独创之功,且“千”和“万”对得太呆板,作“群”则错落有致。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陈宝琛有一首名作,“那知绿怨红啼景,便在莺歌燕舞场。”“绿怨红啼”“莺歌燕舞”都是很俗气的成语,这一联却甚妙。以俗为雅,是大诗人显本事的手段。
颔联叙王昭君事,简洁有力,句子和对仗也漂亮。这一联是标准的“流水对”,两句一气贯注,可作一句读。诗不是历史,在叙事的时候要注重辞彩。
颈联也写到史事,字里行间可见昭君绝世之姿。“春风”“夜月”两词从侧面写其风采,十分雅洁。
尾联写昭君生平悲怨,议论平实。杜诗不做翻案文章,不标新奇之论。宋代的欧阳修和王安石都有《明妃曲》,欧阳修从汉帝不识宫中的昭君,拓开一层说“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王安石则做翻案文章,说昭君“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我认为欧作更好一些,但也生硬,不脱文章家喜欢立论的习气。诗可以有议论,但要避免简单化。杜甫不在议论上求新立异,因为他知道这不是诗的重点。
李商隐《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
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
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
猜意鹓雏竟未休。
这是李商隐的名作。首联的“高”和“百尺”意思重复,如上所述,七律字数有限,要避免重字,也要避免重意。次联引贾谊、王粲为例;引古为例有个好处是“不粘不脱”,可以说是咏古,也可以说是喻己,比如“贾生年少”可以是自喻,“虚垂涕”也可以是作者对贾生的评价,认为他不必为世事痛哭,从而显出作者越世高迈的气概。颈联是名联,全篇因此振拔。这样凝练的句子把七律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末联点明题旨,却是败笔。纪晓岚说:“使老杜为之,末二句必另有道理也。”纪的眼光很高,评价李诗贬多誉少,颇能切中要害。李商隐的诗中间二联对仗都很好,足与杜甫争雄,像这首诗的颈联,雄浑高朗,不及老杜处则往往在结尾。此诗前面已表现了宏阔的眼界胸襟,末联突然说自己志向高远,不屑与小人争利,小人所争者只是“腐鼠”,恰恰说明他还是介怀的,这样反而把本来很高的境界拉低了。古人提倡“温柔敦厚”,有人片面地理解为不做激烈之诗。其实激烈不激烈,并非第一义,重要的是得体不得体。
三
宋是七律的黄金时代。我以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者是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和金人元好问。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是东坡和他弟弟苏辙的诗。和诗不仅要遵守原诗的韵脚,其他方面也要照应原作。首联的“应似飞鸿踏雪泥”,原作是“共道长途怕雪泥”,严格来说和作的韵脚不能用原作的词,东坡沿用“雪泥”一词,不足为法。该诗前四句劈空而至,极为超卓。“飞鸿踏雪”的比喻很简单,不过是说行踪无常,但胜在喻境之美,令人起空茫之思。颔联并非对仗,却有对仗的意味,黄庭坚有一首有名的七律,颔联是“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也不是对仗而有对仗之意。我们知道陈寅恪曾经推许苏东坡的“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东坡同时代的诗僧惠洪也说他的“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是“对甚的而字不露”(对得非常妥帖,但不显露)。这样精于对偶的大诗家,偶然不遵常格,得其意而忘其形,便能写出特别挥洒的句子。诗的后半段乏善可陈。这是东坡七律常见的缺点,有卓越的想法,语言也很流畅,全篇却欠设计和锤炼,不耐讽咏。我们往往敬佩他的聪明,却很少被他打动。
黄庭坚《题落星寺四首》(其三)
落星开士深结屋,
龙阁老翁来赋诗。
小雨藏山客坐久,
长江接天帆到迟。
宴寝清香与世隔,
画图绝妙无人知。
蜂房各自开户牖,
处处煮茶藤一枝。
这是一首拗体诗。圆熟流畅的句子像甜食,难免吃腻,黄庭坚的诗就是消食的苦茶。熟悉格律的读者看这首诗,时时感觉苦涩不畅,因为每一句的格律都被刻意拗折,读起来诘屈聱牙,但相比圆润之句容易滑过不留痕迹,这样生满棱角的诗作往往能留下深刻的印象。首联是“深结屋”而非“结深屋”,将“深”字做动词“结”的状语,比名词“屋”的定语显得更有力。山谷诗的美妙如同枯劲的书法,将所有丰腴的部分剔除,骨力毕露。第二句化用了杜甫《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之二“何处老翁来赋诗”。有趣的是,杜甫这首诗也是拗体七律。中间二联,“坐久”“到迟”,都与俗世的纷扰忙碌形成对比;“与世隔”“无人知”,尽见其萧瑟寂寥的会心之处。尾联的“蜂房”句很有名,这一比喻也呈现一种漠然的美感。末句的“茶”“藤”,都是体现枯淡之趣的名物。我们可以看到,全诗的所有描写、甚至用典都和文体的拗折契合。因为浑化,所以读来纯粹自然。
陈师道《春怀示邻里》
断墙著雨蜗成字,
老屋无僧燕作家。
剩欲出门追语笑,
却嫌归鬓著尘沙。
风翻蛛网开三面,
雷动蜂窠趁两衙。
屡失南邻春事约,
只今容有未开花。
陈师道的用力处是使七律的五十六字包含更多的曲折。他的诗仿佛“一步一景”的园林,句句有转,句句可味,整首诗或许有浑然的情怀,但这情怀却是由无数动态的念头相续而成,所以显得活泼。本诗的题目“春怀”正是如此,首联两句在句中都有因果(因为“著雨”,所以“蜗成字”;因为“无僧”,所以“燕作家”),用字很密。颔联的“剩”和“归”字凝练:“剩”是“更加”的意思,春日的情怀本不许人孤寂,屋里又是这样惨淡的光景,所以“更”欲出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更”字的因果,不仅包含了首联,也收纳了诗题,足见匠心。“归鬓”给读者意外的体验,因为“出门”是动作,“归鬓”是名词,其实不能对仗,但字面上又完全对仗。到此为止,意念转了几层,人却还在屋里,下半首继续描写和想象。黄庭坚形容陈师道是“闭门觅句陈无己”,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闭门觅句”和他心思百转、重门叠户的诗风,或许有很深的关系。
陈与义《登岳阳楼》
洞庭之东江水西,
帘旌不动夕阳迟。
登临吴蜀横分地,
徙倚湖山欲暮时。
万里来游还望远,
三年多难更凭危。
白头吊古风霜里,
老木沧波无限悲。
陈与义的七律句法极疏朗,本质上和“一步一景”、层层转折的诗风相反:不需曲折花巧,而纯然以清刚之气放笔直写。首联的“之”是无意义的虚字,用于七律本是对有限空间的浪费,但陈与义用在此处,恰恰表现了他的风格无须计较空间,颔联仅仅点明了时间和地点,但不加修饰地陈述宏阔的空间,极显大气。颈联由此时此地引出过去人生的经历,展现纵深,因为用了很巧妙的联想(已经游历了万里,还登楼看远方;三年间那么多危难,还要凭倚危楼),所以显得自然流畅。这种风格的七律最重要的是自然,所谓“一气贯注”,流泻而下的“气”不能有一点滞碍之处,所以难处在“虚”而非“实”,苦心思考和刻意雕琢反易坏事。尾联是寻常的吊古语,和全诗一样,没有一句是意外的——意外会破坏清空之美。
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
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
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
犹及清明可到家。
宋代最会写对子的诗人可能不是苏轼,而是陆游。他的七律数量极多,对偶的质量也很好,引得同时代的刘克庄惊呼:“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从另一角度看,说明很多人以为难得的“好对偶”其实是可以批量生产的。他的文学技巧太高,感情也太丰富,以至于反而不容易让人体会他的真诚,尤其是关乎国家的宏大题材,多看就会觉得(也许是错觉)那只是一幅幅“好对偶”,正如发现汤味鲜美来自味精。所以此处选择了一首无关宏大的名作。作者客居京华,在百无聊赖中,注意到了一些有味的细节,写成了隽永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到,好诗比“好对偶”难得的多,就像真诚的哭笑永远不像演员表现的那么多。
元好问《岐阳三首》其二
百二关河草不横,
十年戎马暗秦京。
岐阳西望无来信,
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
残阳何意照空城!
从谁细向苍苍问,
争遣蚩尤作五兵?
元好问在七律一道上,掌握了某种诀窍,使他的诗最具沉着之致。此诗就是很好的例子。首联劈入一个惨烈的大背景。颔联其实是用了两个典故,上联用了杜甫的“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将“眼穿”二字融为“望”字;下联用了北朝古歌的“陇头流水,鸣声呜咽”。妙在都是化用,即便不知其典,仍不失为出色的白描。元好问是北魏拓跋氏之后,又是杜甫的继承人,他的诗风也恰恰像这一联的用典,是北朝苍直之气和老杜悲慨之怀的合体。颈联和尾联都以问句结尾,则略嫌单调。尾联之问隐承颈联:既然野蔓都能有情地缠绕战骨,上苍为何无情至斯纵其凶暴?质问上苍是痛苦到极致的表现,《后汉书》中说:“凡人之情,冤则呼天,穷则叩心。今呼天不闻,叩心无益,诚自伤痛。”这也是作者的伤痛。
四
元代没有影响深远的七律作家。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七律作者很多,有一些作者的作品总体质量不亚于唐、宋大家。我选了两位典型:李攀龙和钱谦益。
李攀龙《怀子相》
蓟门秋杪送仙槎,
此日开尊感岁华。
卧病山中生桂树,
怀人江上落梅花。
春来鸿雁书千里,
夜色楼台雪万家。
南粤东吴还独往,
应怜薄宦滞天涯。
如果说黄庭坚、陈师道发掘了杜诗中高妙的优点,李攀龙则找到了易学易会的法门,批量生产杜诗。他的诗就像描红本的字,工整到很难挑出缺点,也很难找出艺术的灵光。这首七律在风格上更近王维或李颀而非杜甫,但和他的学杜诗一样,情感节奏高度模式化。颔联将《招隐士》的桂树之典和古笛曲《落梅花》凑在一块,小有巧思,但我们不应忘记刘禹锡的《竹枝词》:“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早已把它们合在了一起。颈联的“书千里”和“雪万家”,是他喜欢的大数字对联,也显呆滞。总之,这首诗和他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只能算平平,那么李攀龙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想他像是一个筛子,筛出了唐诗的精华,而他作为筛子,恰恰承载了唐诗的糟粕。正如陆游使人们意识到“好对偶”可以量产,李攀龙也使人们发现,往日推崇的某些唐诗在艺术上并没有那么高的水准。比如,杜甫的《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人称“杜诗之最上者”,但徐渭评论:“人皆尽称此首,吾独以为板而凑也。‘来天地’、‘变古今’,板也;‘北极’句,凑也。”我以为此首足当佳作而无愧,但毋庸讳言中间二联确实是杜诗中“易学易会”的部分,而非“艺术的灵光”。
钱谦益《西湖杂感》之二
潋艳西湖水一方,
吴根越角两茫茫。
孤山鹤去花如雪,
葛岭鹃啼月似霜。
油壁轻车来北里,
梨园小部奏西厢。
而今纵会空王法,
知是前尘也断肠。
钱谦益在文学上有最开放的心态,善于融合各家的长处,而这恰恰是杜甫的特点。李攀龙编诗选,于宋诗一概不收,唯恐学诗者受其影响;他忘记了他最推崇的杜甫提倡“转益多师”,以博大和革新见长。钱谦益的态度和杜甫一致,而学问更为渊博,所以在七律一道上,隐然达到了可以和杜甫争雄的高度。如果把杜甫的七律看成一座大湖,那么李商隐以降的大诗家基本上都是它的支流,在流动的过程中由伏而显,渐渐发展成水量丰沛的大河,这些大河再度汇聚成一片大湖,那就是钱谦益的七律。李商隐的含蓄、苏东坡的超逸、黄庭坚的雅致、陈师道的细密、陈与义的清健、陆放翁的对偶、元好问的沉着,无一不被熔铸其中,截长补短,去粗取精,加以过人的天分和特殊的遭际,成就了一千余首质量极高的七律。如果要稍作领略,可以看他《投笔集》所收录《后秋兴》组诗,奇情壮采,至为耀目。这里选了他晚年的《西湖杂感》诗中的一首。首联的“吴根越角两茫茫”,是元代陈樵的成句。七律一般不宜袭用前人成句,除非有推陈出新之效。颔联虽然寻常,但气味雅淡。有一些寻常的诗句,措置得宜,则令人一唱三叹。陈寅恪诗宗钱谦益,名句如“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与牧斋此联有异曲同工之妙。颈联描写当日的繁华。到此为止,作者只是不带感情地平静描述。我们看到最后,才能体会作者的克制是多么值得:尾联瞬间引发了全诗的沧桑感,回过头看前六句,无不足以令人“断肠”。钱谦益无疑掌握了控制情感的秘诀:不动声色。
五
清诗的成就很高,尤其是七律,前代几乎每一家的风格都发展到了极致。唐代的一些传世名作,依清代的标准或许只能及格。我们回顾诗史,从唐至清,七律的平均质量在上升,但最耀眼的作品注定属于上游的开拓者,钱谦益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越往下走,开拓便越显艰难,更多的作家选择了对已有风格的深入挖掘。从大诗家中,我选择了两位成功的开拓者:陈三立和郑孝胥。
陈三立《晓抵九江作》
藏舟夜半负之去,
摇兀江湖便可怜。
合眼风涛移枕上,
抚膺家国逼灯前。
鼾声邻榻添雷吼,
曙色孤篷漏日妍。
咫尺琵琶亭畔客,
起看啼雁万峰颠。
陈三立的风格是如此鲜明,连李商隐、黄庭坚和钱谦益都及不上他,只有杜甫对诗歌文字的革新才能与之相比。在他之前,有一些诗人革命性地使用汉语,比如乾嘉时代的广东名诗人宋湘有一首咏木棉的七律,颔联是“祝融以德火其木,雷电成章天始春”,用字之法令人耳目一新,但没有人能像陈三立一样,将新的字法树立为风格。这一首诗是他风格的典型。首联把普通的旅程,夸张为“有力者负之而去”的神迹(《庄子》的寓言说“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陈三立只是拿来比喻夜晚行舟),奇则奇矣,未免有“狮子搏兔用全力”之感。颔联的“移”和“逼”字是句眼,他的儿子陈寅恪有一联“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同样用到“家国”和“灯前”,但与乃父气味完全不同。颈联的字法也很生辣,“日妍”是个生造的词。古诗不妨造词,如李贺的“花楼玉凤声娇狞”,“娇狞”就是生造的词语,擅长古文和古诗的韩愈更是造词的高手,七律则应避免生造词语。尾联的“啼雁万峰颠”,也是陈三立喜欢使用的高奇之境。陈石遗批评陈三立诗“千篇一律”:“为散原体者,有一捷径,所谓避熟避俗是也。言草木不言柳暗花明,而曰花高柳大;言鸟不言紫燕黄莺,而曰乌鸦鸱枭;言兽切忌虎豹熊罴,并马牛也说不得,只好请教于犬豕耳。”钱钟书也说他的诗远不如学钱谦益的陈寅恪,只有一种高亢之气。这些评论未免刻薄,却也切中要害。陈三立虽然像杜甫一样开创了文体,成就却不如其他七律大家,因为他的风格不仅单调,而且简单,容易复制,把“避熟避俗”变成了另一种熟和俗,而他的才气逊色于同样喜欢自我复制的陆游。我认为散原的另一个缺点,是力量的滥用。他喜欢将生辣刺眼的字词不加节制地使用,就像一个把每一道菜都做成重辣的厨师,食客的味蕾因此麻木,根本无法尝出食物本身的美味。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应该向钱谦益学习控制之道。幸好,他的儿子这么做了。
郑孝胥《春归》
正是春归却送归,
斜街长日见花飞。
茶能破睡人终倦,
诗与排愁事已微。
三十不官宁有道,
一生负气恐全非。
昨宵索共红裙醉,
酒泪无端欲满衣。
郑孝胥喜欢做宗社党人语,但他的诗却有经常在革命者身上体现的浪漫气质,并且终生未改,我们看到他在“七十残年世共轻”的晚年所做的重九诗中还说“俯视中原三万里,不妨抱膝过重阳”,与早年“名花身世真堪羡,烈烈轰轰做一场”没有什么不同。有人认为他接近韩偓(他自己也说得力于冬郎),事实上他比韩偓多了一种激烈傲兀,而这恰恰构成了他的主要诗风。这一点在这首名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首联写得相当草率,明人论诗,说“俗笔开口便怨”,正可以评价这一开头。杜甫写同样题材的作品,以“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起笔,相比此诗显得何等温柔敦厚。由此开始,整首诗都被怨意笼罩,颈联是名句,也是最怨之笔。郑孝胥晚年的地位相当高(虽然绝不可能为他赢得任何正面的名声),但诗中始终弥漫着少年郁郁之气。我固然欣赏这些长歌当哭的诗句,但感觉未免儇薄了一些,缺少大诗人应有的温雅或厚重的气质。
六
清以后旧体诗的质量远不如昔日。但在七律方面,仍出现了一位必须一提的诗家:陈寅恪。
陈寅恪《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
谁缔宣和海上盟,
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已久留胡马,
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幺同有罪,
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
莫遣遗民说汴京。
陈寅恪的作品多为七律,风格上颇效钱谦益,与其父陈三立的诗风可谓完全相反:散原讲究气骨,尽力烹炼奇特的字眼;他讲究韵味,尽量避免奇特的字眼。在诗道上他与陈宝琛一脉相承。站在他的美学立场来说,奇特的字法和句法就像调味料,会破坏诗歌的本味。他早期的一些作品淡而无味。以后随着过人的识见、丰沛的情感融入诗中,他的七律境界之高,已非常人可以企及;语言之雅洁,也几近完美。自然凑巧的东西会给人带来一种毫不费力的舒适感,是比“才气横溢”或“笔力绝伦”更高的境界,这首诗正是如此。我们看到史事贴合时事;颔联对仗看似过于工整(“花”对“柳”、“胡”对“汉”,蒙童可为),但无不妥帖;颈联字字都有着落,“战和”句更是表达了人人意中所有而难以言表的事态;尾联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韵味悠远绵长。我们甚至会感觉作者是“发现”了这首诗,而不是“创作”了这首诗,正应了“毫无作态”一语的字面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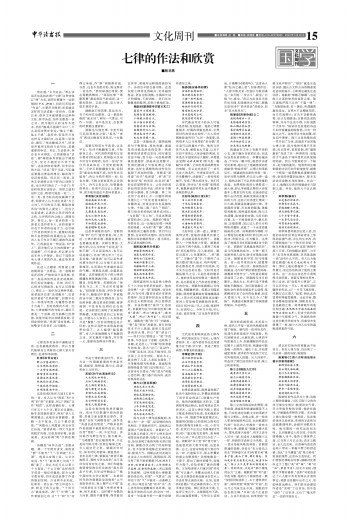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