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一鸣
《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是中国书籍史研究领域的不朽之作,也是著名学者钱存训先生的代表作。它不仅是一部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也因其生动明快、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成为一代代对中国书籍稍感兴趣者的入门必选之作。2002年,时值《书于竹帛》英文初版问世六十年之际,东方出版中心推出该书六十周年纪念版。笔者不拟赘述是书卓越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谨以此为契机回顾书籍史研究发展的历程,重审《书于竹帛》作为一部书籍史经典著作的生命历程。
《书于竹帛》最初出版于1962年,但其肇源则远早于此,可以说它是书籍史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几代学人长期酝酿与探索后取得的成果。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的文献学传统面临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追溯与总结中国书籍的发展历程与发展规律,这一阶段也可以视作中国书籍史研究的准备期。在这一阶段,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可谓是承前启后之作。其宗旨如叶氏之侄叶启崟所述:“于刻本之得失、钞本之异同,撮其要领,补其阙遗。推而及于宋元明官刻书前牒文、校勘诸人姓名、版刻名称、或一版而转鬻数人,虽至坊估之微,如有涉于掌故者,援引旧记,按语益以加详,凡自来藏书家所未措意者,靡不博考周稽,条分缕晰。”简言之,《书林清话》的史料与论点来自于叶德辉对多年读书、藏书经验的积累与总结,并通过专题进行排列。从专门史角度来说,它并非系统性梳理中国书籍史的著述。但是,由于叶德辉多年来浸淫古书,熟谙旧籍,所以其讨论的问题大多都有文献或者实物依据,其所关注的所有内容也都属于书籍史的研究范畴,因此可以说是中国书籍史研究准备期的一部巨著。
在《书林清话》奠定的基础上,学者对书籍史这一主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形成了一系列的著作,如李继煌所编的《古书源流》,陈彬龢、查猛济合著的《中国书史》等等。尽管已有探索源流、考古稽原的意识,但其内容仍以采摭历代史料为主,带有鲜明的传统学术笔记特征。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与书籍史相关的史料逐渐搜集完备,关键问题逐一解决,一条从古至今的书籍史主线已然呼之欲出。而它的最终完成及完善,著名学者刘国钧可谓厥功至伟。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归来以后,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中国书籍史相关著作。刘氏在对古今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及总结的基础上,以朝代更迭为基本线索,从图书的思想内容和物质形态两个方面,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书籍的产生、发展及其社会作用,第一次较为科学地构筑了中国书籍史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刘氏的研究“确立了中国书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和学术框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中国书史的研究”(吴慰慈《试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120周年》,《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年第6期,第5—9页)。
1925年,刘国钧开始担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在其任教期间,正于该校求学的钱存训先生完成了本科课业的修习,同时也继承了该校的书籍史研究传统,从此钻研此道,终臻化境。当然,钱先生能够投身中国书籍史研究并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不仅是受到刘国钧等国内学者的影响,更是对东、西两个向度相关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学习。美国学者托马斯·卡特(Thomas Carter)撰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就是钱先生汲取营养的土壤之一。是书以雕版印刷为中心,按照“中国印刷术的背景”“中国的雕版印刷”“雕版印刷西传的进程”“活字印刷”的顺序,梳理了印刷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在西方中国书籍史研究领域有导夫先路的开拓意义,也启发了钱先生去留意雕版印刷以前的书籍文化。
1947年,精通传统文化、经受过系统书籍史研究训练并从事过大量古籍整理实践工作的钱先生受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Creel)之邀,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0年后,他完成了题为“The Pre-printing Records of China :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Books”(《印刷发明前中国书和铭文的起源与发展》)的博士论文,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学博士学位。1962年,钱先生完成了对是书的修订和增补,更其名为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书于竹帛:中国古代书籍和铭文的起源》),名著方正式出版。
身处异乡的钱先生敏锐地关注到: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书籍的基本认知,本质上是将其视作以汉字为表现方式的文字记录。因此,《书于竹帛》的立意打破了中国学者“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跳出汉字文化语境,以兼具中西学养的中国书籍专家身份,考察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古代文字记录。对此,钱先生有过一段被广泛引用的精彩论述:
中国文字记录的一个重大特点,便是它独有的持久性和延续性。这一特点使得世界上一个有创造性的远古文化,得以继继绳绳,绵延至今。中国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义以外,还有其特殊的形体,这种具有特殊形体的文字、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
中国文字的另一特色是它的普遍性和广被性。这种具有形体的文字,即使各地方言不同,也可以共同使用;不仅中国人在使用,也是东亚许多其他民族的共同文字。他们虽各有自己的语言,但也采用中国文字的全部或一部,作为思想传播的媒介,如越南、朝鲜、日本及琉球,中国文字的应用于书写和书籍,在历史上都有一段很长的时期。
可见,钱先生叙述中国书籍源流的出发点是中国文化和文字的特异性,核心线索是汉字文献的载体变化。因此,是书除第一章《绪论》外,根据文献的不同载体安排各章内容,分别为第二章《甲骨文》、第三章《金文和陶文》、第四章《玉石刻辞》、第五章《竹简和木牍》、第六章《帛书》、第七章《纸卷》、第八章《书写工具》,并在第九章《结论》部分中对各章内容予以回应和总结。纵观全书,对汉字文化的观照贯穿始终,完整地展现了汉字对中国书籍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塑造过程。考虑到本书原用英文撰写,面向对象为海外读者,这层意涵就显得更为特殊,也使本书跳出了地域与语种的界囿。
钱先生此书的思路与视角有别于此前的书籍史著作,引发了学界的热烈反响,同时也启发了后来的书籍史研究。如日本学者平冈武夫所说:“钱存训教授的这部著作,犹如前述书名‘书于竹帛’,出发于追寻汉字的根源:写在何物上?以何物来写?如何来写?因此逐渐形成为书籍的形式。换句话说,这部著作是在于追寻汉字的根源,为此目的而写作。这是一部真正出发于重新观察汉字文化的著作。”正是这种迥异于以往书籍史研究的考察视角,使《书于竹帛》的章节组织与脉络梳理不执着于建立朝代更替的叙述模式,而是选择了更具普适性的载体变迁为主要叙述逻辑。因此,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字记录的变化借助“甲骨—金属与陶器—玉石—简牍—缣帛—纸张和笔墨”这一文献载体演变的轨迹得以具象呈现,以获取不同文化语境的读者与研究者的理解与接受。这也保证了是书具有常读常新的潜力与空间,使读者可以从这部诞生于六十年前的经典著作中得到新鲜的阅读体验。
作为一部经典著作的新版,六十周年纪念版《书于竹帛》尽可能地囊括了已有的相关资料,试图为这一经典之作注入新的元素。此版堪称《书于竹帛》出版史上的集大成者,它收录了许倬云教授所撰的《百五人瑞:钱存训先生一生行述》,邀请沈津教授撰写了六十周年纪念版序,并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增订再版本,收入了之前各中文本中未收的夏含夷教授所撰后序《1960年以来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以及《重大考古发现(1899—2000)》《中国文化、书籍与文字记录年表》。这些内容的学术价值远超于对是书的引介,可以视作是书衍生出的研究成果。此版附录还容括了李棪、李约瑟(Joseph Needham)、平冈武夫分别为《书于竹帛》中、英、日文版所作的评介与序言,其中对于是书的评价与论述受到学界的高度认可与广泛沿用。此外,附录中还有别立谦编译的《〈书于竹帛〉评介摘要》、钱先生之侄钱孝文所纂《钱存训书史著述编年》以及长达60页的中、日、西文参考文献。加之书前刊印有关钱先生和《书于竹帛》问世历程的图片20幅,1960年芝加哥大学教授霍华德·文格(Howard Winger)与顾立雅向著名出版人卡罗尔·鲍恩(Carroll Bowen)推荐出版钱先生博士论文的信件,1961年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关于出版此书的审稿意见,以及此书英、中、日、韩历次版本的封面。此次出版所附的这些信息,不仅为专人与专书研究提供了丰富且系统的研究资料,还给书籍史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个案。
如果说《书于竹帛》是中国书籍史研究的重要节点和里程碑,那它的出版与阅读史同样是书籍史研究上的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案例。有西方阅读史研究者认为,阅读才是书籍生命的真正开始。从这个角度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翻译与重印,《书于竹帛》的生命历程得到了延续、丰富与近乎无限的延伸。从这一角度说,一千个读者眼里也有一千本《书于竹帛》。仅就六十周年纪念版所搜罗的诸多相关序跋、评介与资料而言,李约瑟聚焦于《书于竹帛》对文字及数据资料的搜集与揭示,平冈武夫关注于汉字文化的演进规律与出路,劳榦则主要就具体观点展开讨论并提供史料补充,夏含夷立足于对中国古文字考古的梳理……可见,一部经典著作之所以保有旺盛不息的活力,是得益于读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解读、加工、发掘与重构的。在《书于竹帛》的出版历程上,六十周年纪念版既是一个结点,也是又一个起点,将滋养中国书籍史领域更多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和观点。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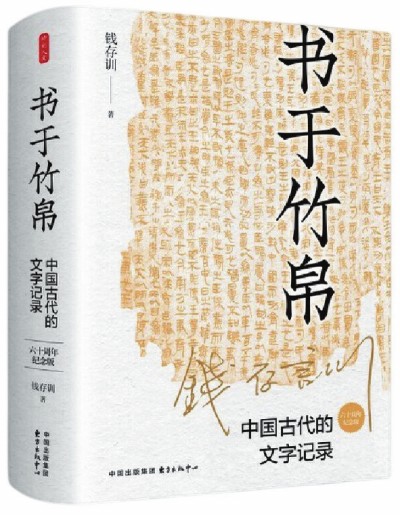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