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
岁末,收到李伟国兄的两部著述,一部是编辑的《宋文遗录》(下称《遗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12月),一部是撰著的《中古文献考论:以敦煌与宋代为重心》(下称《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1月)。著者是我的学长,我考进上海师大历史系本科的当年,他随即入读本校古典文献的研究生。1981年,他跨入出版界,迅速驰名海上,成为学者型的出版家。在古籍出版与研究上,他的成就集中在敦煌学与宋史两大领域。关于前者,他参与决策了《俄藏敦煌文献》与《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被文献学大家胡道静先生赞为“不世之大业,文化之盛举”。关于后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慧眼独具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擘划影印了宋史要籍汇编,包括浙江书局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清许涵度本《三朝北盟汇编》与明永乐本《历代名臣奏议》,为嗷嗷待哺的新时代宋史研究及时输送上急需的资粮,我们这代学人正是借助这批要籍走上研究之路的;新世纪初,他主政上海辞书出版社,又极具魄力地拍板一次性出版《全宋文》的大工程,为宋代文献出版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年假有暇,翻阅对读两书,深感无论在成果整理还是方法示例上,他为历代诗文总集的编纂、辑补与研究都留下了值得推重的实践经验与真知灼见。
一
立凡例于实践,示轨辙于未来,无疑是著者的首要贡献。
2006年出版的《全宋文》,连同此前问世的《全宋词》《全宋诗》与其后推出的《全宋笔记》,可谓宋代文献结总账式的整理,而《全宋文》在体量上远超其他三部大全的总和,对宋代文史研究的推动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宋文》成功付梓之后,伟国兄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继续从事《全宋文》的后续工程:一是参与主持完成了《全宋文》专题资料库;二是投身于《全宋文》辑补的编纂工作。他揭示了《全宋文》对宋代文史研究的两大阅读功能:一是有序的阅读功能,即研究者一旦选定某文学流派、文学家或历史人物,便按图索骥地对相关作品进行有序的研读;其二,无顺序的阅读功能,即研究者“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调取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与其他相关资料一起成为排比研究的物件”,这一功能适用于“为数更多的历史、语言、哲学、经济、军事等研究者”。与此同时,他强调,《全宋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进一步挖掘、搜集、整理和研究仍有巨大的空间”(《考论》416-417页)。在卸任出版领导岗位后,他心无旁骛地一头扎进了宋代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中,《遗录》与《考论》就是他历时十五年构筑的纪程碑。
在搜集、整理《全宋文》遗文过程中,著者总结了六条搜求原则,对历代诗文总集的编纂与增补,既具操作性,又富启发性。其一,对宋人文集的重新发掘。这是由于总集首次编纂时往往限用文集的某一版本,而忽视了同一文集现存单刻本、丛书本与海外刻本之间的诸多差异,即便同属四库本的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也颇有出入。《遗录》从文津阁本《景文集》辑出宋祁佚文达六卷之多,基于这些实践,他创立了“《四库全书》的集合性价值”的学术命题,并且呼吁,这种“作为一个图书、文献或信息集合体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完全可以借助数据化的现代技术获得空前有效的提升。其二,充分搜求前人忽略的重要史书。著者对朱熹撰稿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与《三朝名臣言行录》深有研究,从中辑出为数可观的《全宋文》失收遗文。其三,爬梳搜罗宋代以降的地方志。仅据国内罕见而东瀛收藏的《(嘉靖)湖广图经志书》,著者就辑出《全宋文》佚文多达77篇,并为其中滕宗谅致范仲淹的《求岳阳楼记书》撰作专论(《考论》327-353),为范仲淹撰记时是否到过岳阳楼作了定谳。其四,从存世宋代各种法帖中辑集遗文。《遗录》据《凤墅帖》辑入黄庭坚书帖九篇与岳飞书帖三篇,都弥足珍贵。其五,从新发现的《宋人佚简》与《武义徐谓礼文书》中辑录遗文。对这一原则,在理解上似应举一反三。实际上,《俄藏黑水城文献》乃至《敦煌吐鲁番文书》仍有宋代遗文值得勾稽;而已出版的《大足石刻铭文录》与重庆白鹤梁水文题刻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宋文可供辑采。其六,从现存各种形态的宋代碑铭中辑集遗文。其中包括宋代以来所有金石典籍、海内外公私藏家的碑石拓本、近代以来新发现的宋代石刻文献及其研究论著、实地寻访新出土的宋代碑刻。
在六条原则外,著者对整个搜访整理中的注意事项也各有具体的提示,包括材料真伪的辨析考证,石刻文字与手写文书的辨认释读,录文的校勘、标点、分段、断限与排序,作文时间、作者小传、图版拓本、工具性索引等附加信息的著录,等等。由于长期浸润其间,积累与经手了数以百万字计的宋代文献,亲历甘苦,深知繁难,故著者在讨论搜求原则与整理要求时,联系实例,现身说法,不仅度人金针具有操作性,同时由此及彼富于启示性。
总之,在新形势与新技术下,对一代诗文总集的编纂与辑补,在阅读功能、使用价值、搜求原则与操作事项等方面,著者既从文献整理上投入了甘苦备尝的丰富实践,更从理论方法上给出了启迪学界的深入探讨。
二
立足严谨规范的文献整理,展现当行本色的历史研究,堪称是著者的拿手绝活。
毫无疑问,在一代诗文总集编纂与辑补过程中,对哪些文献可以或不宜编入总集,本身就以相应研究为其前提的,但这种研究主要停留在文献学层面。总集一旦完成,便转化为公共的学术资源,一般而言,整理者也就大功告成;进一步利用文献进行再探索,便是历史研究者的用武之地。但伟国兄之于宋代文献,不仅是深度的整理者,更是出色的研究者,尤其在宋文搜辑的拓展过程中,某些新信息总会激发他的研究活力。
新世纪初,河南富弼家族墓地出土了由韩维撰写的富弼墓志铭等重要文物,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他将新出墓志与已收在《全宋文》里的同一铭文对校比勘,断言“出土文本较传世文本为好”;但他的研究并未止步于文献学层面,而是进一步将包括新出墓志在内的四种富弼传记从文本渊源与叙事异同上开展了独到的研究,撰有《墓碑的故事和铭文中的历史》(《考论》168-191页)。在这篇颇具创意的论文中,他将这篇作于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的墓志铭与范纯仁撰于同年七月的行状、元祐二年(1087)由苏轼撰笔的《神道碑》以及以北宋《四朝国史·富弼传》为史源的《宋史·富弼传》集结成一个序列,紧扣政局的嬗变与作者的异同,分析对比了四个文本在不同时期对富弼事迹的不同表述,得出了鞭辟入里的判断:“即使是政见歧异最甚的熙宁、元丰、元祐时期,士大夫仍然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唯行文方式和开放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这样的研究,在方法与视野上已超越了文献学的层面,令人信服地成为北宋中期政治史的新论点。由于《全宋文》已收韩维的《富弼墓志铭》,尽管“出土文本较传世文本为好”,鉴于编例,《遗录》未将其收入是合理的。
《遗录》收录了千唐志斋庋藏的李清臣撰《张氏墓志铭》,墓主为张亢之女;与此铭相对应,著者有《〈宋故冯翊郡太君张氏墓志铭〉考》(《考论》192-217页)。据其考证,这位张氏实为范仲淹幼子范纯粹的生母,她以低微之身进入范家,服侍主人,生下儿子。作为范仲淹的配偶,张氏的生父并非与范仲淹同时、占籍临濮的名臣张亢,而是另一位同名同姓的钱塘普通人士。著者将文献索隐与历史研究无缝对接,不仅有力廓清了范仲淹研究中的诸多疑窦,而且指出,这位张氏因身份限制,“与范仲淹的结合,在当时士大夫阶层看来,是不值得一提的”,故在记载范仲淹生平的诸多碑铭中都被隐去,“实在是当时礼教观念所致”。整篇考证犹如曲径通幽,最终结论不啻拨云见月,洵为《遗录》与《考论》交相辉映的精彩个案。
《遗录》还分别收入了北宋杨畏在绍圣四年(1097)为亡妻王氏(王尚恭女)所撰的《王氏墓志铭》,与其另一亡妻王氏(王宗望女)在杨畏死后由王氏亲兄王纯撰书的《王氏墓志铭》。在北宋晚期政坛上,杨畏以“杨三变”之号而臭名昭著,其人品更为士大夫不齿。传世的杨畏墓志铭仅有篆盖的标题与落款的日期,这一奇特现象引人关注,在研读其两位亡妻的《王氏墓志铭》后,著者特撰专论《没有内容的“墓志铭”》(《考论》218-226页)。据其考论,杨畏因清誉扫地,其第一位亡妻辞世时,竟然请不到士大夫为她撰写铭文,只能亲自操刀;杨畏死后,“这样一个被世人鄙夷的人物,他的后人居然请不到人为他撰写行状与墓志铭”,致使其墓志铭仅有篆盖而无铭文;在其身后,他的第二位妻子物故,由于杨畏遗臭未尽,仍无人愿意为其亡妻志墓,只能由亡妻之兄执笔撰铭。著者的论述令人寻味:由于杨畏在政坛上人品为人不齿,致使在“墓志铭这样一件宋人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上不仅祸及自身,还贻害了两位夫人” 。
著者正是凭借着娴熟的文献功夫,游刃于钟情的历史研究,《考论》中的宋史论文无愧于邓广铭先生给出的盛誉:“取材全极广博,论断全极精审”(邓小南《考论·引言》)。
三
作为《全宋文》辑补的阶段性成果,《宋文遗录》收文近三千篇,字数超二百万,其规庑宏大,业绩昭著,有功于宋代文史研究是毋庸赘言的。在整个编纂过程中,由于工序繁多,头绪复杂,在个别细节上偶失照应,也在情理之中。纵有小疵,不掩大德。这里,笔者芹献两点,聊供《遗录》后续编纂时参酌。
其一,关于某些遗文的作者信息著录。《遗录》据文津阁本《竹洲集》收入该文集著者吴儆的任命告敕两篇(《遗录》1571页),将作者定为宋孝宗;在辑录《武义徐谓礼文书》时,将宋宁宗朝与宋理宗朝形成的徐谓礼各篇授告的作者同样分别定为宋宁宗与宋理宗。众所周知,任命制敕虽以皇帝名义颁布,却例由翰林学士、知制诰或中书舍人等词臣撰稿。《遗录》据文津阁本《景文集》辑入多篇内外制,未将其著作权划归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而仍定为宋祁,应鉴于作者明确,著作权归属自是理所当然。而倘若作者无法考实,相关告身的作者信息定作“佚名”似较妥当,而不宜归为其形成之际的在位皇帝,庶几在作者信息上执行标准归于统一。
其二,关于某些遗文是否符合收录体例。《遗录》据《重修金华丛书》本《蟠室老人文集》辑入南宋葛洪文五卷,弥补当年《全宋文》编纂时“无力获致”的遗憾,诚为快事。其中也收入葛洪的《涉史随笔》序与随笔文共26篇。《涉史随笔》属于史评类专著,有四库全书与知不足斋丛书等多种版本别行,倘若将葛洪此书以单篇文章一并揽入的话,那么范祖禹的《唐鉴》(类似例子还不止此)也由序言与306篇史评组成,是否也都应编进《遗录》呢?在已出《全宋文》范祖禹文下仅收《唐鉴序》而不收单篇史评。两相对照,同样涉及取舍标准是否统一的问题。
《全宋文》辑佚是功在千秋的大工程,诚如伟国学长所说,“在三五年乃至十年内是不可能穷尽的”。让人鼓舞的是,他壮心未已,宣布还有近千万字的宋代遗文正在董理中,并期许在八十耄年全部完成。作为同行,我与宋代文史研究者一起,在向他深致敬意的同时,更跂予望之,乐观其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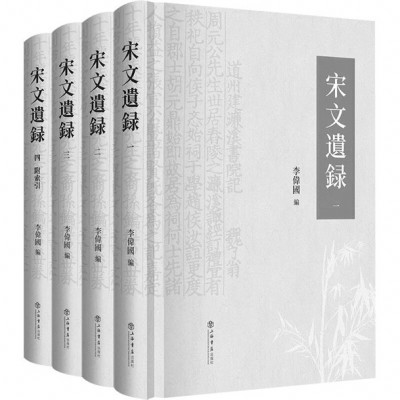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