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
1988年4月,我应邀赴美国,分别访问威斯康辛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讲演并进行学术交流。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广西柳州召开的柳宗元学术会议上结识美国学者、威斯康辛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Jr,1943-)先生。他是唐代文学专家,早年与人合著《柳宗元》一书,直到如今仍是西方学者研究柳宗元的唯一一本专著。当时我的《柳宗元传论》已经出版,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也得到他的赞许,一见如故。他和当时许多美国学者一样,有在台湾学习、研究或教学的背景,与台湾学者相熟。研究唐代文学是他的专长之一,因而与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唐代文学专家罗联添教授有长期交往,关系很好。罗先生著有《韩愈研究》《柳宗元事迹系年暨资料类编》等名著,饮誉学林,我也熟知并在研究中多所参考、借鉴。在当时的形势下我和罗先生尚不可能有结识之缘,而罗先生已经知道我研究韩愈、柳宗元的成果。倪豪士教授曾和罗先生议论过我和我的著作,并曾计划找机会让我和罗先生在香港会面。有这样一段因缘,1987年他来天津外国语大学访问,我请他顺便来南开大学看看。他当面邀请我去威斯康辛大学做短期访问。他回国后,经过往来通信商定,第二年春天我到威斯康辛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办个讲习班,由我来做关于唐代文学及其与佛教相互影响关系的系列讲演。又1986年秋我从日本回国后,冬天到广东潮州参加一个关于韩愈的国际学术会议,是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提议组织的、得到广东政协领导吴南生先生的支持。会议邀请不少国际知名学者前来参加,其中有美国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 1942-)教授。他是当代美国中国学领军人物,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精于辞赋研究,被海内外学界誉为“当代西方汉学之巨擘,辞赋研究之宗师”。当时他正穷精力翻译《文选》,已完成其中辞赋部分,分装两巨册出版。会议期间,我们有机会多次交谈,深相契合。他回国后著文介绍会议印象,有一节文字专门写到我,多作褒语,并说到中国经过“文革”已长时期没有评定高校职称,而不到五十岁的我已经被提升为教授(实际晋升教授是在日本神户大学任教时,日本文部省以外籍教授资格聘任我,信息反馈到国内,南开大学破格“任命”我为教授,未办理评审手续)。他听说威斯康辛大学邀请我讲学,通过在那里工作的他以前的学生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教授邀我顺访华盛顿大学。我当然珍惜这样的机会。又到威斯康辛大学所在地麦迪逊来往要路经芝加哥,倪豪士教授又安排我访问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系和宗教学系。这样,我初访美国,即访问这三所著名学府。
访问威斯康辛大学
四月初,我从北京乘中国民航班机到东京,转乘美国西北航空班机;是美国方面订购的机票。在东京羽田机场换乘,登机时经济舱已满员,我幸运地被安排乘公务舱。到芝加哥奥利机场,倪豪士教授派人来接,转乘公共汽车到威斯康辛大学所在地麦迪逊。有个小插曲:下车的时候,我告诉迎我的看样子是学生的人,他和我的车票钱由我来付;他说学校可以报销。后来听另外一个学生说,他们师生议论过,由中国来的人不少,像我这样提出自己要付车钱的,在他们那里还是第一个。自付车钱是我在日本养成的习惯。这种小节也表明,往往处理一些小事会给人造成某种印象。
倪豪士先生领我在学校安排好住宿处,办妥相关手续,即请我到他家里。是一座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典型的两层住宅。夫人是东方文物学家,在艺术品商店做事,没有孩子。当晚集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十几位研究生聚餐,表示欢迎。研究生里美国学生之外还有几个中国学生。有一位是大陆来的,其余都是台湾来的,态度大体都很友好。有个台湾学生向我了解在中国的生活情况,问我住房多大。当时我刚刚分配到四十几平方一套房,感到很满意了,回答之后,那个学生一脸的不屑。后来在一次讲演里我提到天津市的发展,说修了几座立交桥,也让台湾学生觉得好笑。其时状况如此,而我作为大陆教授的见识亦如此!
第二天会见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周策纵先生和刘绍铭先生。两位以前我都曾闻大名。周策纵先生在当时的大陆学界已经是知名华人学者之一。他的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广为人知,另有在中国出版的中文版《弃园内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有幸见到他,我很高兴。刘绍铭教授也很有名,台大外文系出身,在读大学期间曾和白先勇、叶维廉、李欧梵等人一起办《现代文学》杂志,1966年年纪轻轻就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现代文学专家,著述颇丰,亦很有创见。还见到一位教汉语的美籍中国人教师陈先生。他见到同胞,自然很亲切,向我介绍大学情况,多做指点。这几位都十分热情地接待我。在那里的几天,他们各位分别在外面宴请我。第二天晚上,倪豪士夫妇在家里正式设宴欢迎,形式很郑重,餐桌上点了蜡烛,素食,主菜是每人一个夏威夷水果,小西瓜大,皮上有皱褶,至今不知道什么名字。
在威斯康辛大学两周,做五次讲演。内容有宏观的,如“唐代文学与佛教”;有具体的,如“王维诗与禅宗”“韩愈的《原道》”。每次讲两个小时,然后讨论,时间一个下午。不少教师也来参加。周先生住家离大学很远,且已年高,基本是每讲必到;有一次他有事没来,第二天还特意来索取我的讲稿。他向我介绍美国以及威斯康辛大学中国学研究情况,请我到中餐馆吃饭;我在的时候,正赶上那一年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执导,尊龙、陈冲主演的《末代皇帝》获得最佳影片奖。他特意领我到电影院去看这部片子。我们进放映大厅的时候观众不少,开演一段之后观众开始纷纷离座,美国人显然对影片的内容不能理解。后来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又见过周先生几次。一次他提到我翻译的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的《中国诗歌原理》,说是还没有看到;几乎每次他都会问到我在日本留学的两个女儿的情况。学术大家这样谦虚,这样细心,让我钦佩、感动。他故去后,他在香港的学生、浸会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致教授等人编辑他的遗文成《周策纵文集》两巨册,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曾谋选择部分论作成书,在大陆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成。我在这里愿意插叙一个现象:我后来又访问过外国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每次讲演,许多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授、专家们都会来听讲,并参与讨论,其中包括不少是十分著名的学者。我早期出访时年纪并不大,学术成果也有限,来听讲的人大都知道我的名字、有些什么著作,交谈起来很亲切,也很容易沟通。但在国内大学受邀给外校学生讲演,一般情况下只是邀请我的教授或至近的朋友来听讲,其他教师、甚至是教学或研究课题内容与我相同或相近的很少有人来参加。这样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应当不只是我一个人遇到。
在讲课中有个细节:一位台湾学生提问,态度轻忽,望着天花板。倪豪士先生立即厉声告诉他:“你说话看着孙先生!”可见他对学生之严格,对我的敬重和友好。又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一位大陆留学生和他争吵,意思是在助学金分配问题上他偏袒台湾学生。他非常生气,对那位学生的无理指责大表不满,告诉我“你是我的客人,不要理他!”当晚那位学生夫妇在宿舍招待我,我规劝了几句。第二天早晨把情形告诉倪豪士先生,他只是笑了笑。这种小事让我更清楚地了解了这位先生性格的耿直、豪爽。当时大陆和台湾还没有多少交流,两岸关系还很紧张,台湾学生大都对我表现得十分友好。一位女生知道我有女儿在中学读书,特意出去买了一本英文词典,让我带回去送给她们。直到现在这部辞典仍保存在我的书房里。我回国后其中有的人还和我通信,写博士论文向我请教。
十多天,多数时间倪豪士先生陪伴,参观图书馆,逛书店。特别是有充裕时间向我介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状况:哪所大学或研究机构有哪些人,有哪些成就,出了哪些新书,还有美国中国学界人事关系、逸闻趣事等,让我对美国的中国学界有了比较细致、深入的了解。他曾开车领我看过一个古战场;又到农村参观,遇见种西洋参的农民,向我推销西洋参;他们夫妇还请我看了一场歌剧——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有一天赶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把我请到家里看电视直播。高德耀教授也热情地招待我。还有一位日籍教授在家里举办招待会,也请我去参加,很热闹,认识了许多人。空闲时间我在麦迪逊逛街。小城,很安静,书店很多,商铺、餐馆基本是服务大学的,确是读书、教书、从事研究的好地方。
当初倪豪士教授邀请我,说可以提供路费和食宿费用,结束讲课后意外地付给我1200美元酬金。
临行前,我请倪豪士先生替我安排一个西餐店,宴请他们夫妇。届时他们正装出席,愉快地度过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乘美国著名的灰狗巴司赴芝加哥。
我和倪豪士夫妇结下持久的友谊。大约十年前,就是我到美国访问他二十几年之后,有一天学校外事处来电话,说一个美国大学的代表团在北京,要专程来天津看我,问我能否接待。我答说可以。原来是倪豪士夫妇陪同他的大学校长来北京师范大学访问,想专程来天津访问我。届时南开校长设宴招待。倪豪士见到我热情拥抱,众人都为之愕然诧异。
访问芝加哥大学
我早晨乘灰狗巴司离开麦迪逊,中午到芝加哥。时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以研究明清 小 说 著 名 的 马 泰 来(1945-2020)教授在汽车站迎候。马教授我早已耳闻大名。他精于中国古代文献和小说研究,所著《采铜于山——马泰来文史论集》2017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另有《新辑红雨楼题记》《林纾翻译作品全目》等文献学论著。我下车的车站前面就是芝加哥美术馆。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参观美术馆。我答说如不嫌耽误他时间,当然很愿意看看。这样,在美术馆大厅寄存行李,又在美术馆里面的餐厅吃过午饭,就有幸参观了国际知名的芝加哥美术馆。在其中的东方部看到许多中国文物,包括许多精美佛像,倍感亲切。当初联系好接待我的是李欧梵教授,李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在学期间曾与同学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其后赴美国哈佛大学从史华慈和费正清等,获颁博士学位。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专家,代表著作在大陆出版的有《现代性的想象:从晚清代当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我的哈佛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等。我到的当天是周日,他回纽约的家里去了,委托马泰来教授招待我。妥善安排在芝加哥大学宾馆住宿之后,马泰来教授晚饭前来接我,先是导游芝加哥唐人街,然后请我到一个中餐馆吃饭。当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唐人街店铺许多都悬挂着台湾旗帜,书店里摆满台湾出版的中文书,包括我写的台湾盗印的《唐代文学与佛教》。
第二天早晨,马泰来教授陪我到大学图书馆,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因为时间紧迫,略参观馆藏后,余国藩(Anthony C. Yu,1938-2015)教授来会。余教授是比较文学和宗教学专家,芝加哥大学巴克人文学讲座教授,以英译和研究《西游记》蜚声国际学界。他的弟子、台湾“中研院”李奭学编译他的论学文集《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200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互道仰慕后,领我到研究室,与八九位研究生见面,请我讲演。我只是粗略讲了研究古代中国文学必须注重佛、道二教影响的重要性,我提出在这一点上余教授的《西游记》研究乃是典型范例。讲完后略加讨论结束。
晚上,李欧梵教授从纽约回来,仍假唐人街中国餐馆招待我,马泰来教授作陪。席间主、宾几个人就中国文化、文学议论了一番,久久方散。
访问华盛顿州立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三天,转赴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华盛顿州立大学,途中在明尼阿波利斯转机。康达维教授在华盛顿机场迎候,然后驱车到他府上,在市郊一个多居住美籍法国人的名叫Bellev⁃ue的小镇。他家也是典型的美国二层楼房住宅。夫人张泰平是位干练的女士,华裔,当时正在西海岸一份具有相当影响的中文报纸《华声报》服务。育有一个女孩,六七岁的样子,很可爱。因为住处法国侨民聚居,孩子习惯说法语。泰平女士说康达维十分宠爱这个女儿,逢生日、节日要花钱请小丑来家里逗她玩乐。孩子怕生,我来了,不得不送到朋友家寄住,让我住在她的房间。这让我十分过意不去。我坚辞去酒店住。不允。客从主人,只好住下。次晨天刚亮,听下面车库有汽车发动声,知道夫人已经去报社上班;早晨起来,康达维教授准备早餐,餐后领我去学校,召集学生做个简单讲演,访问的正式任务就算完成了。在坚辞之下,当晚我搬到大学附近的一个酒店去住了。
在华盛顿这几天,得机会和康达维教授详叙。一方面了解他的工作:正在做《文选》汉译,他把已经完成、出版辞赋部分两册,赠送给我。古典辞赋铺张扬厉,辞奇语奥,向称难解。康达维的翻译注释部分文字篇幅不知比原文要长多少倍;有些条目旁征博引,像一篇篇短论,显示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广泛利用中、外文献的功夫,令人叹为观止。交谈的另方面是美国学人的工作,他特别向我介绍了薛爱华(E.H.Shafer)的《撒马尔罕的金桃》(The Gold⁃en Peacher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nag Xsotics;吴玉贵中译本: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等考订类著作,让我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又带我游历城市周边,参观渔市等;曾驱车到美、加边境,本想到边境另一边温哥华的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但是到边境不允许通过。询问边防处之后得知,台湾人可以,大陆人要办签证,而签证手续需要五个工作日。我们只好废然而返。张泰平夫人代表报纸对我做了一个专访,在她工作的中文报上刊出,配有我访美的长篇报道,称我是“美、中文化交流的使者”。
有一天,接到一位旧识司马德琳(Madeline Spring )教授打来电话。她是康达维教授的弟子,研究唐代文学,曾到天津访问过我。她说所在克罗来多大学要办博士班,希望我推荐中国学生。这当然是件好事。回国后我替她推荐了一个学生。三十年后她转职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又曾请我专程前往访问,下面还将讲到。
在访美临近结束的时候,我遭到一次失窃,让我对美国的法律得点感性认识。在美国的最后一天,逢周六,我从酒店外出,发现裤兜钱包里放了一叠美元;美国朋友曾一再告诉我出门不要带较多的钱,我就回酒店把六百美元装个信封,放到箱子里。信封里还有些日元,箱子没锁。回来发现,美元剩下一百元,日元没被动。我担心打扰康达维夫妇,但还是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让一位社科院来访学的女士帮我报案。晚饭后报案,等了好长时间,警察局回电话说周六案件很多,需要排队等候处理云云。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来了一男一女两个警察,了解情况之后,他们说:酒店规定贵重物品要交大厅柜台保管,所以丢失东西酒店没有责任;能够进入房间的只有两个人:柜台管理人员和清洁工。他们推测柜台的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事情暴露他会丢掉工作;唯一值得怀疑的是清洁工。他们询问酒店管理人员清洁工情况,说是个黑人妇女。按她留给酒店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没有人接。他们估计是她拿了钱,正赶上周末,应该是出门消费去了。我们问能找她来询问吗? 他们说不能,现在没有权利询问她;说我周一可以到法院提出控告,法院批准才能动手办案,而且时间会拖得很长。他们又说窃贼正是利用这一点:酒店旅客多是暂住,失窃了也没时间追究。就这样,做个记录,不了了之。这让我近距离接触一次美国警察,了解了他们办案的方法。第二天早晨,仍是康达维教授送我到机场,“强迫”我吃点东西,买了带给家里的礼物,依依惜别。
回程又遭遇一件事。这回是“有惊无险”。乘坐的仍是美国西北航空班机,还是在东京转机,到东京的时间是下午六点左右,按行程要在东京住一夜。飞到东京下机,在出发大厅看见一个中国民航飞北京的航班正在办理登机手续,经和柜台的人商量之后,我就坐上这架飞机,晚八点到北京,赶上火车回到天津。但行李没能在东京转运跟过来。我只好第二天到北京机场去取。当时国际航班不多,我到的时候机场行李厅没什么人,里面有间屋子堆满待领的行李,找到我那个箱子,推出来,到出口,被海关的人拦下来了。气氛很严肃。我说明缘由,然后开箱检查。大概海关的人也没什么事,检查十分仔细,衣物、书籍一件一件地翻,包装的礼品盒都粗暴地撕开。其中有一个礼品盒底下我真地放了当时是“违禁”(当时台湾出的学术书,版权页上有“中华民国”年号都在“违禁”之列)的印刷品。看那个海关的人拆开了,翻了翻,竟没发现什么。当时我真感到头脑发涨。按当时的规定,如果被翻出来,携带违禁物品,算是违反外事纪律,反馈到本单位,后果会很“严重”。但结果顺利过关。折腾了有半个多小时,原来好不容易把箱子塞得严严实实,勉强合上盖子,经翻过之后,东西杂乱地堆得像座小山。海关检查的人扬长而去。在日本、韩国的海关我的行李都曾被仔细严查过。那里海关的人大底是一边检查一边道歉,大意是说按规定不得不如此云云,查完后会亲手把东西整理好,按原来在箱子里的位置装好,鞠躬致意,放行。真得佩服他们工作的严谨和记忆力。海关作为国家的入口,颇能反映其时国情的一面。
两点感受
结束三周第一次访美行程,做了几次学术讲演,和三所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结识一批新朋友,得到不少学术信息和资料,收获是相当丰盛的。有两点我尤其印象深刻,对我后来治学影响深远。
一点是,我此次访美,加上两年在日本,得以了解两国的学术现状和动态。与国内的情况做比较,感受突出的一点是,西方(日本在思想、学术领域应属于“西方”)学者治学一般题目更具体、更注重文献功夫,而国内多数学者无论研究题目还是内容大体更注重宏观状况、多作议论。特别是日本学者的工作,往往是下大力气考辨一个词语或名物、考证一个事件或人物,看似显得琐细,甚至难以发现其学术价值。但正如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亲自到日本考察后所说的,就像编织一个网,日本学者结好一个个网点,集合起来就成一个完整、结实的网。对于长时期受到“左”的冲击、“以论代史”倾向还相当严重的我国学术界来说,借鉴西方这方面的观念和做法是十分必要的。我向来主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质上即是历史;而研究历史,揭示史实真相乃是首要的、基础的工作,在日本执教、到美国参访,也让我更加坚信并努力实践这一点。
第二点是关于我个人的,事属渺小,不过对我自己却关系重大。上世纪80年代我还比较年轻,学术成绩有限,但在日本、去美国遇见的学界同行大底知道我,不少人读过我的书并表示赞赏。我心里清楚这当中有很多是面谀溢美之辞,但也可以体会到不少是真诚的称赞和期许。国外中国学界对我的书如此看重,让我大受鼓舞。而在得到精神上的鼓励之外,又结交下不少外国同行,后来许多人和我长久持续地保持友好交往,给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不少实际帮助。
14年后的2002年10月我曾偕内人访美,当时是去参加在亚利桑那州Tussen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会议同时庆祝康达维教授六十五岁诞辰,我们有幸参加晚宴,作为中国学者,夫妇被礼为上席,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欢迎。
25年之后的2013年,我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之约偕内人往访,时间从9月12日到10月22日。还是经康达维教授精心安排,在这一个多月里,再次访问华盛顿大学,接受康达维夫妇的招待;又受到旧识司马德琳教授邀请访问南部凤凰城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这样就游历了美国西海岸从最北端到最南端。本来东海岸一些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知道我来美也有朋友商量往访,由于时间限制,且东、西海岸奔波过分劳碌,乘飞机要六个小时,只好婉拒了。在伯克利我们住在小女儿孙一菂处,她在伯克利大学Department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担任高级研究员。在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受康达维教授委托,由戴梅可(Michael Nylan)教授接待,是一位研究中国思想史、艺术与考古方面成绩卓著、相当有影响的学者。她十分热情好客。除了安排讲演、参观、正式宴请等学术交流活动之外,还在家里亲自下厨,请内人、小女儿和我享以美味,并约来她原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夫妇作陪;她还把用自家院子里柿子树结的柿子亲手做成的柿子酱送来让我们品尝。在中国研究中心讲演,我讲的是中国古典禅宗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听讲的人坐满一个大教室,讲演后讨论,反应热烈。在亚利桑那大学,司马德琳主持东方学系,见到老朋友高德耀等人。讲演和宴请的时候意外地有著名宋史学家田浩(Hoyt Tillman)教授听讲。虽然他和我本来“隔行”,但像是对我相当了解并深表钦佩。
这是我最后一次访美,近一个半月,时间较充裕。小女儿工作有余暇能够脱身,有较多时间陪我们一起旅游:用一周时间驾车游览犹他州,走了犹他州一大圈,参访多个国家公园;又乘游轮游历墨西哥;参观好莱坞等旅游景点。这在我来说是多年海外工作中少有的休闲机会。
又这次访美4年后的2017年,我八十岁,康达维夫妇趁来华访问机会,专程来天津并预先在香格里拉饭店预定寿宴,为我庆生。这次,又在天津接受他们的热情招待。只是我们相对感叹渐入老境,只能以健康长寿互勉了。
就这样,我们访美,他们夫妇也多次来天津光顾舍下,和我们夫妇结下深情厚谊。我们交流学术信息,我也帮助他们解决中国研究中的一些问题。2021年最近的一次,他转来另一位著名中国学家柯睿(Paul Kroll)教授有关汉译佛教文献中的一个问题,我解释后,得到他们两位的赞许,康达维先生说在我这一辈学者中没有人在熟悉这类文献方面超越我,学者中我是他最为赞许的人(There is no scholar of your gen⁃eration who has more insight in⁃to texts of this kind. I have long told Taiping that the scholar I most admired is Professor Sun.)。这当然是扬誉之辞,也算对于我们友好交谊的一种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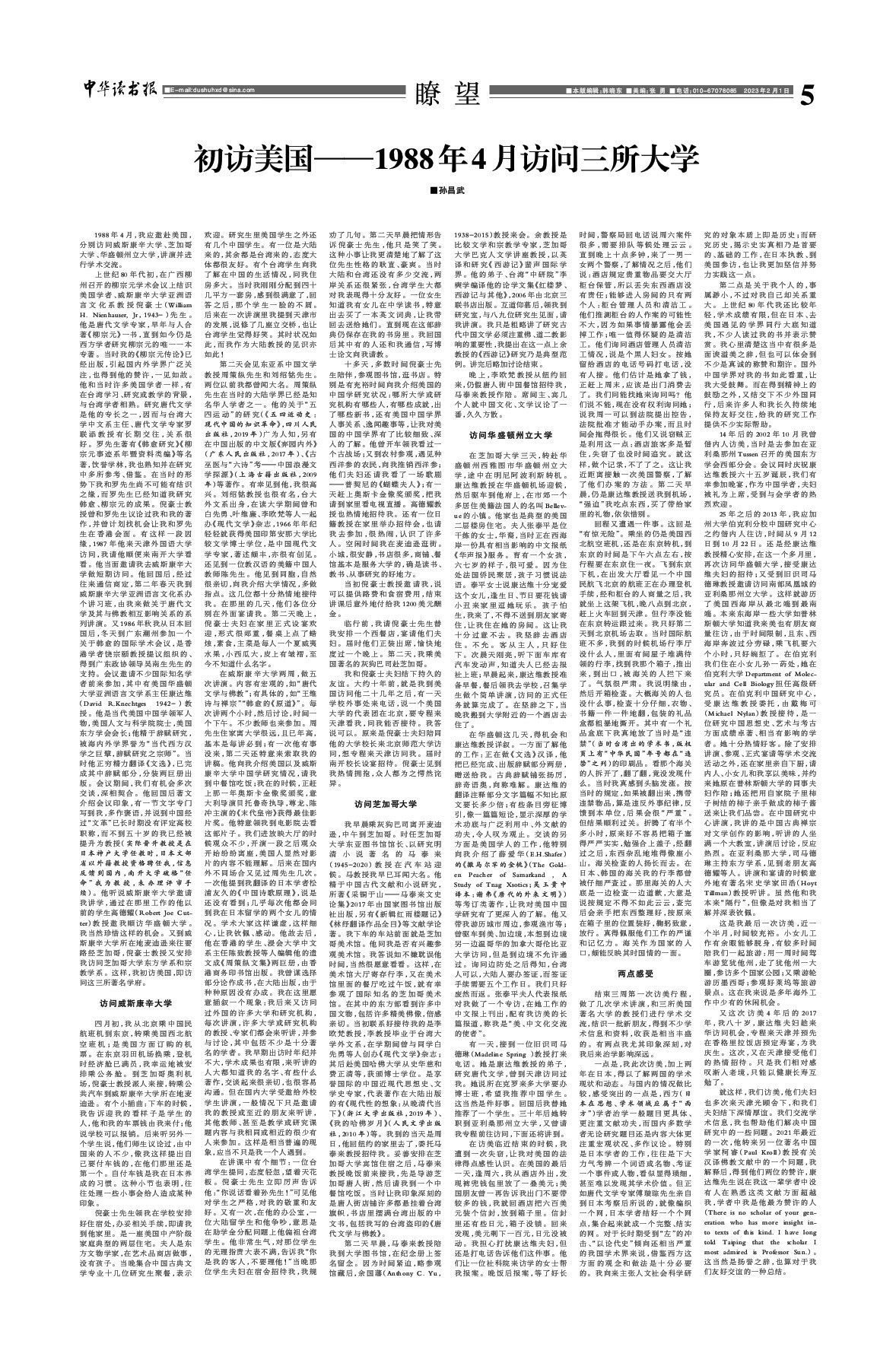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