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曾经说过:“舞台是一座蕴藏无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狱,是天堂。谁能想象得出艺术创造的甘苦与艰辛呢?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演出,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炼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焦菊隐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有出息的艺术家都企望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它是用渊博的知识、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汗水一点一滴浇灌而成的。”在焦先生的引导下,于是之开始领悟“演员真该像是一个苦吟诗人”,于是他敏锐地去感应,把生活的里里外外不遗漏,一丝一毫地都记载下来,记在情感中,记在笔记本里。
认识程疯子的过程是很长的。虽然刚一接触剧本就像是碰见一个熟人,但是对这个角色的完整的理解,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用几句简单的话把他说出来。
我爱我这角色——我认为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因为照我现在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水平,我还不能有一个胸襟去爱许多人、许多角色。剧本的第一遍朗读,已经把我带到生我长我的地方。那些人,我都似曾相识;那些台词,我都是一句一句听着它们长大了的。
我的杂院生活和那一些演剧经历,除了叫我体贴我的角色,同时也加给我一种责任:我觉得他们要我替他们打抱不平,替他们诉苦。在排练中我意识到了这个责任,我乐于接受它,因为那些不平与痛苦,都是我曾经亲身尝过的。这种责任感成为我在工作中的一个最好的推动力量。
旧社会里艺人大都受压迫,但却未必都疯。凡是疯了的,我想除了社会原因以外,相对地说,也多少有些他自己的弱点:大家都同是受压迫的,为什么单独他就疯了呢?那一定是有他个人的思想上成为决定因素的某些弱点。为了使疯子的那些弱点(如自尊,不实际,对现在不满就逃避现实……)找到合理的根据,我把他定成旗人子弟,唱单弦的。因为这些子弟们从小总是娇生惯养,不知道一粥一饭的来处不易。据了解,这些人都嗜唱单弦,原来还都是“票友”。但是,出身这样不好的人,何以又会有那么样一种善良的心地呢?我们按程疯子的年龄推算,在他小的时候,正是民国初年,清朝贵族已是没落的时候了。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听长辈讲说往事,总离不开分家、妯娌吵架、卖产业等等内容;疯子这位子弟,就是在那个环境中长大的,而且,在大家庭里,或是因为自己的生母是被迫买来的小老婆等原因,已经是处在被欺侮的地位了。随后,他在不断地“没落”过程中,了解到更多的事情,对于好歹就大致有个分寸了。因此他可以同情许多受委屈的人,但是“绅士出身像害天花病似的……就是病好了之后,满脸的疤总是去不掉的”(《夜店》台词)。他总觉得自己毕竟与大家还有不同,甚至能以自己还曾经是个虽是受委屈的少爷而骄傲了。体验生活开始的一个阶段,主要的目的成了给程疯子找历史,最后写了一篇六千字的程疯子传,才算对程疯子有了个比较系统的认识。神秘不凡的程疯子,在我的脑子里消灭了,他不是“革命的候鸟”,只是个可怜人,倘若不是北京解放,他是没有活路的。我也希望给观众的印象能是这样。
“疯子究竟疯不疯呢?”我碰见过好几个同志这样问我,但是我自己一直不这样想我的角色,我只想给他在思想感情上找到一条线索……
这位旗人子弟出身的可怜人,所以被人叫成疯子,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属于思想上的。照我们现在的分析,他可能是个抱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人,自卑自尊错综在一起。他想不明白他为什么竟会落到这步田地,他以自己如今靠吃老婆度日为苦恼,他想他应该出去做事情,也应该有事情让他做,但事实上没有。他对娘子是满怀惭愧,于是他也就想,总有一天做点事让大家看看。除了对赵大爷充满了尊敬以外,对于其他邻居,则认为他自己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好出身”,过过好日子。因此,虽然自己比谁都不如,但还满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心理,觉得别人都是可怜人。他自己有个小天地,拼命维系着这个脱离现实的“精神逃避所”,像小孩子吹胰子泡儿一样,觉得它实在好看,同时又生怕它万一破碎了。
另一个原因是属于外在的,身体形态上的。正因为他有前面所说的那种思想,和从没有参加过别种劳动,使他浑身必然地,也是习惯地保留着旧艺人气息。他请安、作揖,表示自己有礼有节;他总要穿件“宁穿破,不穿错”的大褂;曾经打过“脚布”的脚,弄得至今腿脚还不利落;头发还能让人想起他梳过辫子的模样。他的这些习惯,和这些没落历史,在他身上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也足使龙须沟的人们对他另眼相待了。
程疯子的性格随着故事的进行,时代的变化,他是有很大的发展的。怎样处理他这个发展过程,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于我,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解放前的程疯子,在一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境界中,勉强培养出一个自己的小天地来。
沟真的修了,而且程疯子也看上自来水了,有事情做了。现实的变革和实际的利益,教育了他,告诉他活着是有指望了,于是他也不再乱想了,安心做事了,他也就实际些了。
焦菊隐先生说:“演员体验生活时,应先普遍深入这一阶级阶层中去观察体验,不该奢望一下子找到典型,应先找类型,最后形成典型。”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是曾经吃过苦头的。我们曾经为了演《胜利列车》到长辛店工厂去体验生活。我演一个木工,他是个党员。当时有好几个爱好文娱活动的工人同志经常与我在一起谈、打腰鼓、扭秧歌。我觉得他们都不是我的“对象”,不是角色所需要的人;把那单纯地看成是我体验生活以外的“辅导工作”。另外我再把我的角色介绍给他们,把剧作者对那角色所做的注释读给他们听,要求他们替我介绍一位恰当的“对象”。工人同志们热心地帮助我,但他们想来想去,也很难完全找到那么一个人。结果,在工厂里住了一个月的时间,纵然每天碰见的都是工人,体验生活的收获却少得连自己也很难算得出来。现在想起来,当时就是犯了“奢望一下子找到典型”的毛病。本来人的思想情感是有阶级性的嘛,同一阶级的,特别是同一生产单位中的人,他们必然会有同一性质的思想情感,只可能某种情感在这个人身上少点,那个人身上多点罢了。只要我们善于去发掘,普遍地去注意、比较,很多人身上都会有我的角色。记得去年十月一日(指1950年,编者注),组织腰鼓游行的时候,正值《龙须沟》体验生活在进行中,我发现我们的总领队于夫同志脸上有一种笑容,是属于北京人的,是与角色有关的,我回来反复模拟和发展,结果成了现在程疯子脸上的基本样子。从焦先生教我领悟了这个道理,才算开始知道生活本身有多么丰沃。演员真该像是一个苦吟诗人,敏锐地去感应,把生活的里里外外不遗漏,一丝一毫地都记载下来,记在情感中,记在笔记本里。一定要“先找类型”。典型是存在的,但他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哪一个人的身上,只存在于作家的笔下和演员的创造里。
我明确了体验生活主要是指着体验思想情感,也只有你要发掘汲取的目的是思想情感的时候,你才会觉得现实生活的丰沃,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我泡茶馆的生活中,每天看着那些人,先后走进茶馆来,谁见谁都半鞠躬半请安地行一个礼,然后找个地方坐下,用一包茶叶,一两盘围棋消磨一整天。那里也有个小台子,上面摆着几件大鼓、三弦之类的乐器,有的“子弟票友”上去唱了,台下的人就听得入神,下棋的就头也不抬。在这种环境中,我逐渐明白了许多事情,我明白那位老名宿为什么单到那个游艺社去表演,我也明白为什么有那么些人每天都在这家不为人所注意的茶馆里打发岁月——因为他们带着与程疯子性质相同而数量更多的弱点,使他们觉得到现在还没有他们去的地方;只要找到一个能让他们温习故日生活的所在,哪怕地方再小再脏,他们也是愿意去的。因此,我想到程疯子第一幕住在杂院里的心情,一定与他们同样地希望找到一个能让他温习故日生活的所在。但他已经完全找不到那么一个地方了,连想泡一家极简陋的小茶馆也不可能了。他既然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他的理想世界,只有缅怀于自己的过去,在脑子里孤零零制造出一个小天地来,自己勉强维持着,陶醉着。这样的人当然是不爱干活儿的,他住在那个杂院里,也只有和孩子们闹闹,把岁月打发过去算了。另外,我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总是请安、作揖,见人寒暄那么半天,主要是:为了表示他自己有礼貌、有教养;这却并不太有尊重对方的因素在里面,因为我看他们行礼的时候,连看对方都不看一眼。这种礼节,我也适当地用在角色上了。
从我托人介绍去认识某一位与角色较接近的老名宿,到我在茶馆里普遍地注意到许多的人,因而得到丰富的收获,这个实践的过程,更巩固了焦先生所教诲给我们的体验生活的真理,更雄辩地批判了我在《胜利列车》体验生活中的错误观念——要一下子找到一个“模特儿”是不对的。现在,我想,倘若当初我只找那一位名宿学几段单弦,也许到现在单弦能有一两段唱得不错,但对于我的角色的创造,又有什么用处呢?至多我也只能熟悉他一个人,无法比较,就不容易知道哪些情感是带有这一阶层的普遍性的。
就在龙须沟附近住着一位艺人,他原是上海某家剧院的“二路角儿”,因代老板约京角而那位角儿唱砸了,一气而中风。现在腿脚很不利落,需要拄着棍儿走路,寄住在岳母家。戏,自然是完全不能唱了。
从他身上也看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他比谁都没法生活,甚至会叫人想到他为什么还活下去。他在杂院里的地位不高,甚至是叫人看不起;但他毕竟自觉不凡。记得我第一次碰见他,他从人群中扶杖走过,头也不回。在他,也许是由于自卑或是由于众人都不理他而避开众人的,但从客观上看,他是很高傲的。
说起往事,他眉目传神,一脸唱老生的表情。语调更是抑扬顿挫,颇有趣致。语汇中不通的“文言”甚多,诸如“故所以”“故此”“果不其然”等。
仅仅这一次的拜访,对我创造的帮助就太大了,甚至可以说,比我在排演《胜利列车》时住在长辛店工厂里一个月里边的收获还要大些。自尊和自卑,在他身上是那么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在整天被人看不起的生活中,“有个墙缝口”他都想“眯起来”,但他拉不下脸去求他的故人,他对他们“那脉子人”都要躲着走。他寂寞得可怜,周围没有亲人,用一个不能指望的“盟兄弟”当作自己生活的支持力和希望。当发现有人能尊重他和他谈谈的时候,他能滔滔不绝,把一切都说给人听。这一切,都最直接地帮助了我去创造程疯子,甚至他当时所说的某些话,也都化为我现在台上所说的台词。另外,他更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因为我认识了他,我想起我的角色在解放以前,应该叫观众看不出像程疯子那样的人会有什么活路,是解放了,才逐渐看到他的前途。
跟随焦菊隐先生工作,是一种幸福。在排演场里,焦先生沉静,细致,说话不多。他让每一个演员,每一个职员,都尽量地创造。他不时嘱咐我们说:“要尽量放开,尽量地突破自己,不要怕不像样儿,导演可以帮你收。”在补充老舍先生的文学剧本的时候,焦先生让每个角色自己写作,或者表示自己希望有怎样的一场戏,怎样的一些话。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偶然地发现一两个手势,一种坐或走的姿态,觉得可以或应该用在表演里。那么以后该怎么办呢?怎么把这个动作具体地运用到戏里去呢?我在以前演戏,往往就把这些东西直接地设计在哪一段戏或哪一句台词里。结果总是僵硬不堪,自己也感觉到和别的角色搭配不起来,但是还不忍割爱。人家说我犯了形式主义,我就更不以为然,因为自己以为这些动作是从生活中吸取来的!这次,在《龙须沟》的排演中,焦先生纠正了我的错误,他告诉我说:“你要把那个典型性的外形动作,孤立地练习,练习,不断地练习,在反复的模仿中,你会体会到那个人当时所以那样动作的内在动机,也就是他的思想情感。然后在排演场里,要忘记那个动作,只要你情绪掌握对了,那个动作就会自然地出来了。”
这次演程疯子,在走路的样子上,我也是经过创造的,但这回并没有硬搬,我是依照焦先生的指示做的。开始我是从侯宝林先生的一次表演里得到的素材。他模仿白云鹏先生唱大鼓的神气,他弓着腰,一步一步地向观众走来。侯宝林先生表演得那么真切,我虽然没见过白云鹏先生,但也能使我相信白云鹏先生会是那样的。就在这同时,我也想到程疯子也会是那样的。我要把这形象用在我的角色的身上。于是我开始练习,我在生活中学那样走路。在我不断地模仿中,开始是发现只有打过脚布的人才会那么走;继而是愈那么走就引起我的联想愈多,而且也愈把我的联想向思想深处引去:我发现了这种走路与茶馆里那些人的半请安半鞠躬的礼节是分不开的;又因为这样走路不会走快,我发现了这种人或者根本就不想快走,慢慢走正可以让他慢慢想……我很难用笔一一记出我在练习这种走路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么多的联想。但是,总的我可以说,从这外形的模仿中,又帮助我体会到更多的程疯子的内在情绪。
(本文摘自《北京人艺演员谈表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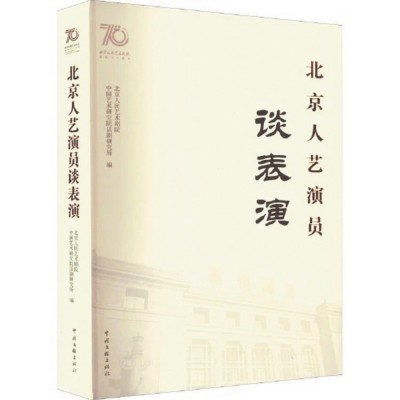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