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北京洪堡论坛——区域国别学研究生沙龙”系列活动的第二期内容,四位学者从世界史、地图史、国际关系史以及汉学史的角度,以具体的实例对区域国别学进行阐述。“北京洪堡论坛——区域国别学研究生沙龙”系由对外经贸大学冯晓虎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罗林教授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丁隆教授共同创办。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主任):
今天我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谈一谈我对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理解。我主要想说三个方面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是研究政治还是研究语言和文学? 是研究政治还是研究社会和文化? 是仅仅研究大人物还是应该把接触和了解人民群众放在重要位置? 首先说第一点。外国问题研究者需要非常严格的外语训练,那么专业八级是否足够呢? 譬如研究区域国别问题的学者,肯定不仅是需要看一点外文书和读一点外文媒体上的消息,而是需要跟外国人和外国文化广泛接触和深度交流的。那么这一特定学科的专家到底需要多高的专业外语水平? 语言文学在区域国别研究里面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我今天特别想强调的是,专业外语训练在区域国别研究当中应该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我觉得外语学院以外的机构和专业,对这一基础训练的重要性目前还是强调得远远不够。
其次,我还想说的是,除了政治和政策之外,区域国别研究显然是需要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我们去越南或者韩国访问的话,如果我们跟他们谈地缘政治问题,他们的感受肯定跟我们的感受是不同的,双方的沟通需要很细致、很敏锐才能顺畅和深入。譬如说我们研究越南的学者在河内的街头是否能够跟别人进行无障碍的交流? 而在学术会议上,学者要不仅能够作书面的或者口头的正式报告,在涉及敏感问题的时候,还要能够温和同时又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同时让对方能够理解和感受到对话的空间。对方的表达可能会很含蓄,但其实他的情感和观点都在他的表情里面、语气里面。这还是涉及语言能力问题: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到底需要多高的外语水平? 我觉得应该远远超出“专八”水准。但是我们现在设置的学科培养目标,似乎还没有对外语的刚性要求。譬如对非外语院系本科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或者在外国史研究这样的领域,我们现在并没有规定他掌握的研究对象国或区域的语言需要达到什么水平,是否应该有一个不低于外语专业本科生水平的刚性要求?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几乎把非英语的中学外语教学都停止了,原来有些地区有很好的俄语和日语的中学教学,现在基本上没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博士生的研究领域是北非、西亚和巴尔干地区,我们如何安排他们学习阿语、波斯语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各种语言?总不能就会英语吧? 提供外语学习条件和设定外语学习目标,可能是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重大和基础性问题。
另外,区域国别研究的外语准入标准是什么? 研究英国和美国问题的学者掌握英文就可以了吗? 这似乎是符合常识的情况,但真的可以吗? 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如果通晓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西欧大陆语言,还有俄语、越南语等,肯定大大有利于他们研究涉及美国历史和现状的一些重大问题,譬如冷战和越南战争,譬如俄美关系、越美关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中外关系的研究经常需要放在多边关系的语境中来进行。
我举个例子。最近媒体经常提及一个情况,就是在东欧的地缘政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多数人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与多数人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在地理上靠得很近,在历史上有过冲突,而且双方在这些冲突中都受过伤。但是在20世纪和当下,这些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的紧张关系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未必有明显的关联。天主教和东正教传统上的文化保守性甚至是这些民族与俄罗斯之间对话和相互认可的一个基础。研究俄美关系很难单纯由美国历史研究的角度进入,研究者还需要对东欧和俄罗斯历史有深入和广泛的了解。美国精英和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很复杂,正面和负面的元素都很丰富。没有对俄罗斯文化细腻和敏感的把握,不了解俄罗斯文化在美国的真实和重要的地位,我们很难正确判断俄美关系。培养一个研究美国的区域国别问题专家,仅仅掌握英语是不是够? 比较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的学界,起码有少数美国问题的专家应该同时也通晓俄语,同时是俄罗斯问题的专家,且没有单方面的倾向性,能够敏锐地感受俄美两国的文化和政治动态。
最后,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关注到政府政策和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当然也会关注很多大人物和有名的人物,但同时也应该关注普通老百姓以及这些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我的感觉是,在最近的几十年,我们不太注意美国的普通人。由于商业和贸易竞争,我们不仅不太注意美国的劳工阶层,也没有去认真和系统研究在这种格局下如何去处理和改善我们与美国工人、普通人的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肯定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不光是对美国、欧洲和日本,对越南、韩国以及中东和东南亚的国家,好像我们的研究现在都不太热衷于关注那里的基层社会和普通人民。所以我觉得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发展兴起——如果我们能把握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把眼光更多地集中在普通人身上。
综上,借助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发展,我们需要研究沉默的大众,用多学科的、多方位的视角去观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普通百姓,应该有一些同情的观察和理解。过去我们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劳动人民之间的友谊应该是中美关系和我们其他对外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想说,我们的眼光,不要老盯着那些著名的大人物。我们能不能更多关心一下国际关系和中外关系中的普通人? 如果我们忽略了普通人,我们怎么可能掌握像美国这样一个复杂社会的未来走向呢? 所以一方面是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中,需要把外语训练作为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不要老是把研究集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大人物身上。
汪前进(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今天讲一个小的问题,说是小,但意义却很大,叫做“以小见大”。这个问题就是:世界的中心究竟在哪里?
为什么会讲这个问题呢? 当年,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将所带来的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挂在教堂里,中国人看后比较惊奇与喜欢。因为是外文,看不大懂,故人们建议他译成中文。但在译成中文时遇到一个问题,因为原图把中国放在最东边,不符合中国人“天朝大国”的观念,中文图应该将中国放在中间。利玛窦只得这么做了,他所绘的《大瀛全图》《山海舆地全图》和《坤舆万国全图》都是这样,后来的《两仪玄览图》也是如此;而且几乎所有的其他传教士绘制的世界地图也遵守这一“规矩”。利玛窦虽然这么做了,但他心里很不舒服。他写信给耶稣会上层人物说:因为中国人不知道地球实际是圆的,处处都是中心,也就是说,地球本无中心;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是在中心;而且中国人又夜郎自大,认为他们国家才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中国人愚昧的表现。直到今天,不少中外学者也深以为然。
我当年读书的时候看到了这些观点,也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后来接触了许多外国古地图,发现利玛窦的观点很值得商榷。就是说,即使中国确实曾有很多落后的地方,也有很多愚昧的地方,但是如果用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是站不住的。为什么? 因为很多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或者别的文化传统的地图,绘图者几乎都是把他的国度、他的文明、他的宗教起源地放在地图的中间。利玛窦时代的欧洲地图里欧洲几乎都在地图的中间,其他民族也莫不如此。既然如此,中国人要求把自己的国度放在中心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关于“世界中心”,有两种表述方式,一种是观念上的,一种是地图上的。
我们先来看看观念上的。古希腊人认为德尔斐神庙就是世界中心。他们将“中心”称作“肚脐”,欧洲文化也认为肚脐才是中心。犹太人把犹太圣城太巴列作为世界中心,这跟《旧约》有关系。还有人认为耶稣的圣墓是中心。也有人认为死海是世界的中心,因为它是陆地上最低的、咸度最大的一个“海”,这在《圣经》中也被提到。印度教和藏传佛教都认为神山冈仁波齐是世界的中心。其他的地方也有关于世界中心的观念,比如澳大利亚土著人认为艾尔斯岩石是世界中心,又如复活节岛也是一个中心,有人认为巴厘岛上的阿贡火山是世界的中心,秘鲁的印加帝国认为古城里面的太阳神庙是世界中心。中国古人早期认为天下之中在今天河南登封县告成镇——那里至今还保存有周公测影台,后又认为是“洛邑”(洛阳,“洛州无影”)。由此可见,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世界中心观念。我们知道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有一句名言:“谁统治了欧洲,谁就统治了世界的心脏地带”,“谁统治了世界的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他认为东欧就是心脏地带。所以不仅不同的文明有自己的世界中心,不同的政治文化理论也有自己的世界中心。
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各民族所绘的世界地图是如何表现世界中心的。巴比伦人画的世界地图是把巴比伦画在中心。《马赛克地图》是拜占庭时期的,也是把首都画在中心。几乎所有的欧洲人,特别是教徒——无论是信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认为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所以早期的地图中三洲(亚、欧、非)交接的地方就是世界中心。后来的一些图,如西班牙的世界地图,毛罗的世界地图,也是把耶路撒冷当作世界中心。后人复原的托勒密世界地图(旧大陆)也是把耶路撒冷置于地图中心。伊斯兰世界绘制的世界地图均以圣地麦加作为世界中心。古印度人的世界中心在哪里呢? 佛教徒认为南瞻部洲(实际是以古印度为中心)是世界中心,即人所居住的洲是世界的中心,而中国被称为东震旦。历史上,朝鲜人信奉中国文化,接受“天圆地方”的观念。朝鲜人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也是将中国置于地图之中。这幅图和中国的《大明混一图》(约1389年)一样,画出了欧洲和非洲的轮廓。
由上可知,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文明都有自己的世界中心的观念。利玛窦的偏见应该说不攻自破。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我首先回应一下刚才两位老师的发言,尤其是彭老师提的两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所有外国语大学都面临的两个问题,可以称之为灵魂之问。那就是:国别区域研究有没有门槛? 如果有门槛的话,这个门槛是什么? 换言之,是把学科作为门槛,还是把外语作为门槛? 刚才汪老师的发言可以概括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学科门槛:历史学科的可能觉得,不懂历史,怎么能做区域国别研究。外语学科的可能认为,外语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前提。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不懂一点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最基本的理论,怎么能做区域国别研究呢? 总之,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门槛,因此要形成共识是很难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开展今天这样的跨学科讨论,在交流中增加各自对其他学科的了解。
另外,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彭小瑜老师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庶民历史。我是研究政治学的,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对美国历史也比较关注,因为做美国政治研究必须对美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美国历史学界我不太清楚,但在政治学界,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后,有两本畅销书,在我看来就是庶民史。第一本畅销书是《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作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她在南方几个州进行了田野调查,以了解中下层白人为什么强烈支持特朗普。第二本书是《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作者前不久赢得了共和党俄亥俄州参议员提名。这本书讲述的是作者作为底层白人在单亲家庭成长的故事。还有一些类似研究,我就不在此赘述了。总之,2016年以来,美国政治学界一直在通过“庶民”的视角反思“特朗普现象”,分析特朗普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受到如此多底层民众的强烈拥护。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当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一个学科”。区域国别学的繁荣其实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知识需求。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门大国独有的学科,这是国内外学界的共识。全球大国必然有全球利益,而要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就必须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历史上,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其区域国别研究曾经独领风骚,拥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这样引领区域国别研究的名校。二战后,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其区域国别研究突飞猛进,短时间内赶超了英国,时至今天仍然处于世界绝对领先的地位。
那么,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呢?我就以自己的经历和观察谈一些粗浅想法。我在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学习了六年,获得博士学位,因此对美国政治学算是比较了解。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政治学系一般包括五个研究方向,分别是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政治学理论、研究方法,其中比较政治研究的是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不涉及美国与他国的双边关系或者他国外交,后者属于国际关系领域。也就是说,比较政治研究的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具体研究话题包括政党和选举、社会福利、民主化等。比较政治分为两类,一类是聚焦某个国家或地区,如中国或者中东,研究者成为“中国通”或者“中东通”,他们往往不追求广度(理论构建和假设验证),而是更注重深度(细节描述和因果分析),另一类则相反,重在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无论小样本或大样本)进行理论构建和假设验证。
在我看来,美国的比较政治和我们今天讨论的区域国别研究高度相似,但两者之间也有着重要区别:第一,美国的比较政治属于政治学,而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拟定为交叉学科,可以授予文学、法学、历史学学位。第二,美国的比较政治兼具深度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广度,而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更强调深度(上面提到的“三通”人才)。第三,比较政治一直聚焦外国国内政治,而现阶段区域国别研究更注重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关系。第四,比较政治被认为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国别区域研究的宗旨是资政服务。尽管两者之间有着上述区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取经,包括追求严谨的研究方法、兼顾深度和广度、强调田野调查、注重研究者外语能力训练,等等。
虽然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个新的一级学科,可以说“路漫漫其修远兮”。我认为,可以制定长期、中期和短期发展目标。长期目标是在中国培养亨廷顿、普沃斯基、福山这一类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关注有全球普遍性的问题,提出了创新性的概念和理论,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研究。中期目标是在中国培养李约瑟、傅高义、安乐哲这一类的学者。他们一生致力于研究某个国家,成为享誉世界的“美国通”“日本通”“德国通”,等等。短期目标就是在座各位每天的日常工作,我把它概括为“学生、学会、学刊”,其中“学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才培养,涉及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招生规模等等。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教授):
刚才几位教授都谈到了借鉴西方经验,就此问题我也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区域国别研究在德国的发展历史。位于德国鲁尔区的波鸿大学曾被称作德国乃至全世界最丑的大学。但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它在1962年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科理念,这一理念就其本质而言,其实就是一个区域国别的设想。我以东亚学系为例,来具体介绍一下波鸿大学的学科设置。
波鸿大学东亚学系第一次把中国的文学、语言、历史、哲学、政治和经济放在一起进行教授,统称为“Area Studies”。波鸿大学建校之初,就确立了这样的一个办学思想,即重视各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东亚学系下属的东亚研究所,设置了一个汉学和一个日本学教授的职位,并将所有和这个领域相关的专业都合并在一起,以保证东亚研究所在此领域内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为满足东亚学系不断发展的需要,学校在发展过程中还设置了更多的教授职位。2005年我在波鸿大学担任兼职教师的时候,东亚学系研究中国的教授就有四五位,这跟传统的德国大学完全不一样,例如波恩大学汉学系就只有一位教授,海德堡大学也只有一位或者是两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波鸿大学当时确实进行了地区或者区域研究的新尝试。
此外,波鸿大学在建校之初,还专门为东亚研究所制订了一个计划,并再次强调了这个新成立的研究所的特点:这是一个中心研究所,它的阵容、研究方式和设施都超越了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范畴,囊括了区域研究的各门学科。而语言学和历史学是这个东亚研究集群的基础,它使东亚学各个专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成为了一种可能。这个计划是1964年提出来的,即便今天看来,它依然十分具有前瞻性。
1964年3月2日,东亚研究委员会按照区域国别研究设置了12个教授的职位:第一个是汉学——主要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第二个是日本学,第三个是中国历史,第四个是日本历史,第五个是东亚当代史,第六个是人类文化史,第七个是东亚社会学,第八个是东亚地理学,第九个是宗教学——主要是佛学,第十是东亚艺术史和考古学,第十一是东亚法学,第十二是东亚经济学。这个设置充分表明,早在1964年,波鸿大学就已经开始讨论各个东亚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很多边缘学科,比如说蒙古学、越南学、朝鲜学也同样得到了重视,因为区域国别研究跟其他的研究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语言的问题,从事东亚研究的前提是掌握这门语言。此外,文学和历史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这12个教授职位的设置在汉学研究史乃至整个德国的高等教育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97年在波鸿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在他的报告中提到了以下三点:一是区域的固定性的观念已经站不住脚了,因为区域是流动的,区域的边界是不确定的,因此,区域之间具有相互渗透性。200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全球史更强调这一点。二是区域研究不再是出于自身的目的,而是理解全球性的论题的基础。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关联性,是一种相互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种独立的身份。三是跨学科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方面,而是更加注重实践。这位学者的观点虽然是在1997年提出来的,但我觉得它实际上跟今天我们讨论的区域国别学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今天在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时依然会强调这三个方面。
我本人长时间从事德国汉学史的研究工作,而德国汉学本身是东方学的一部分,因此,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东方学何时可以转型成为研究区域国别的学科? 我们在研究汉学时经常会提到东方学的学术史,会审视以前曾经忽略的问题,同时形成一种新的学科意识。我想这可能就是区域国别学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契机——它将很多我们以前认为不可能放在一起的学科组合到了一起,这个学科群将给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研究成就,形成突破。希望今天的这个跨学科的讨论能使我们对区域国别学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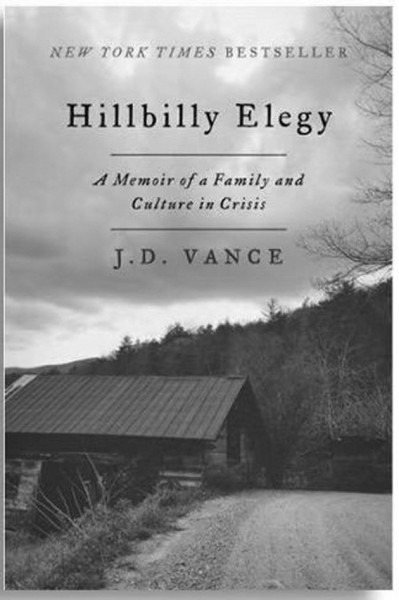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