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收到潘英杰兄的赠书《国学十年》,上面收录了悼念霍韬晦先生(1940-2018)的文章十篇。其中不乏介绍霍先生学术的篇什,如《儒家性情学的开新与落实》《不死的文化》等,钩玄提要,颇能弘阐师门之学;更多的则是记述自己亲炙霍先生的从学经历,如《我来继起》《招魂未已,我辈归来!》《千劫万劫,只待重逢——敬悼恩师霍韬晦先生》等,鞭辟入里,每使我心有戚戚焉。我受教于霍先生虽然不如英杰兄之久且专,但也算有幸亲承了先生的咳唾。掩卷而思,从前与霍先生交往的片段又一幕一幕涌上心头。
霍韬晦先生生于广东南海,中学时代赴港求学,1960年就读于香港联合书院中文系,并随佛学耆宿罗时宪先生修学,1964年考入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随当代大儒唐君毅先生修习儒学。1969年,霍先生赴日本京都大谷大学精研佛学。1972年,霍先生返港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首开印度哲学、印度佛教哲学、梵文等课程。1982年,霍先生受聘担任新亚研究所研究员。同年,创办法住学会。此后三十余年,霍先生致力于佛教思想的现代化和儒家性情教育,曾创办法住文化书院、法住出版社、香港中医专业学院、喜耀教育文化基金会、抱绿山庄(广东肇庆)、喜耀粤西学校(广东罗定)、新加坡文化学会、新加坡喜耀幼儿乐园、马来西亚喜耀文化学会、新山喜耀私立学校(马来西亚新山)等众多文化实体,涉及的范围涵盖学术、出版、艺术、教育、培训等诸多领域,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彰显当代儒门罕见的创造力和行动力,平生讲学以“性情”为宗,主张“文化回归生命,读书长养性情”。
我得以受教于霍先生应从与郭文龙先生的结识说起。2009年,我取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没有继续深造,而是选择参加教育工作。2010年的冬天,有一次我去百胜楼(Bras Basah Complex)逛书店,就在一家书店旁边赫然发现原来本地居然有一个专门推广儒学的文化团体——新加坡南洋孔教会(Nanyang Con⁃fucian Association)。在厌倦了学院儒学的风气之后,我对民间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自然,我当即毫不犹豫地敲开了南洋孔教会办公室的门,进门在里屋坐定,赫然看见墙上挂着一副醒目的对联,上面用遒劲的隶书写着“绝境生大信,无事见精神”。霎时,我猛觉有一股淋漓的元气、刚健的力量扑面而来,呼应着我内心中蓄势已久的困惑。我在心里暗忖:究竟什么是“大信”? 一个人怎样才能在平居无事时也精神饱满? 撰写这副对联的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直到与郭先生相见,我才得知这副对联是霍韬晦先生所撰。当晚,我与郭先生一直聊到深夜,从儒学是什么,到儒学的现代实践,再到南洋孔教会的自我定位,我的一连串提问单刀直入,郭先生的答复也直截了当。从对话中,我了解到郭先生的一系列答复是受到霍先生的启发。事实上,正是由于霍先生的指引,郭先生才逐渐放弃商业的努力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儒学的弘扬中来。从此,虽然我尚未与霍先生谋面,但他在我的心中已经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此后,我曾在稠人广坐中听过霍先生的几次讲座。印象最深刻的是2011年霍先生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所做的“辛亥精神如何承继? ——兼评孙中山之三民主义”讲座。霍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自发的救亡运动。它由推翻满洲政权,进而争取民主,再进而谋求富强。但是,辛亥革命并不彻底,虽然暂时扭转了中国的命运,却很快陷入新的危机。霍先生认为,“三民主义”必须再加上“民德”,只有将其奠基在“民德”的基础上变革才有内在的文化保障,才不会腐败变质。又如,2012年为响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起的全国大对话而做的“新加坡还需要什么?”讲座。霍先生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在于融会了中西文化,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但是,近两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正面临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新加坡未来的发展如果要避开这些危机和陷阱,本质上就是要在融会中西的基础上开创出一种新文化。如果想要长久地维持繁荣,这是新加坡需要做的深层努力。再如,2014年在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主办的“儒学与国际华人社会”国际儒学研讨会所做的“儒学为什么可以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发挥作用?”讲座。霍先生提出,近百年的中国走上了文化与生活撕裂的道路,用他的话叫做“形神分离”。但在海外,儒学依旧存活在海外华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只是概念的存在、学术的存在。海外华人社会之所以能像孤臣孽子一般在无依无靠中顽强生存,关键就在于对作为华人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坚守。
霍先生的讲座有如洪钟大吕,每次都让我深受震撼,也让我看到自己的无力与渺小。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我虽然已遍读四书五经,也曾博涉诸子与史传,但我并没有穿透历史的千年之眼,也毫无回应现实之力。霍先生对辛亥、五四、抗战等历史的大关大节处,总是寄以深情,并投入深切的思考,以期打通历史的关节,疏通文化的命脉;在亚洲金融风暴、茉莉花革命、新加坡全国大对话、英国脱欧等大是大非面前,他总是出以悲心,提出明确的方案,以期回应现实的困境,化解人类的危机。梁启超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这很可以用来说明霍先生的悲愿。辛弃疾有一句词:“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我以为,霍先生便是当代儒门中一位真正的经纶手。
2011年,我报名参加了霍先生主持的“喜耀生命”初阶和进阶课程。记忆所及,这门课程包括诸多精心设计的环节,旨在通过特定的生命“实验”,促使学员真诚面对自己,认识日常生活中常常被自己忽略的深层的心性障碍,通过锻炼、点拨、反省而找到生命成长的方向。活动的设计融入了现代心理学、企业培训的一些方法,但在根子上则是儒家的仁学和禅门的机锋。霍先生是佛学专家,同时接续了现代新儒家的学脉,早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后又经历数十年民间讲学的磨炼,越发显出打落知见、直击人心的力量。老实说,我对喜耀生命课程的设计并不完全理解,甚至一开始的时候还非常抵触。事实上,连霍先生自己也说:“光明的人性并非失去,而是在现代文化天罗地网下,人变得无力。人若要苏醒,非施以较猛烈、或较适切的药不可。”既为“猛药”,当然就不是无施不可的。尽管如此,我在这门课程上的收获还是极大的。在环环紧扣的“实验”中,我被迫直面自己的习气,我看到自己身体的僵硬、情感的冷漠、心灵的狭隘,原来在经历二十年的学校教育和人间世故之后,我的身心已是如此的不柔软,我的情感已是如此地干枯;原来我对学术以外的世界已是如此地封闭;原来我的自信只是一副精致的伪装,其实我早已是“乱山无数,不记来时路”,既听不清自己内心的声音,也迷失了真正的方向。在我的进阶结业证书上,至今还保留着“要做一个有承担力的读书人”的契约。课程结束后,我写了三首诗呈给霍先生,记录了我当时的实感和领悟。重读这几首小诗,仍能扪触一种如获新生的心情:
其一
出户偏怜草木青,一山关己动诗情。春江焉用东风送?原本怡然自在行。
其二
误把春山围做城,谁怜山外绿盈盈。出山莫辩内与外,绿水青山满眼明。
其三
行人原与碧山亲,却向山尖觅早春。春色无言随看在,浑然不见有行人。
霍先生勉励我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建议我阅读《天地唯情》《都市通识》二书。回家后,我立即认真阅读这两本书。我在《天地唯情》一书的边框上写着:“情是生命的动力,是行动力,这是情的深度;情是生命的空间,是开放性,这是情的广度。”在扉页写的是“把情通出来”。现在想来,这短短十天的两期课程对我实有变化气质、旋乾转坤的大力,让我从心量狭小、日趋麻木、理性缚结的学术习气中觉醒、松动和挣脱出来,重面自己的真情,重拾自己的初心。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现在要给它下一转语:“未能真诚面对自己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反思自己的。”一切都必须真实地回归自己的性情。
2016年,我全程修读了霍先生在新加坡开设的《经学与现代社会》一门课程。课程一共八讲,从“经与经学”一直讲到“晚清经学”。由于我个人也一直关注经学的现代转型,这门课在我而言可以说是如渴得浆,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制的。结束后,我整理了录音稿,并由张静师姐做了修订。其中第一讲的讲稿后来以《经与经学——〈经学与现代社会〉之一》为题发表在《中国文化》第45期(2017年)。遗憾的是,其余各讲尚未来得及审定,霍先生就遽尔与世长辞了。霍先生强调:“我们要让经学的精神重新复活,重新找到它在现代的新意义。这个工作要在新的文化格局中进行,要与现代世界和西方学术会通。”这也是我现在努力的方向。同年10月,霍先生发愿开办国学专修班,希望在全世界华人青年中招募真正有志读书的学生。霍先生托郭先生转告我,希望我和华庆能报名修读。非常遗憾的是,当时我在修读博士课程,正在着手撰写论文的节骨眼上,没能及时报名参加。我当时想,霍先生一向精神矍铄、精力过人,等我博士毕业再从容向他就教的机会应该还有很多,没想到这一愿望如今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我的儒学道路主要是受到“文化焦虑”和“人生焦虑”两种内在力量的驱动。其中,得力最深的是劳悦强先生。在劳先生那里,我唤醒了自己的文化意识,学会了读书,也接受了较为全面的传统学术训练。四书、《史记》、诸子乃至佛学,我都是跟劳先生亦步亦趋学的。自始至终,我跟随劳先生一直读到博士,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也深受劳先生的影响。前不久,我发表了一篇名为《现代经学的思想史进路——劳悦强经典诠释方法论述评》的论文,算是这方面的一次粗浅的汇报。劳先生也讲人生,但他更多的精力是用于诠释经典,透过经典体认文化,立足文化思考人生。在他的学术关切中,应该说文化是第一位的,人生是第二位的,这在我看来正是钱穆一脉学术的法乳。而在霍先生那里,他更重视生命的实感和性情的开发,他以一种淋漓酣畅的生命存在与其他生命觌体相见,以心观心,以人治人,常使人当下有省,有时真能使人体会到陆象山所说的话:“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霍先生也讲文化,但他说“真正的文化不在书上,而在人身上”。因此,人生才是第一位的,文化是第二位的,读书则是更次要的。这一宗旨,应该说是对唐君毅先生学术的继承和落实。可以说,是劳先生将我引入经典的世界,而霍先生则将我从经典的世界中剥落出来。在我看来,这两脉学术都真切感人,都足以廉顽立懦,貌似相反,实则相成。我的焦虑至今还没有完全消融,这两脉学术始终给我可靠的指引和温暖的亮光。
回念往昔,感怀师恩。读了英杰兄的悼念文章,让我又掉落到深深的回忆和感恩中。作为霍先生一个短暂亲炙的学生,我并没有忘记先生的斧琢,也不敢遗忘自己立下的约定。我写下这些回忆的片段,既是对先生的一种纪念,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就像英杰兄在《霍师丧礼感怀》中说的:“霍师往生了,以前那一个一直不接地气、时而被概念所转、时而被现实所惑、时而被欲望所困的不长进的学生呀,才稍稍地醒悟过来。”我期盼自己像英杰兄一样,在固有性情的提撕中,在前贤学术的光照里,也能从习气、概念、现实和欲望中稍稍地醒悟过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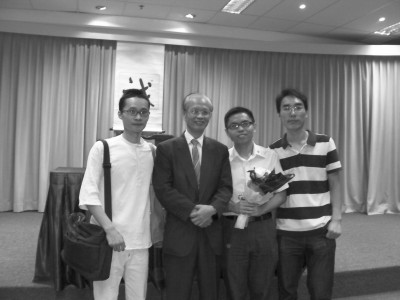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