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为中国读者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德语作家之一,斯蒂芬·茨威格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首先归于某些先入为主的认识——他是畅销书作家,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擅长心理描写,被认为是最懂女人的作家;他的中短篇小说享誉世界,多次被搬上舞台或银幕。与此同时,跟多数畅销书作家的命运相似,刻板印象和负面评价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视其为通俗小说家、二流作家的人并不在少数。张玉书先生在《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一书的代前言中,就曾提到在德国拜罗伊特大学讲学时的一桩旧事。当时一位德国同行把茨威格归类成通俗小说家,并称茨威格的作品之所以雅俗共赏,乃是因其文字浅显,缺乏深度。
茨威格被普遍接受的另一个身份标签是:回避政治。这个标签并不是空穴来风,且无论作家本人还是后世研究者都不予否认。在《良心反抗暴力: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一书中他写道:“我对政治深恶痛绝。”在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中,他也曾说:“我从不属于任何党派,从不关心政治。”纵观其文学创作,尤其贯穿其一生的人物传记,可见他的“不问政治”是一种超政治的态度,是刻意回避历史中客观存在的细节。他终生热情拥抱审美与智识,冀望以永恒的精神价值克服混乱的现实政治,通过伟大人物去营造理想的世界。
1881年出生在维也纳的茨威格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那时的维也纳是多民族国家的首都,是犹太人最为向往的世界中心。在和平安稳的社会环境下,加之家庭提供的优渥条件,茨威格自小便接受良好教育,具备丰厚的语言基础和文学底蕴。大学时代的茨威格,跟百年前的德意志大学生一样,在欧洲旅行,结交文人墨客。1901年,他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诗集《银弦集》。他做翻译、写小说、当编剧,足迹从欧洲延伸到美洲,潇洒而令人艳羡。茨威格早年所见是细腻敏感的人心和壮丽多姿的世界。没有紧张的政治,战争和疾病也只是烘托人生多舛命运无常的道具而已。
当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时,个人的呐喊就被淹没在扬尘与轰鸣之中。20世纪初,世界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变打破了茨威格生活的平静。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去战争新闻处做志愿工作。一战结束后,他返回故乡奥地利继续写作,同时在公开场合亮相,反对极端化和民族主义。一战当中有无数犹太人奔赴战场,为祖国而战,因此那时并没有损害到犹太人的身份尊严。真正成为作家生命分水岭的,是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的时刻。从此,他历来漠视的犹太人身份,再也无法如他所愿地躲在家谱或档案簿里,而是从作家生活世界的背景一跃走到前台,作为政治气候变迁的缩影,从此与他的后半生紧密相连,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尽管生活被迫转折,但文学创作却始终伴随茨威格一生。作家笔耕不辍的,并非为他收获最多拥趸的中短篇小说,而是一部又一部人物传记。如果说“一流”或“伟大”之类的评价,因没有统一标准而显得过于主观,那么,在茨威格的众多身份标签中,传记作家恐怕是最不容质疑的一个。在中国读者当中颇具人气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版本一再翻新,令我们揣测,或许是茨威格早年的中短篇小说与这些群星过于耀眼,反而令他的其他十余部人物传记的光芒被暂时掩盖。
2
回顾茨威格的一生,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也大致与他的传记写作平行。第一个阶段是从1881年到1918年。在这一阶段,作家的生活富足安逸,所学习的内容、所从事的工作大多遵循个人喜好。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本人物传记《艾米尔·维尔哈伦》,这本传记的传主维尔哈伦是当时著名诗人,与茨威格本人感情深厚。
第二个阶段是从1918年到1933年。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茨威格的作品逐渐融入战争元素,他本人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战争。这一阶段的人物传记有更为宏大的视角。作家除了为自己的好友罗曼·罗兰作传外,还完成了“世界的建造大师”三部曲,共涉及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九位茨威格所敬佩的大文豪。《人类群星闪耀时》就出自这一时期。
茨威格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从1933年纳粹上台起,到1942年茨威格于巴西自杀止。纳粹暴政以及对于犹太人的一系列迫害行为,几乎波及整个欧洲。现实除了让茨威格更加坚定人文主义、和平主义外,还迫使他直面此前回避的身份问题——犹太人。当由一群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纳粹在德国掌权后,犹太人的身份成了他撕不掉也抹不去的标签。
作为一名犹太作家,茨威格在这一时期不得不同其他犹太人和反对纳粹政权的文人一样,开始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茨威格的写作随之发生了些许变化,但他一贯的思想并未改变。他笔锋一转,从为自己的好友、为钦佩的人立传,转而为一众寓意深远的历史人物书写传记。茨威格在1933年至1942年间共写作了六部人物传记作品,其中包括为十五六世纪荷兰人文主义学者所写的《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为十六世纪苏格兰女王所写的《玛丽亚·斯图亚特》,其中有法兰西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讲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发生在日内瓦的新教内部思想冲突的《良心反抗暴力: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为十七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巴尔扎克所写的《巴尔扎克传》,为十五六世纪航海家麦哲伦所写的《麦哲伦传》,以及并未完全完成的《随笔大师蒙田》。
这些传主均是历史人物,大多数还是失败者——或是丢了性命,或是丢了地位,或是被同代枭雄的光芒掩盖。六部作品看似脱离现实,把目光投向几十年甚至数百年前。值得玩味的是,书写历史小说或为历史人物作传,竟成了众多同时代流亡作家(托马斯·曼、约瑟夫·罗特)不谋而合的言志方式。茨威格对待政治历史一度执拗的超脱态度,一直笃信的审美与智识之力,终于不得不服膺“短暂的”然而却无法抵抗的政治现实。玻璃罩子里的梦已经无法继续,和平主义无可避免败给了敌我思维,这尤其体现在《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和《良心反抗暴力: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这两部作品中。
3
《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完成于1934年,正值希特勒及他所率领的纳粹政党完全掌握德国政权,茨威格接连经受打击的开始。先是柏林焚书行动,茨威格的作品也在被焚之列。纳粹禁止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由茨威格编剧的作品也同样遭到剧院禁演。此后,针对犹太人的禁令接连出台,以种族为由的冲突和压迫日益激化,压得这位优雅的畅销书作家喘不过气来。萨尔茨堡的寓所被无端搜查,令他最终愤然离开祖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将创作目光转向四百多年前的一位人文学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书中的一段文字或许能精准地概括两人相似的处境:“个人的意志在民众疯狂和世人分成宗派的时刻无能为力,有识之士想要远离尘嚣静心观察和思考纯属徒劳,时代会迫使他卷入乱哄哄的纷争之中。”
《伊拉斯谟传》第一章开篇便说,“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那个时代最伟大、辉煌的星斗,如今却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这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道出了作者写作的目的:让旧时的伟大人物复活。作者按时间顺序将伊拉斯谟的一生呈现出来,但他并不细数成长经历,而是侧重性格及思想轨迹,以个人精神肖像代替对时代政治现实的分析。正如雷昂·波特施坦1982年在《犹太社会研究》上发表的《茨威格与欧洲犹太人的幻景》一文所言:“他本能地把世界上其他体面和无害的人背后的动机简化为心理学上的真理。”
伊拉斯谟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富盛名的人文主义者,无论是查理五世、亨利八世等封建领主,还是芸芸学者,皆对他敬重有加。伊拉斯谟的学术成就十分辉煌:他用拉丁语写就的格言警句被奉为经典之作,他披露人性弱点的《愚人颂》广受好评,他用拉丁语翻译的《圣经》是路德译本的重要参照。作为一名有思想的学者,他倾尽一生发现并改善宗教世界的问题。在《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一书中,他讨论如何确保那些世袭王位的统治者受到正确教育,以便公正而仁慈地进行治理,使君主之治理永远也不会沦为压迫。他的君鉴具有普遍的价值,不会因统治者改头换面而失去意义。“伊拉斯谟精神”——呼唤理性与宽容,相信人性向善的可能,反对暴力战争以及任何一种形式的狂热,尊重思想独立与自由,建立并维护统一的欧洲——成为人文主义精神的缩影。
伊拉斯谟用“基督教精神”和拉丁语构建起来的学者共和国,使得共同的欧洲文化自古罗马文明衰落以来,又一次重新形成。然而16世纪初,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成为划时代事件,深刻影响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为中世纪以来天主教下的欧洲刻上裂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伊拉斯谟成了夹在天主教与路德新教之间的一块板。
一方面,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却反对严格的教条对思想的麻痹。他是一个温和的改良者,希望在宗教框架下进行改革。他潜心研究《圣经》及其他宗教学者的著作,在此基础上不断为天主教改革出谋划策。但是,他的种种努力在教会看来无异于挑战权威。所以,尽管伊拉斯谟至死都在公开支持教会统一,却无法阻止教会将他的所有著作列为禁书。另一方面,伊拉斯谟不符合宗教改革家路德的期望,他的中庸在路德看来是唯唯诺诺。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是在茨威格看来是两种人:“伊拉斯谟所追求的一切都是为了心灵的平静与安宁,马丁·路德所追求的一切则是为了振聋发聩和激情满怀的斗志。”罗马教会和路德都曾极力邀请伊拉斯谟加入自己的阵营,在他保持中立时逼他表态。
然而,伊拉斯谟不愿看到两个阵营彼此剑拔弩张,更不愿看到民众被迫卷入争斗。进退维谷最终导致两边都放弃了他。马丁·路德敢于公开反抗教会,带领德意志人挣脱罗马天主教会束缚,促进民族教会的成立,从此成了一座丰碑;而那位惧怕流血冲突、立场摇摆不定的伊拉斯谟,却迅速被时代精神所淹没,一度被遗忘。
4
这样一位绚烂一时又归于沉寂的人文主义学者,带给茨威格精神支撑与创作启示。茨威格曾表示,写伊拉斯谟是在“影射自己”,是在“运用类比法来描述,在他身上展示我们的典型和另一种典型”。他如此评价伊拉斯谟:“在所有西方作家和创作者中,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是第一个自觉的欧洲人,第一个为和平而战的斗士,在人文学科的研究和精神目标的追求中一位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凡争做第一的人,必然要面临巨大阻力。从这个意义上,伊拉斯谟对茨威格来说,是莫大的慰藉和精神同伴。
在文字审查和宗教裁判盛行时期,伊拉斯谟的《愚人颂》通过讽刺和象征手法大胆抨击世风时俗,成为黑暗时代里揭示并传播真理的可贵途径。因而,在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层面,这个人物也足以为茨威格提供借古讽今的范例。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及:“(写伊拉斯谟)是帮助我摆脱困境的救星,实际上只有助于我自己。”
与此同时,茨威格表露的有限却可贵的反思意识,常常为世人所忽略。茨威格认为,伊拉斯谟个人深层次的悲情在于,他在内心深处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清醒的怀疑论者;他没有忽视人性之中带着原始暴力因素的本能,深知单凭温和的说教不能祛除人性弱点,深谙理性在世人面前的局限,但却无能为力;他厌恶党派之争,却被时代风暴裹挟,不得不出面与马丁路德展开论战;他推崇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尊重与包容思想的多元,却不得不公开择一而贬一……这种种无能为力共同构成了伊拉斯谟身上宿命般的悲剧性色彩。
这何尝不是在说茨威格自己!
今天我们知道,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同样主张自由意志,根本分歧在于,前者将自由意志的罗盘交给人的理性,而后者把救赎的关键角色赋予神。伊拉斯谟的学者性格在难以以理智逆转的时代精神下,成了一种弱点。而这本是茨威格这样的知识分子自我珍视的宝贵品质。更为罕见的是,茨威格未沉湎于知识分子的顾影自怜,指出伊拉斯谟所信奉的,同时也是欧洲早期人文主义者们最核心的信仰——启迪理性就有可能促进世人进步——是一种悲剧性的错误。
遗憾的是,茨威格一直徘徊在人性善恶的维度上。他看到理性、宽容、和平之心,在暴力、战争以及为激情引导的狂热行为面前孱弱无力,并将其归咎于“人性之中动武和好斗的本能”。我们不由得叹息,茨威格是经历了怎样的跌宕才肯承认,知识分子需要走出象牙塔! 可是,他又是如何抱守历史宿命论,把人性作为历史事件的根本动力,固守在在现实环境与物质关联之外!
5
四十年前有学者曾指出,茨威格在一个飘渺而抽象的反政治空间里,在和平主义、艺术与思想共同体理想之中,寻找庇护和安慰;他试图用他的文学想象来影响欧洲的灵魂,就像他的诸多犹太前辈和同辈的历史书写者一样,引领公众舆论,拒绝政治话题;他否认自己出生成长的现实和亲历的政治环境,对政治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自我欺骗。比如,他眼中的维也纳只有和谐、共荣、理性、宽容,而事实上,贫穷、人口过剩、反犹、宗教和种族分歧带来的隔离,令维也纳这座城市充满了权力斗争和阶级差距,而这些却被隔绝在茨威格的视线之外。
同样被他过度美化的还有犹太性。犹太人的苦难历史在茨威格眼中具有特别的审美价值,西欧犹太人的融合在他看来也不是问题,因为他的祖上已经成功融合了一百多年。甚至他对赫茨尔的欣赏,也不是基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和政治实践,而仅仅是因为这位复国主义者性格上的卓尔不群。在茨威格后期的历史人物写作里,即便对黑暗时代的影射已不言而喻,但是他超政治的态度却几未改变。
1934年,茨威格移居英国。继伊拉斯谟之后,茨威格再次选择宗教改革这个时代背景,创作了《良心反抗暴力: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这一次的核心词是“反抗”。当人们歌颂宗教改革者的勇敢及功绩时,时常忽略宗教改革也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充满暴力压迫和不择手段。这部作品就记述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发生在日内瓦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这本人物传记的主人公是名不见经传的人文主义者卡斯台利奥,而鼎鼎大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则被塑造成鲜明的反派角色。全书共十章,直到第四章才轮到“卡斯台利奥登场”,前三章都在尽数加尔文的发迹史,如何通过对生活乐趣、精神享受、自由意识的打压,从宗教纷争的受害者变成统治者、独裁者、加害者。卡斯台利奥,一位贫穷的人文主义者,独自挺身而出,以笔为剑,为受到迫害的伙伴辩护,控告加尔文扼杀宗教改革运动初心——信仰自由,哪怕明知这场斗争无异于“蚊子抗大象”。
卡斯台利奥没能战胜加尔文,最终在贫困潦倒中去世。“暴力扼杀了良知”,如该书第九章标题所示。然而,作家并不甘心到此为止,而是以“殊途同归”为题结束全书。正如每个人都会死去,这个人人皆知的真理,也可以说并无号召力。这本书从头至尾都像一部呼告、一封控诉,一则不断回到当下的对话,让人读起来喘不过气。茨威格在书中表示:“十六世纪尽管和我们这个世纪相似,也狂热地信奉施行暴力的意识形态,但是还有自由思考、公正无私的人们。”他一如既往把良知、自由、精神当作对抗暴力的工具,最后写道:“倘若当权者认为,他们已经战胜自由精神,因为他们已经把它的嘴唇封死,这纯粹是徒劳。因为每一个新人出生,也会有新的良心诞生,它总会思忖他思想上的职责,要掀起旧日的斗争,为了夺回人类及人性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总会一再地有一个卡斯台利奥复活,来反抗每一个加尔文,来捍卫思想的堂堂正正、不言而喻的权利,反抗一切暴力之暴力。”这不仅仅是在评价卡斯台利奥与加尔文之间的斗争,更是在给自己信心,呼吁其他人联合起来勇敢反抗。
6
可是,茨威格的文字能够促成民众的政治行动吗? 他所信奉的精神是超脱于民众之上的,他笔下的人物,是无法被归入人民大众的。他一度的亲密朋友,比如罗兰,在将目光投向现实世界之后,也与他渐行渐远。在茨威格死后,阿伦特曾评价他没能抓住犹太性的意义来解释自己的人生。的确,仅从茨威格的文学世界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对犹太人命运的任何特别关注。
不容否认的是,尽管他营造的希望与现实环境相距甚远,但他从不教人绝望。他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或教科书式的导演,塑造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一段不成功的人生,却从来没有传达彻底的断念。这个理想主义者要把理想注入读者的头脑。而如何看清并积极回应现实,却不是其文学创作的任务。在茨威格后期的人物传记里,我们尽管看到他对现实政治的影射,可文字背后仍是那个漠视犹太性、回避现实政治、笃信精神胜利法的旧时知识分子。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难道活着的时候不去尽力保全性命,而是把信念放在死后世界对自己的承认吗? 从1942年茨威格的自杀来看,是的。他的所有作品,都不及他用自杀对这个黑暗的时代作出的回应更加直接。1939年之前就已经看清欧洲政治现实的人,心理上早已适应这个混乱的世界,不会因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而彻底崩溃。很遗憾,茨威格不属于那样的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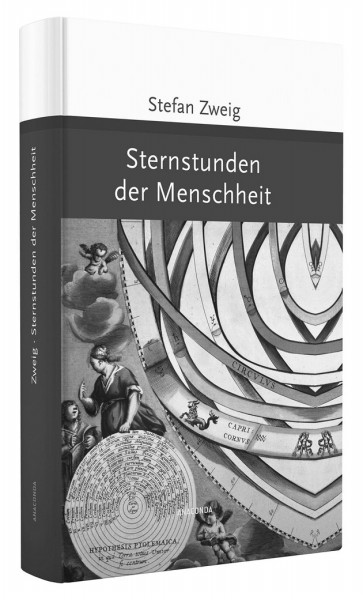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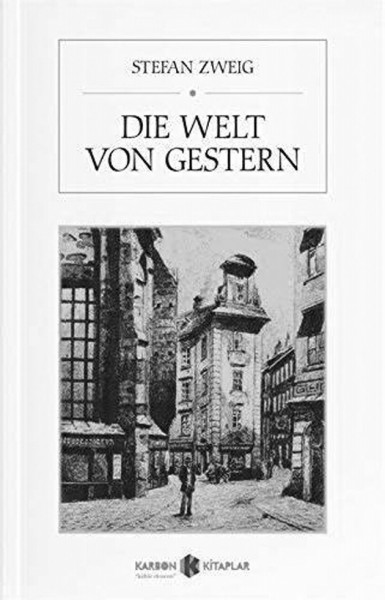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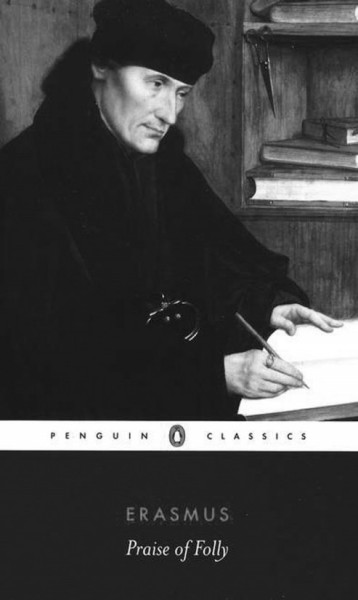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