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位置
原型和位置,这两个词,犹如《亲爱的笨蛋》放出的两只信号弹,我作为读者,会心一笑。我视其为徐海蛟创作的秘密。
原型是作家灵感的源头。画家于大岗,绰号老癫,是个疯子。我曾去大画家沙耆故乡采风,很想以纪实的形式写沙耆。徐海蛟和沙耆是同乡,他把已逝的沙耆,请进虚构的小说,保留了沙耆的诸多经历,以老癫名头,又畅快地活了一回,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小说的魔法。癫或疯,就小说修辞而言,是飞翔的状态,轻逸的形象。其实,老癫活得沉重,但他沉浸在“绘画世界”里,读者感到了一种轻,甚至,能在树杈间灵活地蹦跳。使我想到了卡尔维诺祖先三部曲之《树上的男爵》。童话的元素,轻逸的形象。以此,超越并抵消了生活之重。我生活过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有个护林员,他的窝棚搭在树上,像个巨大鸟巢,随着树长高,“巢”也上升,他专画毛驴,是个接受改造的右派,他让毛驴出面,来连队的大食堂领取每月口粮,毛驴一进连队就叫,像大喇叭,上士就会如数把粮食袋放在它背上。那是此类人的生存之智慧——都是另类,可笑可怜,但又可爱可亲。独特的形象往往能引起共情。
小说史,其实是一部人物形象史,其中有活跃着一个谱系:疯子、傻瓜、愚人。西方文学早先是笨伯,也就是笨蛋。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阿Q正传》中的阿Q(其标志是死到临头,还计较画押画得不够圆)。《亲爱的笨蛋》,作者引进疯画家,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搭档,一老一少,结成爷孙关系。两个男性搭档,本身就会出故事,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福尔摩斯与华生,《唐吉诃德》中的唐吉诃德与桑乔,均为一种二人转式的模式。唐吉诃德是疯子的变体,其标志已不再是骑士时代,却采取骑士的方式应对已变化的现实。《亲爱的笨蛋》疯老头以西方的绘画艺术处理置身中国的现实,这是一种滑稽的错位。比如第一章:树上有只可怕的大鸟——习惯了常规的学生,把在树上的老癫视为大鸟,怎么叫老癫下树? 众人束手无策。唯有孙子于一宝的呼唤起了作用,与疯子交流,得用疯语,那是另一套暗号式的语言体系:家中来了吴师长,要向您汇报工作。借已不存在的吴师长的幌子,实际已不存在,然而幻觉中存在——竟然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小说赋予疯子画家一种臆想,构成了小说鸟一般飞起的轻逸意象,爷孙就这样搭档,冒犯并抵抗了平庸的现实。
《亲爱的笨蛋》,人物和作家都有各自的位置,只不过,一显一隐。人物的位置很明显。董老师(校长)与疯画家为相对的两类人物的代表,代表着正常与异常,一强一弱。董校长的一方是规矩的制定者,势力、歧视,貌视自以为正确。疯画家爷孙俩一方,是规矩的冒犯者,也是小说的精神体现:冒犯。冒犯的同时,又守望,又破又立。孙子于一宝是一个独特的守护者的化身,这种形象我已在塞林格小说《麦田里守望者》见识过,前者是乡村,后者是城市。乡村更为难“守望”。陈规陋习积淀深厚。
小说这种体裁,作家隐在背后,让人物说话,其中,可以看出徐海蛟的操作痕迹——第三人称的视角,比如《笑起来真奇怪》那一章,关于不对劲的议论,等等。著名作家奥茨和帕慕克用关于鸡蛋和高墙比喻作家的站位。明知鸡蛋撞高墙必破碎,还是不约而同地站在鸡蛋一边。《亲爱的笨蛋》里爷孙俩,弱势、脆弱,如鸡蛋,却又意味着能孕育新的生命,书名里,鸡蛋前缀个“亲爱”的定语显示出了作家的站位。我想起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笨蛋是愚人的另一种说法,“亲爱”这个词,表达了作家赞颂“笨蛋”。不妨沿用比喻,把小说里的人物分为鸡蛋派,高墙派,并非不可开交的敌对势力,也不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而是价值取向各异引起的纠结。前者守望天性,珍视生命;后者老于世故,恪守陈规。这是一个怎么实现真正的“个性”的问题,或者说,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爷孙俩以及相关的人物(小李老师),以特有的方式冲撞了无形的“高墙”,体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同时,也成就了小说的价值。
人物、事件
《亲爱的笨蛋》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每一章,或两章,会发生一个事件,事件与事件之间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当然,作家介入,出于结构的考虑,时不时有承前启后的提示),属于非线性叙事。叙事像落入了巨大的漩涡,同时,也是人物的生存境遇。
小说的第一要务是写活人物。是事装人,还是人引事? 徐海蛟选择了人引事。我启用一个“引”字,一个人引出另一个人,一个人引出一件事,是人物主动激活了事(事装人,人物则被动)。人物统合了并沉浸在事件中。阅读中,我已不在乎“时间”这个容器,而关注空间(小岛的村庄)的容器。人物的亮点会像水花一样飞溅。作家脑子里重视了人物,可见每个人物都不怠慢(比如,给张老师配备一个细节:黑痣),由此,达成了群星捧月的文学效果。还写出了生活的情景,大海的气息,一幅活生生的海岛渔村的生存图景。尤其是人物在平凡物事中穿行,情节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细节在现实土地上闪亮。
高墙派固守“相像”——都一样,鸡蛋派追求“不一样”。就小说而言,“不一样”就是“这一个”。门罗说:人物做什么是故事,重要的是“怎么做”? 小男孩于一宝“怎么做”,表现了自己的独特性。
第一章,室内室外,树上树下,画里画外,各种关系中,徐海蛟由一只手切入,而且是小手,一个小学生的小手,局部引出整体,以小引大,这奠定了小说的格局。到了第十章,于一宝已被孤立,他不愿托人说话,而是选择了用手表达:热衷于举手,且不放下,老师不会叫到他。那长时间举手,颇有意味,存在而又沉默。回望第一章,小手引出大鸟——老癫出场的方式是在树上,不下来。与后来孙子只举手不发音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只小手,引出一个大人,进而引出一个小孩——小说的主人公于一宝。唯有他用独特的方式呼唤爷爷下树。有意味的是,作者介绍他的形象时写了破、乱、脏。地面,树上,爷孙俩的形象交相辉映。这么写头发:头顶一团乱蓬蓬的鸟巢。顺笔,树上树下的“鸟”形成了鲜明对比,凝聚成一个轻逸的意象。这部小说,有一系列意象群,消解和超越着现实的沉重。比如,用绘画召唤已逝的一位母亲,一条黄狗。
于一宝不合群,不一样,他表达孤独和关爱,选择拥抱树。第四章自作主张的优秀,他被孤立,没同学愿意跟他一起,他就去拥抱一棵榆树(榆,愚也),拥抱一个老朋友那样,仿佛成了树的一部分。小李老师问他,他说:就是想听听树的声音。与不会说话的树拥抱,这是文学的能量。第九章,听了会疼的故事,于一宝表达对即将出海捕鱼的父亲的爱,他紧抱着一棵橘子树,不让家人摘橘子:害怕橘子摘完了,爸爸就回不来了。孩子逻辑,把不相干的物事——橘子与爸爸,结成一种因果关系,对生命的珍惜,对大海的敬畏。人的脆弱与大海的莫测,都凝聚在拥抱并守望那棵橘子树上了。就如同我儿时,每天看地平线尽头的太阳升起,以为太阳是被我看出来了,进而,我认为,我离开欺负我的小伙伴所在的连队,那么,他们就沉浸在黑暗之中了。徐海蛟紧贴着少年的视角、思维、逻辑,写出了于一宝的心灵:纯真、诚实、善良、同情、正义。
我忘不了于一宝拥抱大树。海难中父亲去世,第十章写了他对各种动物、器物说话,又点到他跑去拥抱榆树说话,表现了失去父亲的难过和忍受。一个一个事件发生(后几章,转为了线性叙事,事件之间有了逻辑关系,画家的平反,于一宝的获奖,给人物弥补缺失,也透露出作家的圆满意识:好人有好报和苦尽甜来)。其中,一条小船,一个洞的事件,于一宝的守望者形象进一步深化,加载了“拯救者”的元素。就是这样,完成了于一宝心灵成长的历程。他能引发我的共情。守望本真,守望海岛,《亲爱的笨蛋》是一部成长的寓言,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守望者的形象。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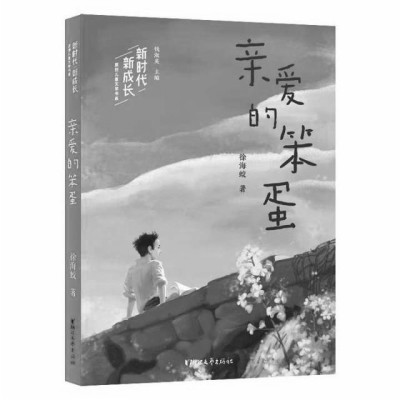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